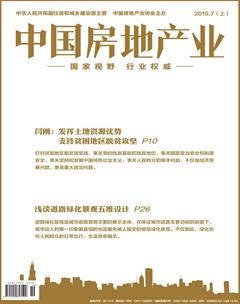利用G20時機推動WTO改革
在經濟全球化面臨新的阻力,全球經濟增長不確定性加大的情況下,亞洲國家加強貿易、投資和金融等方面的合作,是維護國際經濟規則和推動區域和全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動力。
二十幾年前,船橋洋一先生(Asia Pacific Initiative創始人)就提出過“亞洲化”,強調亞洲的作用,為亞洲尋找自身的定位;二十年后,新加坡李光耀學院提出了“Global is Asia”,中國和日本兩國作為世界前三和亞洲前兩位的經濟體,應該成為維護亞洲繁榮發展、多邊貿易體系和經濟全球化的中堅力量。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十年來,各國都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包括中國、日本。但全球比較下來,亞洲終究是在全球金融危機中經濟表現最好的地區,復蘇比較快,損失也比較小。
在全球金融危機前,2006年,中國的經濟規模按當時的匯率計算,只有美國經濟的不到20%。到了2017年,在保持了近十年的較高增長后,中國的GDP(國內生產總值)已經是美國GDP的三分之二。這顯示出不同國家和地區受到危機沖擊的程度和應對危機的政策有效性是不一樣的。如果在危機過程中,有的經濟體出現較長時間衰退或者停滯,就會使經濟體之間的比例關系產生很大變化。整個亞洲,特別是東北亞加上東盟這兩個地區,經濟都相對較好,因此亞洲在全球經濟中的比重得到了明顯加大,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占到半數以上。
因此,我覺得現在應該特別強調亞太對全球經濟的重要性。我們也關注到,在國際經濟貿易秩序受到影響的情況下,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的啟動也為亞太的貿易自由化和貿易規則的推進、為WTO(世界貿易組織)的改革做了鋪墊。6月底即將在日本召開的G20峰會,被寄予厚望,希望能利用這一契機推動WTO改革,維護全球多邊貿易體系的有效性。
中日貿易投資還有很大空間
最近40年,中日兩國貿易和投資快速發展,總體來講發展相當順利,但是還有很大空間。作為近鄰,中日之間相互比較了解。中國一些新的開放措施將提供很多發展的新空間,比如金融業擴大開放,日本的機構應能更好利用這一機會,發展得更快更好。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現的第一個外資銀行代表處,就是當時日本輸出入銀行(現為日本國際協力銀行)的代表處。中國第一筆外幣債券的發行也是在日本。
2002年,中國銀行首次使用了非上市公開募集(POWL)在日本成功融資。從2005年到2010年,工農中建四大行,還有一些保險、能源的領軍企業,也都通過POWL從日本投資者那里募集了資金。
中日在海外第三方、第三國的項目及融資的合作,也非常有潛力。例如,日本國際協力銀行和國開行在泰國一起做的一個項目;另外中投公司設立的中日產業合作基金;還有絲路基金,與亞開行、亞投行等國際機構的合作,在亞洲及“一帶一路”中都探討了對外合作的機會。雖然有時在有些項目上,中日之間也有一些競爭,但總體來講,合作的機會更多。所以李克強總理強調我們應在第三方市場加強合作。
在中日的海外合作項目上,一部分是基礎設施,一部分是生產能力,還有可能是支持社會教育、幫助減貧等一些項目。在這些項目中,多數都需要設計、施工、購買設備和材料,需要有項目的融資和建成后的管理能力,中間也涉及新技術,特別是綠色發展方面。這就構成一種產業鏈,需要發揮多家特長,在這些方面,中日共同合作的機會很多。
當前全球都非常重視科技發展,因為這是經濟增長的新動力,也是我們應對將來經濟社會新變化的必需。中國過去經濟發展水平低,較為窮困,企業的資源有限,所以投入研發的比重較小,從日本引進技術較多。在改革開放40年后,特別從最近這20年來看,局面已經大不一樣,中國企業在研發方面的投入開始大幅度增加,在研發人力資源、實驗室、裝備、器材等方面的投入都大幅改進,很多企業和日本建立了合作關系。中國自身也不斷修正和調整相關政策,比如出臺有利于研發的稅收、會計方面的政策等。
未來科學技術的發展相互之間依存度依然很高,需要互相促進、共享。在生產方面,這表現為供應鏈越來越相互交叉融合在一起,這在東亞特別是中日韓之間有很多明顯的現象和例子。我相信,中日在科技、研發方面的合作仍有很大的機會。
對此,金融界應該全力支持,通過融資方面的安排、資本市場的合作、金融機構自身的科技研發和創造新的金融服務,為中日之間的合作創造更好條件。而中日間的這種合作,也是給全球現在面臨的挑戰和不確定性作出一些實例和榜樣。
推進WTO改革
眾所周知,目前國際貿易出現了不少問題,比如一些保護主義情緒、單邊主義行動等。因此,我們期待G20峰會6月底在日本大阪召開時,能有效推進WTO改革的討論,形成一些初步共識,作出重要推進,特別日本作為主席國,能在這方面起到一個主導和推動的作用。當然究竟能不能夠實現這一點,存在一些困難,外界并不是很樂觀,但確實時間已很緊迫。
G20峰會首次舉辦是在2008年,之前只是部長級會議。當年峰會集中討論如何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其中一個議題就是20國首腦希望多哈回合盡快取得進展,能夠作出結論。但實際上多哈回合談判困難重重,到現在也看不到樂觀的影子。隨后有些貿易糾紛開始出現,也變成了G20峰會的議題。在去年G20阿根廷峰會上,雖然有很多重要議題,但各國首腦都非常關注貿易糾紛,其中特別關注中美兩國首腦關于貿易方面的會談進展。
現在,WTO依然是大家關注的重點,包括WTO機制還能否繼續有效運作,WTO究竟要怎么改革。
目前WTO受到諸多挑戰,其中WTO的貿易爭端解決機制,一個重要部分是上訴機制,到今年年底就會看到,這個機制實際上已經不可能正常工作了。此外,還有國際貿易中出現的一些新議題,諸如數字貿易等,亟待得到很好的解決,但按照現在的規則制定程序,能否制定出新的規則,顯然也不樂觀。
關于WTO改革,國際上研究不少,中國的態度明確,就是堅決支持全球自由貿易和投資便利化的體制,支持多邊主義,支持WTO的工作,也支持WTO改革。討論中也聽到對中國有一些批評,就是可能有些貿易方面開放程度不高,一些做法可能跟國際上有一定差距,其中包括補貼的透明度、國有企業、網絡空間的治理、技術轉讓、知識產權保護等問題。
面對貿易摩擦和外部的批評,中國已經決心并且部署改革,在若干個方面做了準備。即便在別人對中國采取一些保護主義措施時,我們也不會用“關門”的辦法來應對,而是要進一步擴大開放,比如最近公布的金融業進一步開放的12條新措施,中方將會專門對12條新措施給出解釋。總之,中國現在要把過去外資金融機構的設立及業務范圍大幅度地放寬擴大,強調國民待遇,消除市場準入和業務方面過去所存在的一些限制。另外在技術轉讓知識產權保護方面,也有很大的決心向前推進,并達到國際上可接受的標準。
利用G20的時機推動WTO改革很有必要性。與此同時,也需要做些準備,如果WTO改革不順利,在一段時間內出現WTO的弱化,甚至是不怎么太起作用的狀況時,全球多邊主義、全球貿易制度也不應出現空白。在這種情況下,有可能出現一個局面,一些主張自由貿易的國家,可能用諸邊主義(Plurilateralism)的做法率先向前推進,讓自由貿易、貿易投資便利化的規則在局部地區先行推進。這實際上是一種多邊主義的替代性的推進渠道,最終當然還是要走向全球的多邊框架的構建。
此文根據周小川5月27日在日本東京出席“全球增長動力:亞洲貿易、投資、金融合作圓桌會”、東京“博鰲WTO座談會”上的講話整理。前述圓桌會由博鰲亞洲論壇研究院、日本智庫亞太倡議(Asia Pacific Initiative)理事會與財新傳媒聯合舉辦。(完)
(本文作者系中國金融學會會長,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
文章來源:《財新周刊》2019年6月3日(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