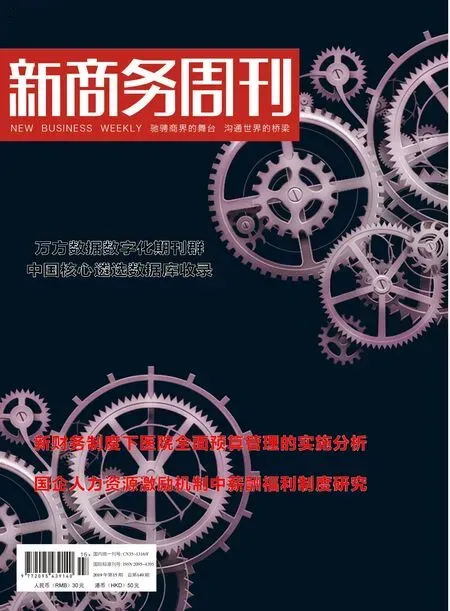淺析利己主義、利他主義與其合理性
文/陳鏡羽,中央民族大學(xué)經(jīng)濟學(xué)院
達爾文自然選擇中的選擇單位是單一有機體,在此基礎(chǔ)上,利他主體或者說為了他人利益而犧牲自己的個體,將在自然選擇中被淘汰,或者將被“自私”的個體所取代。然而“利他主義”的例子在自然界中卻能夠持續(xù)存在,這是一個值得被深思的問題。
1 生物學(xué)中的利他主義
所謂利他主義,就是特定個體在具體的時間和空間條件下,通過犧牲自己的適應(yīng)性的方式增加、促進和提高另一個個體適應(yīng)性的表現(xiàn)。在達爾文進化論中,他認為自然選擇機制的選擇單位應(yīng)該是單一的有機體,因此,利他主義是不會存在的。然而,類似于蟻群、蜂巢等,個體生物自我犧牲的行為似乎充滿了整個生物界。在現(xiàn)實生物界的基礎(chǔ)上,韋恩-愛德華茲指出,螞蟻與蜜蜂等動物的行為,雖然對它們個體的適應(yīng)不利,但是,因為這種做法促進了所在的群體的成功復(fù)制,所以,也有利于自己的復(fù)制成功。即由利他主義的個體所組成的群體比由“自私個體”組成的群體做的要更好。綜上,溫尼-愛德華茲提出了群體選擇的概念:自然選擇以個體為單位發(fā)揮作用,但是作為競爭單位的卻是群體,所以,結(jié)果最適應(yīng)的群體得以生存。
但是另一些生物學(xué)家則認為,基于個體選擇一樣能夠解釋利他主義。更為著名的是漢密爾頓關(guān)于血緣選擇的概念,這個概念意味著個體傾向于努力幫助他們的親人,直到與他們的遺傳相關(guān)性成正比。父母在有性復(fù)制上各享有他們的后代一半的基因,所以個人適應(yīng)被親屬的加權(quán)適應(yīng)所修正。權(quán)重的確定則通過它們彼此的遺傳相關(guān)性的程度來進行解釋。簡單的說,就是血緣關(guān)系親密的個體之所以有強烈的互助互依和利他的行為傾向,因為它們擁有共同的基因,所以拯救相同或相似的基因就是在拯救它們自己。為了證明明顯的利他行為是由自私的有機體帶來的,特里沃斯提出了相互利他主義概念。這一概念的本質(zhì)意義是當一個人對他人友好時,是期望將來被一些相互的善意報答的,目的完全是為了獲取遠期更大的收益,因此這種暫時降低個體自身適應(yīng)能力的行為,顯然可以被看作是利他的自利行為。
2 經(jīng)濟學(xué)中的利他主義
追求財富、或者說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從古典經(jīng)濟學(xué)到當代經(jīng)濟學(xué)理性人的主流觀點。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系統(tǒng)地闡述了“經(jīng)濟人”的合理性,如果將一個人設(shè)想為一個有機體,將和自然界存在類似的假設(shè),那就是利他主義、利他行為將會被自私行為所取代。然而,另一些經(jīng)濟學(xué)家認為,利他的個人在這樣一個殘酷的物質(zhì)世界是具有存在的理性的。
2.1 壞小孩定理
自利行為是個體在約束條件下滿足他自己的利己偏好的最大化行為;利他行為,是個體在約束條件下滿足他自己的利他偏好的最大化行為。因此,無論行為人的利己行為還是利他行為,都源自于唯一不變的利己動機。貝克爾采用了個體理性的傳統(tǒng)經(jīng)濟學(xué)概念。假定為理性的行為者在有限的資源約束下最大化其效用函數(shù),作為經(jīng)濟因素,最大化自身的效用。利他行為是經(jīng)濟人在約束條件下滿足自己的利他偏好的最大化行為。幫助利己主義者i的利他主義者b的效用,被假定為b的消費函數(shù)并且是i的消費函數(shù)。同樣,b的有限資源,即“基本”預(yù)算約束,被視為社會收入。社會收入不僅包括b自己的收入,還包括i的收入對b的價值組成。這種情況下,如果b可以沒有任何貨幣損失的向i轉(zhuǎn)移貨幣,那么當b向i進行轉(zhuǎn)賬,從而是b自己消費的微小變化與i消費的微小改變有相同的邊際效用時,即達到了b夠效用最大化的均衡狀態(tài)。由此,貝克爾得出了壞小孩定理。事實上,自利的壞小孩i可能被利他主義的父親b所影響,仿佛i也是無私的。因為從i自己的利益出發(fā),可以預(yù)期到b傾向于以這樣的方式轉(zhuǎn)移,以至于b的處境也得到改善。而這一做法不僅增加了b的“主觀效用”,而且也通過i的行為提高了b的“客觀收入”。因此,壞小孩定理被認為是包含兩個相關(guān)的結(jié)果,第一個結(jié)果與壞小孩i在預(yù)期到父親b的利他行為時表現(xiàn)有關(guān),作為雙方理性預(yù)期的結(jié)果,兩個人都最大化了他們的效用函數(shù)。第二個結(jié)果與利他主義的父親獲得的“客觀”利益有關(guān)。基于這個結(jié)果,貝克爾認為,利他傾向有利于具有這種傾向的個人適應(yīng),即便與他們打交道的是具有利己主義傾向的人。利他主義在與利己主義者并存的群體都具有生存的價值。
然而,針對于貝克爾的論斷,赫什萊佛認為,只有當“大父親”b有決定權(quán)時,即b可以決定如何分配時,壞小孩i才會被勸說而進行合作。壞小孩與父親采取的行動效應(yīng)不僅依賴于他們自己的行動,且依賴于他人采取的行動。作為博弈者,小孩和父親被假定進行一個單一博弈,并假定依次做出決定,先小孩后父親。在這個連續(xù)的決策中,孩子將會考慮父親的反應(yīng),表現(xiàn)他的無私。但是這種合作行為并不能證實利他主義的傾向。而這恰好反應(yīng)了一個問題“實際的行為總是代表兩種決定因素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偏好,另一方面是機會(約束)”。但是赫什萊佛遺漏了第三個共同決定因素:信念。即為了能夠得出貝克爾的定理結(jié)論,小孩不僅要首先行動,而且要能夠正確的判斷出父親的反應(yīng)。而這意味著貝克爾和赫什萊佛都默認了一個前提,就是小孩對父親利他主義的信念(或者是對父親決策的預(yù)期)是正確的。貝克爾和赫什萊佛簡潔的分析了相互作用的“機制”是一個標準的經(jīng)濟學(xué)機制。而自然選擇的演化機制在這其中也是存在的,它決定了利他傾向能夠生存。
2.2 囚徒困境
赫什萊佛提出了自己綱領(lǐng)性的論點:“偏好模式”,即那些看似隨意的模式,也會因為它們大體能夠適應(yīng)環(huán)境條件而生存下來。赫什萊佛應(yīng)用博弈論分析了在實施威脅與承諾時的仁慈、惡意、憤怒與慷慨等情感的“適應(yīng)”函數(shù)。以囚徒困境為例:

表1 -1PD博弈
如表1-1,當囚徒在抉擇時,如果只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優(yōu),而不顧及別人的情況,這時的均衡就是(坦白,坦白),最終結(jié)果對每個人都不利。而在這個博弈過程中,對于由A和B構(gòu)成的囚徒群體而言,最優(yōu)的選擇就是(抵賴,抵賴)。在現(xiàn)實世界中,存在各種情況和可能性,如決策者的理性水平不高,信息的不完全掌握等等。因此,在實際決策中,出現(xiàn)偏離最優(yōu)均衡的情況是非常普遍的。
假設(shè)一個“利他主義”個人i給予他自己的支付(Pi)的權(quán)數(shù)為(1-v),給予另一個人的支付(Pj)的權(quán)數(shù)為v。因此,一個“利他主義”行為人將最大化自己的效用Ui。則對于利他主義的行為人而言,其效用Ui應(yīng)該有這樣的等式:Ui=Pi*(1-v)+Pj*v。如果v=0,這意味著個人i是只關(guān)心自己的支付的利己主義者,忽視其行動對其他人的影響,因而采取的是“不合作”的行為。如果v=1,則意味著他是一個完美的利他主義者。給定這一博弈對合作或背叛的支付,這個利他主義者將采取合作行為假若他的利他主義程度(v)足夠強的話(只需1/2≤v〈1)。如果每個參與者都是這樣的利他主義者,他們將以與囚徒困境博弈的合作解決方案一致的方式行事。此外,如果能確保另一個人也將合作,那么,合作要求的利他水平可能會較低。如果將上文所提到的信念作為一個人賦予另一個人實際上采取合作行為的一種主觀概率,很明顯,這個利他主義者對合作的主觀概率估計值(π)越高;利他主義者采取合作行為所要求的利他主義(v)就越低。也就是說,可以把π和v視為負相關(guān)。最后,如果兩個參與者對彼此的信念很強或者是完全相信對方,那么,相互合作就會作為他們的一種超優(yōu)策略。顯然,如果博弈者是利他主義者,則“囚徒困境”類型的博弈就可以獲得一個“群體理性”的結(jié)果。
2.3 社會資本的推論
無論是個體選擇意義上的遺傳頻率最大化還是群體選擇意義上的種群生存適應(yīng)性改善,都可以為利他行為提供一定的生物學(xué)解釋。從經(jīng)濟角度來看,當個體由于血緣、居住或工作等原因,被組合到一個或多個群體之后,社會交互行為除簡單的利益最大理性外,還產(chǎn)生了另一種行動的邏輯理性,即尋求共同體生活和被認同的需要。滿足這種需要同樣被認為是增進個人效用的。有學(xué)者認為,提供這種效用的要素則是個體行為在群體中獲得的“信任狀”,或者被稱為社會資本,個體通過社會資本獲取認同,以及動用更多資源、節(jié)省成本的途徑。
基于這樣的社會資本,則無論是親緣利他、互惠利他還是純粹利他,都可以統(tǒng)一到獲取社會資本的目的。也就是說,社會資本可以帶來效用,但需要利他行為在內(nèi)部來建構(gòu)這樣的社會資本。同時,利他行為的實施必然導(dǎo)致個體適應(yīng)性降低和成本支出。當群體內(nèi)創(chuàng)生的有效率的利他行為過少,可動員的總的社會資本總量不足,無法滿足生物存續(xù)和社會存續(xù)的需要時,以及維護利他行為及其復(fù)制的強度不足,導(dǎo)致機會主義泛濫時,群體成員將會選擇退出。加入其他群體可能獲得更多的生存所需要的社會資本,因此就選擇退出該群體,那么群體就可能遭到瓦解,或者說在競爭中被淘汰而消亡了。為了保證群體的持續(xù)存在,就需要一種均衡制度(稅收),使得群體中的每個個體能夠獲得有效的社會資本。而動態(tài)的外部環(huán)境的競爭性是推動群體制度演化的外部動力。
3 結(jié)論
對于什么是選擇單位一直都有不同的意見。那些相信群體選擇的人傾向于認為群體演化將會表現(xiàn)出最優(yōu)的群體行為;個體選擇學(xué)家則認為,最優(yōu)的群體行為可以(但不一定)必然作用于個體有機體的選擇中產(chǎn)生,最優(yōu)的群體行為完全依賴于選擇機制運行的特定條件。在以群體作為選擇單位的前提下,當每個人都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時,對整個社會而言卻是一種資源配置缺乏效率的狀況。引入群體作為選擇的單位使得利他主義逐漸符合“經(jīng)濟人”的假設(shè),因為長期看來個人利益將隨著群體利益的提高而得到更大的改善。在這種條件下,合作的“利他”主義行為是最適應(yīng)的策略;在其他條件下,在由合作者組成的群體中“搭便車”可能是一種比“合作”是更適應(yīng)的策略。面對外部競爭,通常包括了一些沖突元素,而這些沖突元素往往存在于更高的層次組織,比如群體或者是物種間,,由于這個原因,群體內(nèi)的個體的選擇是不能被忽略的。但是在個體有機體的層次上,沖突是缺乏的,這是使個體有機體從根本上不同于更高層次的組織的原因。
在經(jīng)濟學(xué)中,我們擁有的不是兩個而是三個的組織層次:個人、企業(yè)(家庭)和產(chǎn)業(yè)[7]。在每個級別中,整體與部分之間都存在著不同的聯(lián)系。作為最高層次的產(chǎn)業(yè)部分—企業(yè),為市場份額而相互競爭,他們的利益相互沖突。而在低一級的層次中,即企業(yè)層次的部分—個體企業(yè)成員,可以說是牽涉了HD類型的混合動機博弈(或合作博弈),存在著卸責(zé)、“搭便車”與“道德風(fēng)險”的機會,這里的個體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相互沖突的,而在這種沖突下,很有可能會產(chǎn)生次優(yōu)結(jié)果。在最低的個體層次,作為部分的器官,不能說與作為整體的有機體有不同的利益,器官的行為或器官間的分工組合是不可持續(xù)的,除非它們增加了有機體的差別性復(fù)制成功。使有機體與更高層次的組織不同的根本原因是有機體的利益可以被視為與其部分的利益是相一致的。在更高的整合水平上,缺少這種在統(tǒng)合性整體與部分之間利益的認知。
從理性的前提出發(fā),追求總體利益最優(yōu)化的人類在大范圍的空間和大尺度的時間內(nèi)的利益博弈中,如何選擇自己的行為,最終取決于利益需要。由于不管對博奕的各方,利他主義都有著巨大的潛在利益和現(xiàn)實利益的誘因,所以,利己的人類追求利他也就成了一種必然。既然利他主義是人類追求自身利益的需要,所以,人類社會在發(fā)展過程中,必然會采取種種措施,強化人們的利他主義行為,而這可能就是構(gòu)成制度演化的最基本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