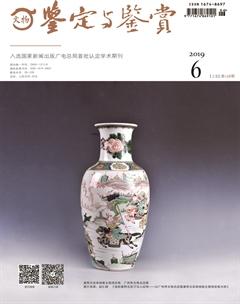出土文獻對研究古史的作用
惠丹陽 李明
摘 要:出土文獻對研究古史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近些年簡牘資料的出土,更直接體現了出土文獻證、正、補傳世文獻的價值,使一些撲朔迷離的歷史事件有了更多的可能性的解釋,為學者的研究開創了新的領域。文章通過對比《編年記》與《史記》的相關紀年,管窺出土文獻對古史研究的作用。
關鍵詞:《編年記》;《史記》;出土文獻的作用
近年來全國各地出土了大量簡牘,這些簡牘早至戰國,晚到魏晉,數量龐大,內容真實豐富,面向基層,為研究古史提供了極其寶貴的資料。1975年云夢睡虎地秦簡的發掘出土,是秦簡的首次發現,對研究傳世文獻極為貧乏的戰國末至秦朝時期歷史具有十分珍貴的史料價值。其中《編年記》逐年記述了秦昭王元年到秦始皇三十年統一六國的戰爭大事,它的紀年與記事,可以證、正、補《史記》的相關記載。
1 印證《史記》
《編年記》:“四年,攻封陵。”[1]①在此年,《魏世家》《六國年表》都載有“秦拔我蒲坂、晉陽、封陵”[2],雖《編年記》只寫有攻封陵一邑,卻能證明這段史實的真實性。
《編年記》:“五年,歸蒲反。”這與《秦本紀》記載的“五年,魏王來朝應亭,復與魏蒲阪”、《魏世家》記載的“十七年,與秦會臨晉,秦予我蒲反”以及《六國年表》記載的“復(歸)我蒲坂”相吻合,且“歸蒲反”也證實了秦昭王四年攻取魏蒲反這一史實。
《編年記》:“九年,攻析。”《秦本紀》和《六國年表》無此記載,《楚世家》在此年記有“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可與《編年記》對應,說明《楚世家》記載的可靠性。
《編年記》:“十六年,攻宛。”《六國年表·韓》記十六年“秦拔我宛城”,《韓世家》亦載此年“秦拔我宛”,兩者可與《編年記》相印證。而《秦本紀》記十五年“攻楚,取宛”,《穰侯列傳》記十五年“又取楚之宛、葉”,楊寬認為《秦本紀》和《穰侯列傳》屬記載錯誤[3]。筆者認為,攻韓之宛都在昭王十六年,而在昭王十五年攻的宛都于楚,或宛是韓、楚地名相同的不同地方,秦攻打兩地的年份正如史書所記,相差一年。
《編年記》還有很多與《史記》可相印證的,此處不再一一列舉。
2 糾正《史記》
《編年記》:“十七年,攻垣、枳。”《秦本紀》載:“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復予之。”“十八年,錯攻垣、河雍,決橋取之。”即秦在昭王十五年攻取垣之后把垣還給了魏,又在十八年攻取垣。《秦本紀》載:“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鄧。”《六國年表》載十八年“客卿錯擊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攻枳的時間兩處記載都不同,而《編年記》的這一記載可以糾正史書記載的錯誤:秦在歸還垣之后,在昭王十七年攻垣、枳。
《編年記》:“二十七年,攻鄧。”《秦本紀》載:“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鄧,赦罪人遷之。”《白起列傳》載昭王二十八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史書記載時間與《編年記》不同,應以《編年記》為準,攻鄧時間應為昭王二十七年,或者開始攻鄧時間為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攻取。
《編年記》:“三十三年,攻蔡、中陽。”《六國表·魏》和《魏世家》都載此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但《秦本紀》和《穰侯列傳》僅記取魏卷、蔡陽、長社,尚缺一城,疑“蔡陽”當系“蔡、中陽”之誤[4]。如此,《編年記》可以糾正史書“蔡陽”之誤。
《編年記》:“三十四年,攻華陽。”《六國年表·秦》載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擊魏華陽軍,芒卯走,得三晉將,斬首十五萬”。《秦本紀》載昭王三十三年“擊芒卯華陽,破之,斬首十五萬”。《周本紀》載“秦昭王三十三年,秦背魏約,使客卿胡傷擊魏將芒卯華陽,破之”。《六國年表》和《秦本紀》《周本紀》記載此事件年份不同,而《編年記》可明確秦攻華陽在昭王三十四年。
《編年記》:“三十八年,閼與。”趙破秦于閼與,《趙世家》《六國年表》《廉頗藺相如傳》均列于趙惠王二十九年,即秦昭王三十七年,惟《秦本紀》在昭王三十八年。考秦簡《編年記》亦在三十八年,當以《秦本紀》為是[3]915-916。如此,《編年記》則糾正了《趙世家》《六國年表》《廉頗藺相如傳》里的紀年錯誤。
《編年記》:“三十九年,攻懷。”《六國年表·魏》載昭王三十九年“秦拔我懷城”。《魏世家》載“九年,秦拔我懷”,即亦記昭王三十九年秦拔懷城。而《秦本紀》卻記“四十一年夏,攻魏,取邢丘、懷”。《編年記》的這一記載可明確秦攻懷在三十九年,《秦本紀》記載錯誤。
《編年記》:“四十八年,攻武安。”《秦本紀》:“四十八年十月……王齕將伐趙(武安)皮牢,拔之。”“武安”原意為衍文,而《編年記》明確記錄昭王四十八年秦攻武安,這可以確定《秦本紀》里“武安”并不是衍文,而是確實存在。
《編年記》:“三年,莊王死。”《秦本紀》載莊王四年,五月丙午,莊襄王卒。張文虎曰“莊襄王無四年,《六國年表》書在三年。此四年二字,涉上文四月而衍”。按之《編年記》,足證《編年記》之“四年”為衍文[5]。
3 補充《史記》
《編年記》:“六年,攻新城。七年,新城陷。八年,新城歸。”《秦本紀》記“七年,拔新城”,這與《編年記》“七年,新城陷”是一致的。而史書卻沒有記載“六年攻新城,八年新城歸”這一史實,據“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秦確實曾將新城歸還于韓,應是史書漏載。
《編年記》:“十三年,攻伊闕。十四年,伊闕。”眾學者認為“伊闕”應為“伊闕陷”,簡文后當脫“陷”字。《秦本紀》:“十四年,左更白起攻韓、魏于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公孫喜,拔五城。”《六國年表》在昭王十四年記“白起擊伊闕,斬首二十四萬”“佐韓擊秦,秦敗我伊闕”“秦敗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將喜”。《史記》只記有十四年秦軍大勝于伊闕,沒有十三年攻伊闕的相關記載,由此,《編年記》可補充這點。
《編年記》:“廿年,攻安邑。”此年,史書沒有攻安邑的記載,卻有二十一年獻安邑的記載。《秦本紀》:“二十一年,錯攻魏河內。魏獻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東賜爵,赦罪人遷之。”《六國年表》:“魏納安邑及河內。”韓連琪認為大概是二十年攻安邑,二十一年獻安邑,較為中肯[5]131。
《編年記》:“三十二年,攻啟封。”《漢書·景紀》注引荀悅曰“諱啟之字為開”,疑開封在漢以前本名啟封,漢人諱景帝名啟,故改為開[6]。若此,《六國年表·韓》所載昭王三十二年“暴鳶救魏,為秦所敗,走開封”中的“開封”當為啟封,則在此年,暴鳶亡走開封后,秦又進攻開封。由此,《編年記》所載“三十二年,攻啟封”,既可與史書印證,又補充史書內容。
《編年記》:“五十二年,王稽、張祿死。”張祿,即范雎,《編年記》明確記載范雎的死亡時間,為《史記》所無,為研究范雎死因及與之相關的秦朝政策提供了很重要的線索。
4 產生更多可能性
《編年記》:“二年,攻皮氏。”而《魏表》“秦擊皮氏,未拔而解”以及《樗里子甘茂列傳》“還擊皮氏,皮氏未降,又去”,都是在昭王元年,《魏世家》“秦來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則在魏哀王十二年,更早一年。黃盛璋認為《魏世家》比《魏表》早一年是因為《魏表》按秦歷法安排,當時各國歷法不統一[7],這種說法是有說服力的。而對于攻皮氏《編年記》與《史記》記載年份的不同,一些學者們提出這樣的解釋:攻皮氏事發于元年而解于二年。但筆者認為,這仍然不能排除傳世文獻記載錯誤的可能性。
《編年記》:“十八年,攻蒲反。”《六國年表·秦》載十八年“客卿錯擊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表·魏》載“秦擊我,取城大小六十一”,而蒲反剛好是魏地。有學者便認為蒲反應是這六十一城中的一城[7]4。但上文已證明秦攻枳時間應在十七年,即“取城大小六十一”應在昭王十七年,而非十八年,所以十八年所攻的蒲反應當不在這六十一城中。筆者猜測或是秦對魏的戰爭在十八年繼續,攻魏蒲反。
5 小結
通過《編年記》與《史記》的相關紀年比較,我們可以直觀地感受到出土文獻對傳世文獻證、正、補的作用,并且為不確定史實提供更多的可能性,能幫助我們理解、認識傳統書籍的制度。認真研習出土文獻并結合傳統書籍,甚至可以勾勒出某個時代的某種社會制度和框架。如若我們結合出土文獻研究古史,定可以開出創新的領域,有更多新的發現。
參考文獻
[1]陳偉.秦簡牘合集·睡虎地簡牘[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
[2](西漢)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2.
[3]楊寬.戰國史料編年輯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724.
[4]陳偉.秦簡牘合集·睡虎地簡牘[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18.
[5]韓連琪.睡虎地秦簡《編年記》考證[M]//中華文史論叢(第1輯).北京:中華書局,1981:142.
[6]馬非百.云夢秦簡大事記集傳[M]//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第二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73.
[7]黃盛璋.云夢秦簡《編年記》初步研究[J].考古學報,197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