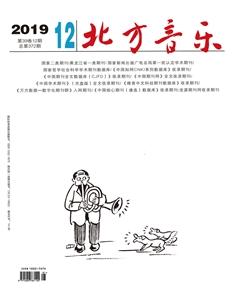信仰之舉
【摘要】《大漢蘇武》通過歌劇這一體裁講述中國古代的故事,表達著中國的情懷,傳遞著幾千余年藏于人們心中的思鄉之情與愛國之義。本文從音樂聆聽的角度分析歌劇音樂的情感力量與精神力量,同時探討《大漢蘇武》在思想、藝術、市場中取得成功的關鍵原因。
【關鍵詞】歌劇;大漢蘇武;音樂評論
【中圖分類號】I233?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大漠無邊起霧煙,身陷異國墜深淵。
忠心耿耿因情重,鴻雁翩翩盼夢圓。
雪裹羔羊尋野草,風吹蓬帳弄琴弦。
一朝榮返發須皓,千載英名綴史篇。
現仍巡演的歌劇《大漢蘇武》從上演至今,獲得國家藝術基金資助項目等多項殊榮,主創團隊包括導演陳蔚,劇作家黨小黃、作曲家郝維亞、指揮馮學忠等創作精英。作為陜西省歌舞劇院“漢代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其貢獻必然會成為中國歌劇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其深遠意義也將載入史冊。《大漢蘇武》以漢元年“蘇武牧羊”這一歷史事跡為載體。中國古代故事離現在很遠,轉頭千載春,斷腸幾輩人。反映了古代義士的浩然正氣,通過音樂與戲劇的平衡,凸顯出蘇武身上鮮活存在的愛國信仰,以及為之灼灼燃燒的生命。敘事藝術往往是令人心動的,其捕捉到了時代大潮中個體人物的命運和悲情。筆者曾有幸于2014年11月11日在武漢舉辦的中國歌劇節中觀看到此劇,當初觀看后感動于大國大義大情,現在回想起來仍記得其磅礴之勢。
一、孤寂的牧羊者
蘇武是大國忠臣,但也是孤寂的牧羊者。全劇中蘇武(扮演者:米東風)的出場總是伴隨著淡淡的笛音,吹奏出他坎坷一生的淡淡清愁,但銅管樂總是適時出現,展示著蘇武永不放棄的決心。
第一幕:樂聲奏響,和平使者。匈奴再次舉兵來襲,蘇武與李陵(扮演者:張海慶)為出兵之事各抒己見,堅持用言語感化匈奴的蘇武是孤獨的,在弦樂柔緩短弓的伴奏下,木管組哀愁的旋律似句句勸說,在蘇武請愿出征之時,銅管樂和弦樂的旋律性突然變強,節奏堅定有力,展示著蘇武的英雄氣概。在銅管樂與弦樂交替出現的故鄉旋律中,蘇武來到匈奴的領域,盡最大的努力傳遞著和平休戰的愿望。但因副將劫持國太,蘇武被扣押,他跪倒在地,旋律從銅管樂的咄咄逼人走向平穩的不和諧音進行,鏗鏘有力的清唱是蘇武立證大漢真善的吶喊。
第二幕:被流放的牧羊者。木管組后附點的節奏型,以及向下進行的不協和音程的使用,營造出地牢陰暗的環境,蘇武的唱段是悲憤的,是級進迂回進行的小調旋律,在他倒下前刻,旋律轉向大調,三連音的節奏型帶來動力性,這是蘇武扎根心中的信念的涌現。無論是面對單于的威逼利誘,還是回望故鄉時的孤寂,又或是李陵帶來悲痛噩耗之時,蘇武始終堅定的心懷對故鄉、親人、國家的情感。蘇武是遠航的孤舟,流浪在蒼茫的霧海之中,他的心始終找不到停泊的港灣。他在孤立無緣之時,思念故鄉,感受著草原的遼闊清寒與知交半零落的悵然。
第三幕,做愛情的離人。愛情是情感中的永恒命題,它總能在不同時空的境遇中獲得新的意義。情感的沖突在蘇武與索仁娜(扮演者:周曉琳)的重唱中得以爆發。二人從初識到離別,四季略過,了結情緣,是牽掛,是愛情。分別之刻的重唱,將痛心與不舍渲染全場,是深情的旋律,是不舍相望的眼眸,是緊緊相擁與緩緩松開,是無力的落淚與將離的無奈,愛情主題變慢、變緩、變重、變厚,直至徹底離別。蘇武與索仁娜的合唱、對唱,其音樂已不止于感人,更多的是撩人心魄,具備了一個愛情故事所應具備的一切。這是草原的愛情,十九個冬春,他和佳人被迫分離,是不舍的感傷,卻又是無可奈何。蘇武回到長安,這段歷經滄桑的世情讓他早已醒透,這段匈奴往事,也只能在心中情系,那忽略的情,擱淺的緣,終究只能到老來懷念。樂聲、人聲,動情之時,最能觸動人心。蘇武在流年中行走,看著光陰逝去,來者已來,不可抗拒,去者已去,無法挽留,但他,無論在哪段年華中,都是孑然一身。
二、政治沖突與情感對立
精神力量在歌劇中不斷被強調,政治責任與個人情感的沖突、對峙正是這部正歌劇的一大亮點。本劇的政治沖突體現在男高音蘇武和男中音李陵一次次的音樂碰撞之中,全面、客觀地刻畫與表達歷史人物的人性特征,其矛盾指向的是二者心中的愛國情懷和道德堅持,是堅持愛國,還是背棄恩德,如何抉擇,可從其音樂矛盾變化中窺見一斑。蘇武與李陵在大漢之時,交響樂隊振聾發聵,管弦樂震震作響,營造出莊嚴、厚重的政治性氣氛,其旋律音調是激昂向上的,體現著大國威嚴與堅定信念。在匈奴叛亂這一事件的處理上,二者的理念相違背,音響的強烈碰撞,讓人無法不注意到蘇武強大的精神世界,以及其俠膽英魂。蘇武的每一次出場,從振奮到哀痛,再到面對匈奴誘惑、李陵勸說時的不屈,音響也從整個樂隊奏響,到單薄的銅管樂發聲,是蘇武沉重的內心,不屈的精神,單薄的身體,仍支撐著他強大的愛國之心。面對李陵的降服,銅管樂與打擊樂器相繼奏響,節奏越發密集,描摹的是蘇武悲憤交加的內心與壓得喘不過氣來的身體。最終在李陵自刎后,蘇武的心中充滿的是對故人矛盾的心情。在合唱隊的伴襯下,一個五度音程的長音,是蘇武的吶喊,是對這突如其來的分別的痛心與不舍。
在整部歌劇中,無論是在鼎盛之時,還是在亂世之間,銅管樂厚重的音響始終代表著蘇武堅毅的形象,每一次的出現,音程、旋律、節奏都隨著情緒上下起伏,展示著他錚錚鐵骨的一面,也展示著他溫暖柔情的一面。這是一部關于壓迫、痛苦、犧牲、勇氣引人入勝的戲劇,整部作品在政治上也符合潮流,與其說這是一個歷史故事,不如說這是作曲家譜寫的內在道德樂章。蘇武是中國西漢時期國格的倡導者和實踐者,他所具備的愛國情懷、忠勇品質,無一不體現了中華民族千百年來所形成的偉大民族精神和時代特征,而這些精神,我們可以從音樂中聽出來。文字是靜止的故事,而音樂則是流動的故事,我們可以在音樂中感受蘇武的情感、思想,可以學習他堅忍的道德情操。
歌劇,從聽覺到視覺,無一不沖擊、占據著現場觀眾的心。全劇通過對蘇武堅守祖國忠誠,以及個人命運的跌宕,折射出國家之義和時代的曲折,將個人命運和國家命運緊緊地聯系在一起,無論是經歷家庭的悲苦傷痛,還是敵人的質問凌辱,蘇武都堅定地選擇了對家國的忠誠。這是藝術創作中“人性”的體現,是在矛盾沖突中不斷深化的情與義,是人在特殊情境下的升華與隕落,是這部作品的要義與要旨所在。
三、“實”“意”相融
當代化意識與國際化面貌是歌劇在思想、藝術、市場中取得成功的關鍵。國際化視野下創作出的中國歌劇已經不再止步于對西方歌劇形式的模仿,而是熟練地運用西方歌劇的框架與范式,將中國元素及精神合理運用其中。其一,較之早期的中國歌劇創作,作曲家郝維亞先生在劇中并非刻意使用中國音樂元素,而是對劇中人物的命運和內心有了深切的思考之后,因故事情節的表達需要而合理地使用劇情所需的音樂元素,如開篇的塤,氤氳氣氛將思緒瞬間拉回至漢代,抑或是中國打擊樂器與吹管樂器對蘇武思鄉情感連續的描繪。這一點較之前人,是當代作曲家音樂創作思想理念的轉變,從有意為之到按需所取,中國歌劇在不斷完善。其二,傳統歌劇中的情節是在矛盾的出現與解決中推進,而《大漢蘇武》則是將矛盾一一呈現,“國家主題”“苦難主題”“愛情主題”相繼發問,直至結束才得以解決,這不同以往的創作思路,使得該劇的音樂極具動力性。其三,如歌旋律至上的音樂創作思維也在悄然發生改變,“愛情主題”中的獨唱、合唱、重唱是該劇優美詠嘆調的集中體現,但女高音索仁娜這一角色僅僅是作曲家為了平衡歌劇聲部而創作的支線情節,并非全劇的主線,而為蘇武創作的詠嘆調《干渴像刀子一樣割裂著我的喉嚨》《我老了》等,觀眾聽到的是苦難,而非優美,從中可窺見表達本身比“好聽”更為現代作曲家所重視。其四,該劇的過渡性場面也極具情感,作曲家在唱段的連接處設置充分施展音樂力量的完整旋律,既有分隔之意,又巧妙進入下一場景。《大漢蘇武》作為一個交響樂般的三幕大歌劇,以中國地道而豐富的“歌劇式”音樂展開情節,在音樂語言的運用中,作曲家以交響化的器樂思維和純熟的配器手法,出色地將全劇主要音樂主題和風格意蘊展示。
《大漢蘇武》是具有國際化面貌和中國風骨的歌劇,是西方歌劇“寫實”與中國戲曲“寫意”相融的體現,觀眾可在綜合藝術的演繹中發現中國藝術的古樸之韻。
四、感慨唏噓中的《大漢蘇武》
意猶未盡,信仰之舉,感慨唏噓。行筆至此,應該談談此劇的遺憾之處。毋庸諱言,《大漢蘇武》戲劇感較弱,或許定音鼓、銅管樂的減少,權衡管弦樂之間的平衡,則可以體現更為流暢的戲劇感。此外,大篇幅太過直白的宣敘調鋪陳,使得整部作品沉重,第一幕較多的使用宣敘調,因此一開始則稍顯煩悶。因為宣敘調的寫作總是不如詠嘆調、重唱、合唱等唱段那樣自然與妥帖。相比較抒情部分的優美、流暢,音樂在表達戲劇性緊張、力度較強的時刻往往稍顯不足。作曲家郝維亞說,該劇傳達的精神力量是對故鄉的依戀,而筆者卻在觀劇后感受到濃厚的愛國熱情。作曲家雖本無意強調愛國之情,但思念故鄉也是愛國之情的一種體現方式,或許愛國作為精神依靠,可以更好地感受時代的號召,更為精準地觸及國人心中深藏的愛國情懷。愛國在中國歷朝歷代都是十分重要的,于當今,它也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體現。從舞臺呈現看,主要布景實物都做了刻意的變形處理,既有歷史感,也暗含豐富的象征寓意,但由于布景(符節、山)體積較小,空間感主要靠燈光營造,視覺上感覺太“少”。此外,舞臺服裝夸張過度的設計,是與劇情不符合的,這也是讓人游離于戲劇邊緣的重要原因。中國的歌劇發展一直都是大家十分關注的話題,其發展所面臨的困難也是不容忽視的。
《大漢蘇武》在第二屆中國歌劇節中榮獲優秀劇目獎,其實力不容小覷,其創排也可謂是一次難能可貴的嘗試,通過歌劇講述中國古代故事,傳達幾千余年藏于人們心中的愛國熱情,穿越歷史,這是中國歌劇描述中國故事,表達中國情懷,傳遞中國風味。自20世紀初西方歌劇樣式傳入中國,至今已百年有余。這百年來,中國人在歌劇的創作、表演、制作和研究方面持續進行探索,所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但歌劇在中國發展的高度,從作品質量方面仍可見一斑。為何在《白毛女》《原野》等優秀中國歌劇劇目誕生之后,現在的中國歌劇發展,無論在藝術高度,又或是思想情懷方面,都難以在世界歌劇的舞臺上獨樹一幟。筆者以為,這可以歸咎于劇目本身的題材原因,抑或是音樂創作處理方式的問題,也可能是舞美夸張無度的原因。
作為姊妹藝術的民族舞劇是近幾年發展的熱潮,同樣作為綜合藝術形式,為何舞劇可以通過曲折彎直的肢體靈動展現形式與內容,而歌劇則舉步維艱的前行。筆者堅信,音樂足以打動人心,所以,如何在西方歌劇體裁結構下使用中國本土的音樂資源,通過歌劇這一復雜的藝術樣式展現當代中國人的生活與精神,讓蘊含東方文化靈魂的中國歌劇走向世界,筆者以為至今仍是難題,有望通過一代又一代的藝術家們的努力與研究,從而將中國歌劇帶向世界,走進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思想中。過去的經典仍留有芬芳,今日的作品,望經過時代的檢驗,成為歌劇歷史中的又一經典之作。
中國歌劇,多聆聽,多感受,多了解,多認識,去習慣歌唱音樂的情感表達方式,讓聽覺細胞慢慢觸摸樂音,才可以發現音樂的美,這是一種情感美,也是一種旋律美。中國歌劇是基于西方歌劇的基礎上發展至今的,其形式、和聲、配器都更為豐富與理想,音樂通過和聲微妙的變化,樂句的靈活性,相互碰撞、組合產生新的關聯,充分將人、事、物融入其中,音樂與戲劇的平衡必然是歌劇發展中的核心環節。作為歌劇的最高主宰者——音樂,它是戲劇、人物、設計、氣氛、精神的承載者。在歌劇這個體裁中,音樂毫無疑問是重要的,因為只有音樂才可以瞬間沖破我們理智的壁壘,震撼著我們的聽覺神經,讓我們的情感為之起伏。好的音樂,不僅僅是人情感的表現,更為重要的是其背后的人文精神內涵,它從不止于音響素材,而是對世間萬事萬物聲音的極力仿現,一部好的歌劇,它展示的是不同時代、不同民族的“形而上”與“形而下”,其中的意蘊等待知音來品味。春秋轉變幾千載,歷史被書寫著,留下了許多細碎老舊的故事,讓后人去咀嚼回想。歌劇藝術,它所指向的是人類的精神文明,它不一定會使聽眾愉悅,但你一定能強烈的感覺到作曲家所表達的思想世界,試著去聽、去看、去感受、去領略中國歌劇的美。
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可以去劇院欣賞歌劇,擦拭蒙塵的心,感受中國歌劇未來可期的多樣化形式。
參考文獻
[1]沈昕然.歌劇《大漢蘇武》中索仁娜的人物形象與演唱處理分析[D].武漢音樂學院,2018.
[2]薛皓垠.論中國歌劇人物的二度創作——析《大漢蘇武》《方志敏》中男高音角色的塑造[J].人民音樂,2018(2):34-36.
[3]張教華.歌劇《大漢蘇武》獨特的藝術氣質和思想內涵[J].中國戲劇,2016(2):52-55.
作者簡介:顏家碧(1993—),女,廣西藝術學院音樂學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