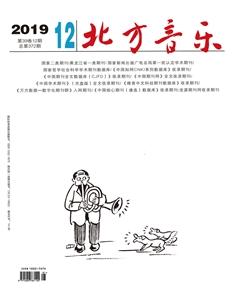電波不逝,信念永存
【摘要】舞劇《永不消逝的電波》改編自解放時期中共上海地下電臺的發報員李白的真實故事,在尊重歷史的基礎上,切合當下審美,運用當代的舞蹈語言融入海派風情。整部作品通過將舞劇的藝術風格和諜戰的緊張懸念感相融合,細致入微地對壯烈犧牲的情報英雄們進行全新的闡釋。本文旨在從舞劇本體出發,以舞劇的創作手法、創作特征與創作價值為切入點,對該舞劇的藝術特征進行全面且系統的探析。
【關鍵詞】舞劇;藝術特征
【中圖分類號】J617.2?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一、精練的舞劇創作手法
(一)骨血豐滿的人物形象塑造
藝術作品形成的過程就是創作藝術形象的過程,完整的藝術形象塑造是舞劇作品中的重要部分。換言之,舞劇創作的核心就是將思想、情感化為舞動起來的藝術形象。舞劇《永不消逝的電波》在人物設定上就有兩位主演和七位關鍵性角色,面對如此之多的人物形象以及復雜的劇情線索,考驗的是編導解構故事、鋪墊懸念以及運用舞臺的綜合能力。
從挖掘人物內心的“可舞性”出發,是編導韓真、周莉亞成功塑造出骨血豐滿的人物形象的關鍵所在。舞劇《永不消逝的電波》沒有將劇中的英雄人物神化和抽象化,而是通過身法造型鎖定人物性格,透過動態語言豐滿人物形象。如編導在塑造“李俠”與“何蘭芬”二人復雜的情感關系與神秘的多重身份時,在不同的情感糾葛中聯系著抽象的意境,通過極具隱喻性的動作與視點的切換,完成對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人物關系的建構。如舞劇尾聲在刻畫李俠大義凜然不顧生命危險去完成最后的任務時,在二人相互糾纏拉扯的啞劇化動作背后,是極具指征與隱喻性的向外掙脫的“分別之勢”。尤其是在與李俠同志訣別后,蘭芬并未用大開大合的肢體動作渲染其悲痛的內心,而是在人群中靜靜佇立,望向遠方,以表達對李俠同志逝去的不舍與敬意。編導選擇這種人物情感表達,是隱忍的、節制的。與肆意的煽情不同,在即將噴發的情緒高點上選擇控制,直抵觀者內心。
舞劇在對人物形象進行立體塑造過程中,對人物動作細節的極致把握,更是展現出兩位女編導細膩的編舞風格。舞劇中,“李俠”無論是一個簡單的回眸亦或是與“蘭芬”的對視,柔和的目光中透露出一絲沉著與堅定,通過內心的戲劇張力傳達出人物形象信息。如舞劇在呈現李俠與蘭芬二人進行重要信息交接的場景時,編導穿插了最直接的啞劇動作——讓二人交接的兩只手在定格中成為視覺焦點,從而在不經意間給觀眾營造一種戲劇的張力。
(二)多重語意的舞臺空間營造
一部作品的整體結構,在處理雙重時空關系時,要在有限的物理時間中盡可能涵蓋更大的空間內容,在盡可能地給觀賞者以較多的審美信息的同時留給觀眾自由想象的空間。通過多重語境的舞臺空間營造,豐富舞劇的敘事手法,是舞劇《永不消逝的電波》創作手法的一大亮點。舞劇中,編導多次采用“空間敘事”的運用,與電影中特殊的敘事手法如倒敘、插敘、平行蒙太奇相結合,展現人物形象內心情感的變化,創造出一種全新的敘事邏輯。在李俠、蘭芬追憶往事的雙人舞段中,編導采用跨時空的敘事手法,通過視點的轉換,交替呈現出四對“雙人舞”,通過現實與回憶的交叉渲染二人革命信念的可貴。舞臺前區的一對代表著當下,而另外三對則是代表不同時空場景下的三個階段,從二人初識到相愛,再到共同投身于革命事業,一幀幀不同語境下的動態畫面,如同電影倒敘回放一般呈現在觀眾眼前。
沒有沖突就沒有戲劇,舞劇《永不消逝的電波》之所以能將諜戰緊張的懸疑氣氛貫穿舞劇始終,就在于兩位編導對舞臺空間的充分運用。在呈現李俠識破特務奸計的畫面時,編導摒棄了冗長的線性敘事,而是采用平行蒙太奇的敘事方式,在同一時間順序下,通過一墻之隔,劃出兩個不同的空間。墻面的一側是裁縫受害過程畫面回放,一側是蘭芬發現特務身份且臨危不亂當場擊斃特務的驚險場景。兩種不同語境的空間都充滿著危機四伏的緊張感,在時空并進下,步步緊逼,直抵觀者咽喉。舞劇中,兩位編導對戲劇情節的巧妙構思還體現在對舞臺上的裝置道具——大型屏風的運用。通過不同時空場景下的位移與切換,屏風時而是舞臺的近景與遠景的分割線,時而是兩個平行的時空交界,在流轉變化的舞臺空間中,復雜曲折的故事情節與人物關系隨之展開。
二、鮮明的舞劇創作特征
(一)符號塑造下的隱喻敘事
普通藝術形象塑造與符號化藝術形象塑造最大的區別在于,符號化藝術人物形象能夠以小見大,提升舞劇的審美價值與藝術魅力。如舞劇《永不消逝的電波》中,編導利用諸多符號化的藝術形象如上海弄堂、街邊、裁縫店、報館的塑造,將上海這座具有深厚歷史意蘊的城市栩栩如生地展現在觀者眼前,從而體現出舞劇深層次的內涵,于細節處引發觀眾強烈的共鳴。在描繪生活場景時,編導在抽象的表現中穿插一些具體的生活細節,如“晾曬衣服”“互相問候”等生活體語,以加強人物及生活的真實感;同時,這種具體的真實感又聯系著抽象的意境,即在暗潮洶涌的地下工作者的生活中,這只不過是為掩人耳目的日常生活。這使得舞劇中一系列具有典型性的符號化形象塑造不僅僅停留在對生活具體現象的模擬上,而更具隱喻敘事的功能。
與此同時,編導善于在舞劇情節的推進中強化某一典型符號,并且通過關聯性道具同構的手法,使語意浮現出來。如旗袍店里雍容華貴的女子群像,在頓挫復沓中彰顯婀娜多姿的體態特征;又如市井弄堂中手持蒲扇,倚坐在矮凳上的弄堂女子群像,在重復扇動的蒲扇間投射出優雅知性的上海女性形象。看似簡單的群像塑造,卻讓觀眾無法輕易得知人物表面下隱藏著的雙重身份。編導利用符號化的形象塑造,完成了舞臺之外的敘事內容,從而構建出了一個時代現象以及時代群像。
(二)舞群交織下的情境意象
意象派詩人龐德說道:“意象是超越公式化了的語言的道。”他的意思是,“意象”系列的運動,不依靠“關聯詞語”來組接,而取消“關聯詞語”,其實是運用“意象”的暗示和隱喻取代以往那種平面拼湊的平鋪直敘。如編導韓真、周莉亞在舞劇《永不消逝的電波》中通過舞群的交織轉換為“情境意象”的營造的舞劇敘述手法。舞劇中,編導在交織變換的舞群中進行群像塑造和情勢渲染,并在此基礎上添加舞群的色彩,即按“戲劇性”的結構嵌入舞群的“色彩”。在舞劇的敘事推進下,這些舞群相互關聯地對比、消長,不僅巧妙地揭示出人物的內在關系,而且超越了啞劇的敘述,在推動劇情發展、輝映人物性格色彩的基礎上,構成了舞劇有機統一的氣韻,從而形成獨具特色的情境意象。
相比于一些舞劇中的舞段僅僅是為舞而舞,從而使得舞段陷入套路化、形式化的困境。舞劇中兩位編導則通過舞群交織來豐滿人物底蘊,營造舞劇的情境意象,使得舞劇“每一幕都有驚喜”。如在塑造撐著黑傘的“黑勢力”群像之時,兩位編導通過在大屏交替位移的背景烘托下,將舞者們的直立行走動作在節奏上進行同步與不同步的交替運用,在舞臺調度上進行規則與不規則的交替運用,從而營造出一種危機四伏、步步緊逼的意境。又如手持蒲扇的女子群舞,伴隨著韻律熟悉的《漁光曲》的再現,該舞段成為極具海派風情的人物內心活動外化。舞者們依靠在小矮凳上,手持蒲扇靜靜扇動,動作神韻或溫婉,或靈動,在“啞劇動態”的舞蹈化中,該舞段成為了人物內心活動的形體化。編導正是通過關注劇情背景、事件走向把握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塑造出色彩對比鮮明、節奏錯落有致的舞群,并且在舞群的交織中構成舞蹈視覺形象最直接的“結構骨架”,彰顯出不同的動作語意的“語境”,從而產生出不同的情境意象。
三、深邃的舞劇價值旨歸
(一)諜戰題材舞劇的全新探索
舞劇《永不消逝的電波》通過大膽創新的藝術創作手法,以戲劇化的肢體語言作為舞劇敘事的符號,為劇中的革命情懷的彰顯賦予了新的形式。舞劇通過舞蹈的表現形式營造出人物所處的典型環境,從而代替有聲的語言敘事,創造出更具敘事價值的舞劇結構,為劇中革命情懷的彰顯賦予了全新的形式,也為諜戰題材舞劇開辟了全新的探索道路。
舞劇中不僅融入了革命情懷和諜戰元素,更通過精練的舞劇創作手法與鮮明的創作特征,塑造出骨血豐滿的人物形象與語意深刻的舞臺空間,細致入微地刻畫出那個年代革命伴侶之間的情感與革命者們對信念的堅守,將革命英雄的情懷完美地釋放出來,從而真正做到運用舞蹈展現諜戰故事,且將諜戰緊張的懸疑氣氛貫穿舞劇始終。并且在符號塑造的隱喻敘事與舞群的交織中營造出獨特的舞劇情境意象,從而達到深邃的舞劇價值旨歸。
(二)本土文化資源的語言轉化
整部舞劇通過對歷史真實的回歸,凸顯出真實的人性,并且發揚上海本土文化資源優勢,于細節處巧妙地融入本土海派風情,切合當下的審美,以舞劇的藝術風格和諜戰的緊張懸念對我黨歷史上壯烈犧牲的情報英雄們進行全新的闡釋。在對本土文化資源進行舞蹈語言轉化時,編導并未拘泥于單一的創作手法,而是將生活具象動態符號化,并且通過舞群的交織營造出獨特的舞劇情境意象,使得上海、諜戰等傳統元素煥發出新的生機。那些熟悉且極具代表性的海派風情文化,正是在具有生活真實情感表達的細節動作的符號象征中得以展現。
舞劇《永不消逝的電波》對本土文化資源進行舞蹈語言轉化,并通過多重語意的舞臺空間營造與舞群的交織制造出一種獨特情景意象,從而構成了完整的舞劇藝術形象體系和引人入勝的藝術意境。當海派風情元素符號碰撞上激烈刺激的諜戰氛圍,豐滿的舞臺空間營造與豐富的人物內心情感相輔相成,獨特的創作技巧不僅為觀者營造出一個想象的空間,也使得整部舞劇創作手法走向多元化。
參考文獻
[1]于平.中外舞蹈思想概論[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 2002.
[2]許薇.舞蹈創作基礎理論[M].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 2016.
作者簡介:涂越(1997—),女,漢族,江西上饒人,南京藝術學院舞蹈學院,18級在讀研究生,碩士,音樂與舞蹈學專業,研究方向:舞蹈理論與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