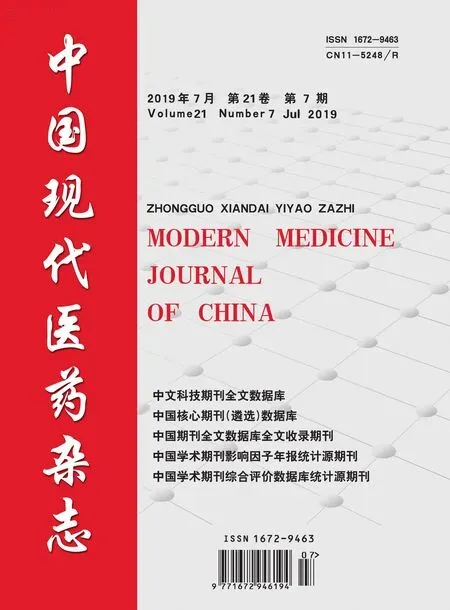血瘀證乳腺癌與分子分型及預后關系的相關性研究
陳桂芬
分子分型已被現代醫學作為乳腺癌患者個體化治療方案選擇及判斷預后的依據[1,2]。根據不同的分子分型選擇最佳的治療方式,可使乳腺癌患者更大程度獲益,提高5年生存率[3]。血瘀證作為乳腺癌常見的中醫辨證分型之一,通過現代醫學的檢測手段,把握其生物學行為,評估其預后,認識其影響預后的機理,從而進行個體化治療,改善預后是值得我們關注的一個課題。為此,本研究從乳腺癌的分子分型及ER、PR 角度出發來討論血瘀證評估預后的價值及其相關性,現報道如下。
1 材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收集我院2017年5月~2019年3月符合以下條件的乳腺癌患者。入組共80 例,均為女性,年齡25~70 歲。血瘀證40 例,平均年齡50.25 歲;非血瘀證40 例,平均年齡52.65 歲。均經穿刺或手術病理確診為原發性乳腺癌,病理類型均為浸潤性導管癌;卡氏評分在70 分以上,預計生存期大于6 個月;入院前1 個月均未服用過活血化瘀等影響中醫辨證的藥物;均未合并有心腦血管、肝臟、腎臟、造血系統及內分泌系統等嚴重原發性疾病者;均無智力障礙,精神病患者不能配合證型評估者。兩組患者在年齡、卡氏評分、實驗室各指標等方面分布較均衡,無統計學差異(P>0.05)。
1.2 方法
1.2.1 對影像學診斷為可疑乳腺癌的患者先采集資料進行中醫辨證分型,分為血瘀證和非血瘀證,然后粗針穿刺或手術獲得病理,確診為乳腺癌并符合納入標準的患者入組,采用免疫組織化學EnVision二部法測定血瘀證和非血瘀證乳腺癌患者ER、PR、HER-2、Ki-67 的陽性及陰性表達情況,根據兩組患者ER、PR 表達情況,分析其預后;根據ER、PR、HER-2、Ki-67 的表達情況進行分子分型。
分子分型(中國抗癌協會乳腺癌診治指南規范,2013 版):Luminal A 型:ER(+)/PR(+),且PR 表達≥20%,HER-2(-),Ki-67≤14%;Luminal B 型:①ER(+)/PR(+),HER-2(-),且Ki-67>14% 或PR<20%,②ER(+)/PR(+),HER-2(+),任何狀態的Ki-67;HER-2 過表達型:ER(-)和PR(-)且HER-2(+);基底細胞樣型:ER(-),PR(-)且HER-2(-)。
1.2.2 中醫辨證方法 所有入組病例于初診時即行中醫望、聞、問、切四診資料采集并運用表格法記錄,參照中國中西醫結合研究會活血化瘀專業委員會制定的《血瘀證診斷標準》,由兩位中醫的資深醫師分別進行辨證分型,討論達成一致后記錄。
根據乳腺癌病因病機分為血瘀證和非血瘀證(包括氣血虧虛、氣滯、氣郁、痰凝及熱毒等)。血瘀證參照中國中西醫結合研究會活血化瘀專業委員會制定的《血瘀證診斷標準》。血瘀主要證候:A、舌質紫黯,舌有瘀斑瘀點;B、脈象多呈細澀;C、唇及指端多紫紺,面部、唇、齒齦及眼周紫黑;D、黑便,皮膚瘀斑等;E、肌膚甲錯;F、疼痛(刺痛、定痛、久痛);G、經期腹痛,血黑有塊。(具備其中任意兩項即可診斷為血瘀證)。不符合以上血瘀證診斷標準的為非血瘀證者。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0.0 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非正態分布,采用秩和檢驗(獨立樣本Mann-Whitney U 檢驗)。
2 結果
2.1 血瘀證與非血瘀證兩組患者的ER 比較 血瘀證乳腺癌組ER 陽性患者19 例,陰性21 例;非血瘀證乳腺癌組ER 陽性患者31 例,陰性9 例;血瘀證乳腺癌組ER 陽性例數明顯少于非血瘀證乳腺癌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7.680,P=0.006)。
血瘀證乳腺癌組ER 值平均秩(31.76)與非血瘀證乳腺癌組(49.24)比較,明顯較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Z=-3.488,P=0.000)。
2.2 血瘀證與非血瘀證兩組患者的PR 比較 血瘀證乳腺癌組PR 陽性患者12 例,陰性28 例;非血瘀證乳腺癌組PR 陽性患者23 例,陰性17 例;血瘀證乳腺癌組PR 陽性例數明顯少于非血瘀證乳腺癌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6.146,P=0.013)。
血瘀證乳腺癌組PR 值平均秩(35.2)與非血瘀證乳腺癌組(45.8)比較,明顯較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Z=2.235,P=0.025)。
2.3 血瘀證與非血瘀證兩組患者的分子分型分布情況比較 血瘀證乳腺癌組和非血瘀證乳腺癌組在Luminal B 型上分布均最多,分別為17 例和26 例,共43 例;在基底細胞樣型分布均最少,分別為8 例和3 例,共11 例。血瘀證乳腺癌組在Luminal 型(包括Luminal A 型和Luminal B 型)分布共19 例,明顯少于非血瘀證乳腺癌組的32 例;在HER-2過度表達型和基底細胞樣型分布共21 例,明顯多于非血瘀證乳腺癌組的8 例,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血瘀證乳腺癌組在HER-2 過度表達型和基底細胞樣型分布例數總和多于Luminal 型;而非血瘀證乳腺癌組主要分布于Luminal 型。見表1。

表1 血瘀證與非血瘀證患者分子分型分布情況(例)
3 討論
乳腺癌在祖國醫學中稱為“乳巖”、“石榴翻花發”等。中醫認為:瘀血內結是乳巖發生、發展的重要病理機制之一。或因憂郁傷肝、思慮傷脾;或因七情內傷、氣血紊亂、臟腑失調,致邪毒內侵,氣滯血瘀,久則聚痰、成瘀,相互博結于乳中,形成乳巖。明代陳實功《外科正宗》中記:“初如豆大,漸若棋子,半年、一年、二載,不痛不癢;漸漸而大,始生疼痛,痛則無解。日后腫如堆栗,或如覆碗,紫色氣穢,漸漸潰爛”。《諸病源候論》記:“瘀久不消則變為積聚徵瘕”。可見,乳腺癌與血瘀之間有非常密切的關系。血瘀證證候主要有疼痛、腫塊、舌質紫暗、瘀斑、脈絡細澀等。許多乳腺癌患者在疾病發展過程中會出現以上證候,然一旦形成有形的結塊,必定會消耗人體的正氣,導致正氣抵抗外邪能力明顯下降,從而使癌細胞迅速增殖、擴散,甚至轉移。國內外研究也證實[4,5],血瘀證患者體內普遍存在血液高凝狀態,這種狀態可致血流緩慢,有利于癌細胞停滯附著血管壁,形成癌栓;還可以促進癌細胞血小板栓子的形成,阻礙免疫系統對癌細胞的攻擊殺傷作用,從而促進腫瘤的生長及轉移。故通過結合現代醫學手段掌握血瘀證乳腺癌個性所在可以更好地指導治療,改善預后。
乳腺癌的個體化治療越來越受重視,中醫和西醫這兩種完全不同的理論體系在乳腺癌的病因病機解釋上也不相同,但辨證論治和分子分型體現的都是個體化治療的思想,因此在判斷預后上是否存在相關,值得我們進一步驗證。
目前,ER 和PR 作為生物標記物被廣大學者廣泛應用于科研評估預后之中。ER、PR 的表達情況是影響乳腺癌預后的重要因子,表達陽性越高的患者具有更長的生存期[6,7]。孫紅等[8]對80 例乳腺癌患者術前進行中醫證候分類,術后檢測ER、PR 及HER-2,血瘀組ER 陽性率明顯低于其他各組,提示預后可能較差,與本研究相符。在ER、PR 陽性例數比較上,血瘀證乳腺癌組皆少于非血瘀證乳腺癌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在ER 值、PR 值平均秩比較上,血瘀證乳腺癌組也皆低于非血瘀證乳腺癌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由此提示,血瘀證乳腺癌的預后較非血瘀證差。
乳腺癌的分子分型能更精確地反映腫瘤的生物學行為,更有利于個體化治療方法的選擇及預后的判斷[9]。乳腺癌分子分型即是結合患者ER、PR、HER-2、Ki-67 的表達高低情況可分為Luminal A型、Luminal B 型、HER-2 過表達型及基底細胞樣型。其中Luminal A 型是乳腺癌最常見的分子亞型,預后最好,內分泌治療效果最佳,對化療不甚敏感;Luminal B 型次之,內分泌治療效果好,對化療是否敏感,目前仍有爭議;HER-2 過表達型雖有靶向治療指征,但預后仍較差;基底細胞樣型預后最差,常早期發生內臟轉移、骨轉移及腦轉移。根據不同類型選擇不同的治療方案,可以讓患者避免過度治療,獲益更大,預后更好。近年來,國內研究者開始嘗試將乳腺癌的中醫辨證分型與西醫的分子分型結合起來,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周莉等[10]將105 例乳腺癌患者中醫辨證分型與分子分型進行分析發現,肝郁氣滯者多屬Luminal A 型,預后較好;熱毒內蘊者多屬基底細胞樣型,預后較差。本研究顯示,血瘀證乳腺癌組和非血瘀證乳腺癌組在Luminal B型上分布例數均最多;在基底細胞樣型分布例數均最少;血瘀證乳腺癌組在Luminal 型分布例數共19例,明顯少于非血瘀證乳腺癌組的32 例;在HER-2過度表達型和基底細胞樣型分布例數共21 例,明顯多于非血瘀證乳腺癌組的8 例,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血瘀證乳腺癌組在HER-2 過度表達型和基底細胞樣型分布例數總和多于Luminal 型;而非血瘀證乳腺癌組分布主要傾向于Luminal 型。由此進一步證實,血瘀證乳腺癌的預后較非血瘀 證差。
綜上所述,血瘀證乳腺癌分布于HER-2 過度表達型和基底細胞樣型的例數總和較多,ER 值及PR 值平均秩均較低,提示預后可能較差。在今后對乳腺癌患者的治療中,可采用中西醫結合,對于血瘀證患者加用活血化瘀的中藥,調節微循環,改善血液的高凝狀態,提高機體免疫力,從而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和治療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