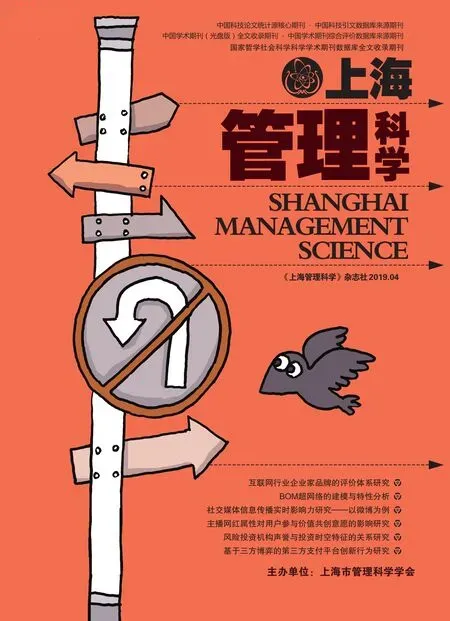主播網紅屬性對用戶參與價值共創意愿的影響研究
王海花 李 玉 熊麗君 杜 梅
(上海大學 管理學院,上海 200444)
“網紅”依托互聯網環境,通過展示藝術特長、制造話題輿論性或進行其他傳播度較強的行為,與大眾的品味、審美相契合,在網絡空間中聚集人氣,進而由這些社交資源獲得收入。近年來,“網紅經濟”在社交媒體持續發力,網紅粉絲總人數增長迅速。《2018年中國網紅經濟發展研究報告》顯示,截至2018年4月,中國網紅粉絲總人數達到5.88億,同比增長25%。根據內容呈現方式、領域分布的不同,“網紅”分為時尚網紅、主播網紅和內容網紅三大主體,而通過趣味搞怪、展現藝術特長的主播網紅逐漸進入大眾視野中,發展勢頭迅猛。《2018Q1中國在線直播行業研究報告》顯示,2017年在線直播用戶規模達到3.98億人,增長率為28.4%,預計2018年在線直播用戶規模達4.60億人,2019年達5.07億人。
“網紅經濟”逐漸產業化發展,這一社會現象逐漸引起學者們的關注。張昊等研究了時尚網紅參與價值共創對時尚產品設計屬性的影響,揭示了時尚網紅在價值共創中的作用。內容網紅以“知識網紅”為代表,可發表特定知識或具有知識產權的特定服務,與內容創新生產息息相關。而主播網紅通過直播平臺與用戶進行信息交互,將用戶打賞等回饋作為收入之一,是直播平臺重要的人力資源,同樣可以作為價值共創的主體,現有企業已經開創與網絡主播合作的先河,斗魚直播平臺以8位數的簽約費簽約馮提莫就是典型的例證。但目前對于主播網紅的研究還比較缺乏,主播網紅對用戶參與價值共創意愿的影響過程還有待研究。
鑒于以上研究現狀,本文以主播網紅為研究對象,結合價值共創理論,探討主播網紅屬性通過何種方式對用戶參與價值共創意愿產生影響,以及企業的程序控制在這一過程中的影響機制。
1 研究假設
1.1 主播網紅屬性與情感體驗價值
近年來“網紅經濟”發展迅速,主要原因包括如下兩點:一是由于“重話題”退位而“輕話題”補位,公共性實務傳播走向衰敗,私人性浮躁喧囂乘虛而入,二是由于“網紅”具有超出預期的吸金能力。最典型的案例是Papi醬,其借助視頻直播平臺,以直播視頻的形式進行內容傳播和形象塑造,一上市估值便有1.2億元,這種吸金能力超出人們預想,因此,“網紅經濟”被定義為全新產業。已有學者對網紅進行了定義,周延風等認為網紅除憑借互聯網媒介獲得高知名度、高影響力的的人之外,還包括以“喜茶”為代表的網紅品牌,也有學者認為網紅是指借助網絡平臺成功走入公眾視野的人。根據主體的性質不同,網紅的定義存在差異,但憑借強大的網絡影響力和傳播度,網紅均對用戶產生巨大的情感支持和影響。在營銷方面,網紅區別于一般領先用戶、現實環境中的名人和傳統意義上的忠誠消費者,其市場敏感度及觀察角度與眾不同,甚至優于某些商家的前端反應模式,網紅與企業合作生產、營銷的模式逐漸顯現,網紅亦可成為價值共創的主體。
主播網紅自身的觀點、態度等行為特征能夠影響用戶對互動內容的判斷和感知,針對用戶消費心理和需求設計具有辨識度和獨特性的內容可打破流量瓶頸,與用戶建立信任關系,增強用戶情感體驗價值。在探討主播網紅屬性對用戶參與價值共創意愿的影響過程中,本文引用張昊在探討時尚網紅屬性對產品設計的影響中關于時尚網紅的三個屬性:網絡流行性、目的性和親民性。網絡流行性主要指主播網紅經自媒體渲染后的網絡傳播度,這種憑借網絡平臺宣傳的主播多是通過平臺層級考核,被平臺置頂到界面顯著位置,成為用戶體驗的首選;親民性指的是主播網紅所表現出的態度親和、平等對話的行為,這能夠拉近其與用戶的距離,將用戶置于與主播地位平等的狀態;目的性指的是網紅與電商的結合實現營銷變現,其對時尚的敏感度、專業性較強,更易引發用戶情感上的信任,進而產生購買傾向。同時,主播網紅對雙方的交流方式具有體驗感知及控制程度等心理感受,人際間互動可對用戶情感體驗價值產生正向影響,進而對用戶參與價值共創的意愿產生積極影響。可見,用戶能夠對互動質量進行判斷和認知、形成用戶情感體驗,故本文將互動性作為主播網紅的屬性之一。因此,我們得到假設:
假設1:主播網紅屬性對情感體驗價值存在顯著正向影響。
假設1a:網絡流行性對情感體驗價值存在顯著正向影響;
假設1b:親民性對情感體驗價值存在顯著正向影響;
假設1c:目的性對情感體驗價值存在顯著正向影響;
假設1d:互動性對情感體驗價值存在顯著正向影響。
1.2 情感體驗價值對其參與價值共創意愿的影響
情感體驗價值是用戶自我表現和社會需求的滿足,主要體現為用戶對社區的認同。情感體驗價值是用戶對產品或服務的無形屬性的感知,這種情境化、差異化、個性化的體驗感知可增強用戶黏性,進而促進用戶的消費傾向。直播平臺可創建一種主播與用戶共同構建個性化體驗的環境,用戶可以與主播網紅積極對話,進行討論、評說、發彈幕、打賞,實時分享觀點和看法,用戶不只作為觀看者,而與直播平臺、主播的收益緊密聯系。在這個過程中,用戶對價值的生成過程所具有的整體控制感會增加用戶的滿意度,用戶若認為在價值創造中自身能夠有所貢獻,且能體驗到對價值共創的影響力,便會增加對產品或服務的正向評價,并積極參與到價值共創過程中。卓越的用戶價值可以帶來諸如正向口碑、再次消費等正向行為傾向。這種正向行為還表現在一是可以購買不同價值的禮物贈予主播,二是通過訂閱會員的方式,每月支付固定的費用以獲得消除廣告、訂閱頻道等普通用戶無法享受到的優勢,這兩種方式構成了直播平臺的主要營收來源。因此,我們假設:
假設2:情感體驗價值對用戶參與價值共創意愿存在顯著正向影響。
1.3 情感體驗價值的中介作用
主播網紅通過調整態度行為特征,并發布有價值、與用戶利益相關并且吸引人的內容,與用戶產生情感共鳴,而情感體驗價值可通過用戶對直播社區的認同來體現,用戶的認同是驅動其參與企業新產品開發的重要因素,對其參與產品或服務創新有積極影響。用戶基于情感判斷,積極參與到產品或服務的創新過程,也可根據自身體驗為平臺建設提供建議,形成用戶反饋機制。可見,主播網紅并不直接影響用戶參與價值共創意愿,而是主播的態度行為會向用戶發出一種信號,用戶基于自我判斷和情感認同,進而表現出價值共創傾向。因此,我們假設:
假設3:情感體驗價值在主播網紅屬性對用戶參與價值共創意愿的影響中起中介作用。
1.4 程序控制的調節作用
由于直播平臺準入門檻較低,主播網紅行為屬性、互動內容的質量成為直播平臺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為給平臺發展提供決策依據,本文選取程序控制作為調節變量,驗證企業的參與行為對價值共創過程的影響。價值共創強調企業與用戶共同創造體驗,企業的作用雖然會減弱,但企業更熟悉環境、流程和工具的使用,企業參與具有輔助作用,但價值共創理念正是由于價值的創造要擺脫企業的控制而提出的,標志著企業控制行為的程序控制會降低用戶的價值創造。Armstrong的流體驗實驗也表明,群體受到的規則限制越多,成員的主動性就會越差,成員之間的交流互動越少,無法獲得流體驗,也說明企業過多的參與行為會抑制用戶互動和體驗的產生。由于直播平臺建立了一系列的行業規范、平臺約束準則,主播網紅在直播過程中的行為、態度、言論具有一定的限制和約束。這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違規行為,但用戶相對開放性的問題難以得到解答,且用戶在情緒高漲時收到平臺對操作與使用的提示,會降低情感體驗價值感知,所以企業過多參與不利于價值共創。因此,得到假設4:
假設4:程序控制負向調節主播網紅屬性與情感體驗價值之間的關系。
假設4a:程序控制負向調節主播網絡流行性與情感體驗價值之間的關系;
假設4b:程序控制負向調節主播親民性與情感體驗價值之間的關系;
假設4c:程序控制負向調節主播目的性與情感體驗價值之間的關系;
假設4d:程序控制負向調節主播互動性與情感體驗價值之間的關系。

圖1 理論模型
2 研究設計
2.1 樣本選取與數據收集
在用戶與網絡接觸點越來越多的時代,用戶在泛娛樂化直播平臺的涉入度較高,且貼近生活,故本文選取泛娛樂化平臺為研究對象,以日常觀看直播和觀看過程中有過消費經歷的用戶為樣本,以線上問卷調查法為主、現場訪談法為輔來收集數據。線上收集的方式主要有2種:一是加入主播粉絲QQ群,向粉絲群體發送問卷鏈接,二是通過社交軟件滾雪球的方式來獲取一部分樣本。
問卷發放從2018年3月份開始,至2018年8月份結束。共發放問卷300份,紙質問卷110份、電子問卷190份,共回收278份,剔除漏填、明顯雷同等不合格問卷后,得到有效問卷237份,問卷的有效回收率為79%,調查樣本的基本情況如表1所示。

表1 調查對象基本信息
2.2 變量測量
量表中各變量均采用Likert 5點量表進行測量(1=完全不符合、2=有點不符合、3=一般、4=比較符合、5=完全符合)。為使量表更加準確且有實際價值,筆者首先注冊為直播平臺用戶,觀察和體驗直播社區中主播的行為特征、用戶的行為及自身體驗感知,對直播社區形成初步認識;其次,筆者搜集了大量有關價值共創和直播行業創新發展的相關文獻,涉及的變量部分借鑒了前人的研究成果。
(1)主播網紅屬性。借鑒了張昊等和趙宏霞等的量表,主播網絡流行性包含“他/她們網絡曝光度高”等3個題項,主播親民性包含“他/她們的行為大眾化”等3個題項,主播目的性包含“他/她們為了推廣產品”等3個題項,主播互動性包含“他/她們非常樂意與我溝通”等3個題項。
(2)情感體驗價值。借鑒Sweeney的情感體驗價值量表,情感體驗價值包含“融入直播社區讓我不再孤獨和無聊”等4個題項。
(3)用戶參與價值共創的意愿。借鑒了Zwass和李朝輝開發的量表,用戶參與價值共創的意愿包含“我經常參加企業或社區發起的新產品創意征集活動”等4個題項。
(4)程序控制。借鑒了王新新、萬文海的量表,包含“當成員不遵守規則時,組織方會不停地說明”等4個題項。
(5)控制變量。結合直播平臺特征及用戶研究情境需要,選擇調研對象的性別、年齡、學歷、平臺用戶規模、登錄頻率及用戶觀看支出作為控制變量。
3 實證分析結果
3.1 信效度檢驗
本文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驗證性因子分析檢驗量表的信效度。首先,本文使用SPSS 22.0軟件對量表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運用最大方差法提取因子(見表2),結果顯示KMO檢驗值為0.848,Bartlett球形檢驗的近似卡方值為2508.223,顯著水平為0.000。因子分析的結果表明,所提取的因子累計解釋71.269%的信息,且所有題項的因子載荷均大于0.5,表示量表的內容效度良好。Cronbach′s α系數值均大于0.7,說明量表的信度較好。
為了檢驗研究量表的區別效度,本文采用AMOS 21.0軟件檢驗模型中7個變量的驗證性因子分析(見表3)。由表3可知,七因子模型(網絡流行性、親民性、目的性、互動性、情感體驗價值、程序控制、用戶參與價值共創的意愿)的適配度更好(X2/df=1.014<3,CFI=0.999>0.9,TLI=0.998>0.9,RMSEA=0.008<0.08),表明量表中的7個變量具有較好的區別效度。
3.2 描述性統計和相關性分析
本文涉及的各變量的均值、標準差以及變量間的相關系數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相關性矩陣表明變量之間均存在相關性,適合做進一步的分析與檢驗。

表2 探索性因子分析

表3 驗證性因子分析結果
注:1-絡流行性,2-民性,3-的性,4-動性, 5-序控制,6-感體驗價值,7-戶參與價值共創意愿
3.3 假設檢驗
本文采用Amos 21.0構造結構方程模型,結果如圖2、表5所示。可看出,主播網紅網絡流行性、親民性、互動性對情感體驗價值均有顯著正向影響(β=0.278,p<0.001;β=0.215,p<0.01;β=0.300,p<0.001),H1a、H1b、H1d均得到驗證;目的性對情感體驗價值的影響不顯著,H1c未得到驗證;情感體驗價值對用戶參與價值共創的意愿具有顯著正向影響(β=0.594,p<0.001),假設2得到驗證。
本研究參照Hayes提出的Bootstrap法檢驗標準檢驗情感體驗價值的中介效應,表5數據顯示,95%置信區間分別為[0.023,0.133]、[0.013,0.114]和[0.026,0.135],均不包含0,說明情感體驗價值在主播網紅網絡流行性、親民性和互動性對用戶參與價值共創意愿的影響中發揮的中介作用均顯著,假設3得到驗證。

表4 描述性統計結果和相關系數矩陣
注:N=237;*表示p<0.05,**表示p<0.01

圖2 中介效應檢驗結果
表5 中介效應檢驗結果

效應估計值p值標準誤LLCIULCI網絡流行性→情感體驗價值→用戶參與價值共創的意愿0.0630.0020.0280.0230.133親民性→情感體驗價值→用戶參與價值共創的意愿0.0480.010.0230.0130.114互動性→情感體驗價值→用戶參與價值共創的意愿0.0670.0020.0270.0260.135
注:LLCI、ULCI分別為95%置信區間的上限和下限
本文采用多層回歸分析方法檢驗調節效應,首先對變量進行了中心化處理(Aiken和West,1991),以減少多重共線性問題,結果見表6。由表6數據可知,程序控制在主播網紅互動性和情感體驗價值之間的調節效應顯著(β=-0.144,p<0.5),這表明企業或平臺的程序控制水平越高,主播網紅互動性對用戶參與價值共創意愿的正向影響越小,反之就越大,H4d得到驗證;其次,程序控制在主播網紅網絡流行性和情感體驗價值之間的正向調節效應顯著(β=0.197,p<0.01),這表明企業或平臺的程序控制水平越高,主播網紅網絡流行性對用戶參與價值共創意愿的正向影響越大,反之就越小,H4a未得到支持。

表6 調節效應檢驗結果
注:*p<0.05,**p<0.01,***p<0.001

圖3 程序控制在互動性與情感體驗價值間的調節效應圖
3.4 實證結果討論
本文以價值共創理論為基礎,通過對直播平臺用戶的深度訪談和實證研究,探討主播網紅屬性、情感體驗價值及用戶參與價值共創意愿之間的關系,從用戶視角和企業視角探討直播平臺價值創造的作用機理。本文的主要結論及管理啟示如下:
(1)主播網紅網絡流行性、親民性及互動性對情感體驗價值的影響均得到驗證,目的性對情感體驗價值的影響未得到支持。
網絡流行性反映的是主播網紅通過平臺考評、用戶推薦的綜合情況,更能引發用戶的話題及審美傾向,從而獲得用戶的情感信任;主播網紅親民性可減少其與用戶的距離感,使用戶感受到與主播網紅處于同等地位,產生情感認同;同時,互動儀式鏈理論和社區融合理論都表明,各種形式的互動都能讓參與主體產生情感體驗,主播網紅可通過音樂舞蹈、知識傳授、游戲評說等形式為用戶創造個性化體驗。主播網紅目的性對情感體驗價值的影響未得到驗證,原因可能是部分主播網紅通過平臺宣傳的途徑進行自我營銷,有嘩眾取寵、獲取用戶信賴的傾向,而用戶更多想在直播社區放松心情、從日常的壓力和責任中解脫出來,所以對營銷廣告比較排斥。
(2)情感體驗價值在主播網紅屬性與用戶參與價值共創的意愿間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證實了情感體驗價值成為主播網紅屬性與用戶參與價值共創的意愿間的連接機制,主播網紅行為特征不會直接促使用戶的價值共創行為,而是通過為用戶創造高層級的內在情感體驗促使其積極參與到價值共創過程中。這與武文珍等通過實證研究證實的非效應性的情感體驗對用戶態度和行為產生的影響日益明顯這一結論保持一致。主播網紅的態度、行為特征伴隨其輸出內容的質量,優質的互動內容會帶給用戶價值觀、消費觀、人生觀的啟迪,通過用戶的情感體驗價值影響其參與價值共創。
(3)程序控制在主播網紅屬性與情感體驗價值間的調節作用。
研究發現:程序控制負向調節主播網紅互動性與情感體驗價值的關系,H4d得到了驗證;程序控制正向調節網絡流行性與情感體驗價值間的關系,H4a沒有得到驗證。原因可能是因為主播網紅的網絡流行性本身對其積累粉絲、積聚人氣是有益的,但平臺對于主播網紅的曝光頻率進行控制,使主播網紅不會得到過度追捧,反而會凈化網絡環境,避免追星、粉絲應援集資等現象的出現,有利于用戶的情感體驗。
4 結論與啟示
本研究以直播行業為背景,以價值共創理論為基礎,探討了主播網紅屬性通過情感體驗價值對用戶參與價值共創意愿的影響機制,以及程序控制在主播網紅屬性對情感體驗價值的影響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建立了直播網紅—用戶情感體驗價值—用戶參與價值共創意愿這一路徑的研究。
4.1 研究啟示
第一, 提升主播網紅素質,差異化輸出內容。主播網紅的言論、態度及行為會影響互動內容的輸出,用戶對平臺的依賴歸根到底是由服務質量所決定的,這與Vargo和Lusch提出的基于服務主導邏輯的價值共創理論一致,該理論認為服務是一切經濟交換的根本基礎。主播網紅直播通過言語表達所闡釋的內容是否符合主流、新穎、有個性,會影響用戶對直播平臺整體形象的定位,進而影響用戶規模;企業應加強對主播網紅培訓的力度,提高主播網紅對所提供服務的專業性,減少低俗化內容的輸出,實現直播平臺的可持續發展。
第二,加大用戶授權,優化用戶環境。在平臺建設中實現與用戶信息的交互、融入用戶反饋機制,不僅需要企業基礎設施的建設,也需要企業授予更多的自主權給用戶,這可以增加用戶對價值共創的成員感、影響力和沉浸感,從而促進用戶參與價值共創的過程。在價值共創模式下,用戶更多追求個性化體驗,尤其是對較高層次的情感體驗價值的需求。因此,企業需關注主播網紅與用戶間的互動水平,同時將與用戶體驗相關的因素考慮進去,包括系統流暢程度、平臺環境及互動策略等。
第三,加強程序控制,提高平臺準入門檻。主播網紅作為直播平臺不可或缺的人力資源,所傳達的網絡流行性、親民性及互動性能夠創造良好的直播氛圍,但由于平臺監管機制不完善,主播網紅行為、言論不當的現象時常出現,網絡環境無法得到凈化。平臺應全面禁止“擦邊球”行為,通過用戶反饋、平臺評估等多種方式對主播網紅定期考核;同時,完善平臺準入制度、實名登記制度及檔案管理制度,在程序和制度上進行明文規定,為用戶創造優質的互動環境。
4.2 研究展望
本研究主要以泛娛樂化平臺用戶為主要研究對象,受到樣本類型和問卷數量的限制,研究的普適性有待考證。本文探討了主播網紅屬性對用戶參與價值共創意愿的影響,網絡流行性、互動性、目的性和親民性較好地反映了情感體驗價值,目的性維度的效果不是太理想。未來的研究中,可對維度進行深入系統的分析,采用扎根理論、深度訪談法等對主播網紅的維度做深入分析,劃分出更為具體的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