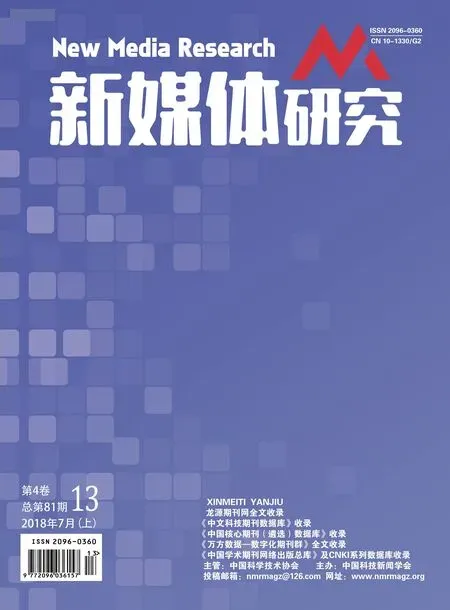后真相時代關于網絡輿論的思考
陳一凡
摘? 要? 后真相時代,當真相變得次要,一些公眾事件所形成的輿論便顯得更加偏激。文章以“上饒五小事件”為例,分析事件發生后網絡輿論所呈現的群體極化現象。并進一步思考這些現象產生的原因;自媒體在網絡中所營造的環境存在由于自身特點而形成的新常態,并且在UGC模式和新聞標準降低的情況下的這種新常態下的網絡輿論的劣性愈加明顯,因而時下的國內網絡環境下總體的輿論工作與大眾媒介素養的提升需要被重視。
關鍵詞? 后真相時代;網絡輿論;上饒五小事件;群體極化
中圖分類號? G2? ? ? 文獻標識碼? A? ? ? 文章編號? 2096-0360(2019)13-0013-02
在互聯網上,移動端的信息流已經占據了網絡信息的半壁江山,網絡渠道將大量用戶分流出來,使得傳統新聞媒體產業逐步走出大眾視野。基于網絡的傳播模式,人們接受的信息有限,缺乏閱讀深度,便很容易被自己的直觀情緒引導,傾向于主觀判斷,以至于“真相”變得不再那么重要,從而形成現在的后真相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情境下,網絡輿論顯得更加偏激,常常出現輿論反轉與媒介冷暴力的出現,值得深入思索與探究。
1? “上饒五小事件”中所出現的網絡輿論
2019年5月10日,據江西省上饒市信州區新聞中心官方微博消息,經信州公安刑警大隊偵查,上饒市第五小學“5·10”案件犯罪嫌疑人王某建對殺害受害人劉某宸的犯罪事實供認不諱,已被依法刑事拘留。網絡上的風波就在第一次新聞的發布后變得偏激與混亂,首先,微博上呈現了大量一邊倒的“叫好聲”,認為小男孩校園暴力小女孩,死有應得,包括許多微博的大V,而批評網友不該為殺人犯說話的人在零星的出現后被大量評論淹沒;另外,隨著家長發聲,有許多不知虛實的傳言也流傳開,基本都是替行兇者發聲。但在5月12日,遇害男孩母親發文,父親采訪發布,情況瞬間出現反轉,爆出女孩父親有偏執的傾向,男孩其實并沒有那么壞,立即就有網民“站隊”男孩,認為殺人犯行為極端等。不過目前已經呈現的兩個對立的輿論,無論哪個,對男孩還是女孩的家庭,都是強烈的網絡暴力。本文將依據后真相時代,從輿論環境,網絡用戶,新聞標準的角度來分析這個事件所形成的輿論熱潮與現階段網絡輿論的思考。
2? 事實真相被架空,情緒引導決策
“后真相”的含義是“情緒的影響力超過事實”,2016年后真相的概念被《牛津詞典》選為年度熱詞,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后真相時代”的到來[1]。針對這一事件,網絡群體的一大部分都在為殺人犯說話,這顯然不是一個健康的輿論應有的走向,其中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情緒引導作用,事件發生時媒體的報道所給予的信息量確實是不足的,信息中含有的校園暴力方面成為了網絡情緒的發泄口,很多人在訴說校園暴力的危害,一時間形成的對校園暴力的抨擊直接將輿論發酵,使得輿論情緒化很重,并且,在碎片化的信息接收下,新看到信息的受眾得不到完整的信息,往往會不自覺的被影響,這樣就形成了網絡群極化,一部分相對理性的人也由于“沉默的螺旋”而減少發言,情緒在輿論占主導后,網絡暴力滋生,形成很不健康的言論攻擊,而事實就已經顯得不重要了。在真相不明朗的情況下,極易出現的網絡群極化表現出了“情緒引導”的特征,網民的決策缺乏邏輯,缺乏思考,往往是被輿論帶著走。在這種出現人命的社會熱點事件中,這種情緒化的輿論顯然對當事人,對真相持有者非常不友好,網絡媒體時代的弊病在微博微信這種大平臺上持續被放大,并更加極端化。
3? 自媒體對輿論引導的新常態
后真相時代很大一部分程度時基于自媒體本身的特征而產生的,[2]微博微信等自媒體極大的彌補了由于過去傳播媒體的單一性所導致的信息源不足等問題,現在人人都可以成為新聞報道的消息來源,這種UGC的生產模式使每個用戶都是價值觀的輸出者。在這種時代,“把關人”的形象被淡化,發布言論幾乎不存在門檻,對普通用戶唯一的限制便是字數限制,這也是碎片化的起因。面對輿論熱點時,公眾在網絡上有時會更輕信小眾媒體發布的一些看似正確的爆料,這些聲音聚集后很可能會占據主流地位。
自媒體語境下的網絡輿論常常表現為眾聲喧嘩,并且容易出現情緒化的集合行動,讓輿論語法變得不受控制。例如這次事件里對男孩父母教育的批評與學校不作為的抨擊,這些言論來自于一些自媒體的流言,并不是來自正規新聞信息的獲取渠道,很多都是主觀臆測,相對于專業媒體的經過嚴格甄別,慎重考慮并有線下的對接信息,考慮各方面后果才發布的消息來說,自媒體時代這種隨意性使得輿論走向不正常成為一種新常態。
自媒體時代的輿論生成主要表現為多點多向性,既是接受者也是發布者的自媒體得到的反饋會來自多方面,大量觀點會聚集和碰撞,信息源在這大量信息中僅僅是作為一個點而存在,而輿論則來自于多點多面的交流,多個自媒體與用戶的交流后呈現出輿論方向,這種方向往往不受監督,因為主體已經變得模糊[3]。另一方面,在網絡里,熱點事件從發生到結束熱度都是轉瞬即逝的,這種時間的短暫性,使得輿論也從潛伏期到終結期相比傳統輿論熱潮而顯得更加短暫,主題內容變化的迅速很容易帶來負面效應大,正面效應低,真相淡化的效果,在公共事件剛剛發生、事實尚未調查清楚時,大眾關注度反而最高,上饒五小殺人事件中,事件前期對于校園暴力的討論一度極熱,但后來反轉的新聞發布時,熱度已經退散了不少,雖然反轉的不一定是真相,但可以預見,真實的情況被披露時,輿論的興奮期已經過去,關注點已經轉移到其他熱點上去了,變化快是自媒體時代的新常態,熱點的短暫性也是造成群極化的原因。
4? UGC模式帶來的信息繭房效果
UGC作為用戶原創內容的生產模式,在網絡環境中大大增加了受眾的話語權,使受眾地位提高,但也加重了信息繭房效應。在這個事件里,倘若是一名愛護女兒的父親,在面對這個事件的評論,很可能會基于自己的傾向去選擇自己帶有價值傾向的信息,然后發布不夠客觀的內容,這是由于信息繭房作用存在而導致的一種個體極化作用。面向整個網絡群體,我們說是一個“泛娛樂化”的時代,UGC模式同時也基于自媒體時代,自媒體時代的弊端也同時表現出來,不同的受眾,作為不同價值觀,不同喜好的群體,基于自己的情緒,自己的繭房效應,形成容易片面的信息傳播,這樣加重了擬態環境,并且很容易偏向娛樂化,色情化,暴力化,這使得公眾處于一種“真空”的擬態環境,依據自己的興趣去接受UGC模式生產的帶有娛樂信息,不實信息的環境,這種惡性循環,使“后真相”逐步向“無真相”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