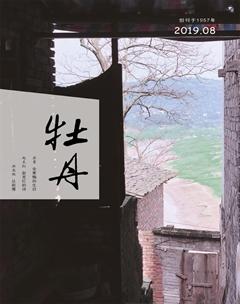教師“紅皮書”
王雪茜
1
我任教的文科班班主任是數學老師,年輕帥氣,是班里很多女生的偶像。他上課時從不拿教科書,也不帶教案,一只手夾一支煙,一只手拎一盒粉筆,講起課來洋洋灑灑,那些數字、公式像在腦子里排列好了,只待他一聲令下,就列隊出現在黑板上。“親其師信其道”,他班的數學成績無班能比,收作業從不用課代表反復督促。
這個班文化課成績雖好,體育方面卻很弱,每次運動會成績都是倒數,班主任只能將目標鎖定在精神文明獎。獲得精神文明獎的一個重要量化標準是廣播稿件的數量。我記得那時是高三開學不久,學校要召開秋季運動會,班主任讓每名學生至少報兩個運動項目,預交兩篇廣播稿。很多同學怕取不上名次,遲遲未報項目,交廣播稿的也寥寥,畢竟運動會未開,沒有“紅旗招展,鑼鼓喧天”的氛圍。
一天大課間,我正在教室后排解答一個學生的問題(學校要求大課間任課教師必須進班輔導),沒注意到班主任何時進了教室,直到他毫無征兆發了火。他敲了敲坐在第一排叫萍的女生的桌子,女孩戰戰兢兢站了起來,她平時總是沉默寡言,因數學成績不好,數學課從不敢發言,她周圍的同學常取笑她是數學低能兒,日復一日的消極反饋強化了她認為自己數學低能的印象,她本能地害怕班主任。個體心理學創始人阿爾弗雷德·阿德勒認為,人類的所有行為,都是出自于“自卑感”以及對于“自卑感”的克服和超越。
“你為什么不報運動會項目?”班主任怒氣沖沖。
萍的臉立即紅了,低著頭一聲不吭。
“問你呢,說理由,別當啞巴。”
“沒有擅長的項目。”她嚅囁道。
“有沒有點集體榮譽感?都沒有擅長的項目就不要參加運動會了。”班主任隨手從講桌上抓起一截粉筆,“啪”一聲甩在黑板上。
教室里霎時寂靜無聲,學生們嚇得大氣不敢出。
人很難逃離情緒的操控,教師尤是。我在多年的教學實踐中發現,教師群體易怒易沖動、情緒起伏明顯。教而不厭、誨人不倦的教育理想,潤物無聲、言傳身教的教育情懷幾乎被各類考核、學生違紀、總結匯報等各種因素消磨殆盡。在情緒中磨尖自己的教師群體,很容易采伐內心的躁動并將其分布擴散,而學生往往成為教師不良情緒的誘因與宣泄口。作為教師,手握鎖圈,上面并排拴掛著的,一邊是惡魔的鎖鉤,一邊是天使的鑰匙。
體育委員見勢不妙,馬上站起來催促未報項目的同學立即上報,學生們紛紛拿出演草紙胡亂寫上項目,交給體育委員。
似乎是余怒未消,班主任邊向門邊走邊恨恨地說:“一群賤皮子,總是不自覺,不要臉。”
“不要臉”三個字讓萍的眼淚刷一下淌滿臉,她抽抽噎噎哭了起來,老師見慣了學生被批評后的哭招,早就不為所動,有的老師看到學生流淚,還會更加生氣。班主任并未意識到“不要臉”三個字對一個崇拜自己的女生的殺傷力。殺雞駭猴的效果達到之后,不以為意地回辦公室去了。十幾分鐘后,上課鈴響過好一陣,不知誰才發現大課間哭著走出教室的萍不見了。通常學生受了委屈,下課找個角落抹幾把眼淚,要好的同學圍著勸幾聲也就過去了。萍不一樣,她在班里似乎沒有關系特別好的伙伴,連同桌也沒留心她去了何處。班長著了急,急急忙忙去報告班主任,班主任這才慌了神,發動全班同學出去找。
青春期的學生自尊心極強,老師稍有不慎,就會引出事端。我剛當班主任時,年輕莽撞,忘記因為什么緣由,在走廊嚴厲批評過一個女生,當時覺得并無不妥,不曾想她第二天竟沒有來學校上課。心虛而忐忑的我不敢耽擱,給家長打電話,家長卻說,孩子早晨背著書包正常上學了啊。最終父母在孩子奶奶家找到了女孩,她如沒事人一樣面無表情。家長說,孩子心眼窄,一生氣就愛離家出走,不怨老師。我至今忘不了彼時大腦一片空白的恐慌和無助,那以后,我再也沒批評過她。
學校北面是一個很大的潮溝,漲潮時水位很深。有同學發現萍站在壩下的淤泥里,那時正逢退潮,潮溝里并沒多少水,她陷在泥里,左顧右盼,進退兩難。幾個男同學脫了鞋襪,下到淤泥里,把她拽了上來。
毫無懸念,迎接班主任的是家長的不依不饒,教育局的輪番調查,學校領導的誡勉談話。最終的處理結果是給了班主任一個不大不小的處分。其他老師物傷其類,很長時間內批評學生不免投鼠忌器。
這場有驚無險的事件后,班主任辭了職,去南方跟他的父親做生意去了,后來發了大財衣錦還鄉,在我們市開了一家五星大酒店。
2
班長屢次對我說,學生們很反感我班的歷史老師。問他原因,又訥訥不說。無風自然不能起浪,閑言碎語我也略有耳聞。作為班主任,我要對我的學生們負責。但,教我班歷史的林老師是學校資歷最老的老師,又曾教過我,我很難無所顧忌。
我讀高中時,林老師大概不到四十歲,可頭發似乎全白了,背也駝得厲害。據說學校新分來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第一次見到林老師,誤以為是學校門衛,直喊“老大爺”。
他的課上得極其沉悶乏味,加之聲音低緩無變化,直讓人昏昏欲睡。歷史課變成了我班的“休閑課”,很多學生不聽課,要么低頭打瞌睡,要么做數學題或背英語單詞,課堂一團亂。林老師大多對下面的情況視而不見,眼睛望著天花板自顧自講下去。
偶有例外。有次林老師大概在家里受了媳婦的氣(全校師生都知道他是一直受氣的),在課堂上突然發了火,一掌拍向講桌,皺著眉頭對我們說,信不信我把你們踹出去?
“不信。”有男生在下面起哄。
“誰接的話把?有能耐站起來說。”
沒人站起來。他氣得半天說不出話來。
林老師離過兩次婚,三婚媳婦是我們學校食堂的臨時工,比林老師小十多歲,特別潑辣,夫妻吵架常不管不顧下死手。林老師帶傷上課是常態,要么胳膊被撓一道血口子,要么臉被抓得橫一條豎一道。他看起來倒不以為意,有時用創可貼胡亂粘一下,有時就裸著傷口來來去去。學生們對他沒有絲毫同情,背地里覺得他枉為男人,瞧不起他。
我們高三時換了歷史老師,林老師慢慢就淡出了同學們的談論圈子。
沒想到幾年后我跟林老師由師生變成了同事,由同事變成了搭檔。
我班的歷史課代表是個老實又靦腆的女孩,頗討林老師喜歡。林老師閑來無事喜歡在自習課到班級溜達一圈,給課代表布置點小任務。我注意到,每次林老師進教室,總有學生竊竊私語,課代表則臉漲得通紅,一副惱羞成怒的樣子。
不久后,有天上歷史課,林老師提問課代表回答問題時略去了姓,直接說“小麗同學,請你回答這個問題”,學生們哄堂大笑。課代表氣呼呼站起來,怒懟道,“我有姓,我不姓小,我姓趙。”
在課堂外,關系比較好的師生之間,比如班主任與自己班學生之間,任課教師與課代表之間,老師喊學生小名倒并不是什么新鮮事,不過是師生之間表達親昵的一種常態而已。但在課堂上,老師喊學生小名或外號的情況則極為少見,尤其異性師生之間,更顯尷尬,不僅會將涉事學生置于難堪處境,更容易引起其他學生的誤解和反感。盡管學校對此并無硬性規定(或許壓根覺得無需規定),但這似乎早已成為師生之間約定俗成的“潛規則”。
課代表堅決要求辭職。
辦公室老師們議論紛紛,有老師說曾見林老師單獨找女學生在談話室談話,說些“聽老師的話,你成績還能提高”之類的廢話;有老師說林老師多年來上課只愛提問女學生,對男學生不聞不問;還有的老師“嗤”的一聲,嘴角鄙夷地一撇,不搭話,只意味深長地冷笑。
我給林老師換了個男課代表,他試圖跟我解釋點什么,但終于什么也沒說。
“關心”與“猥褻”,“正當”與“越軌”有時邊界模糊,很難判斷,況且,我的判斷毫無用武之地。
那一年校長強奸學生、老師猥褻學生的案件仿佛集中式爆發,并在網絡上快速發酵,“校長”立時成為“貶義詞”。我曾在360搜索上輸入“校長猥褻學生”,相關搜索結果70300個,而輸入“校長強奸學生”,相關搜索結果增加為82300個,輸入“老師猥褻學生”,相關搜索結果則為115000個……
各學校很快出臺了相應的規章制度,其中一條大同小異——任何教職員工不得將異性學生留在教室、宿舍或其他僻靜場所進行單獨談話。心理教育、激勵教育、賞識教育、因材施教的大門被通通堵死,即便矯枉過正,這項規定就真的能防患于未然嗎?
從那以后,林老師成為一個愈加沉默的人。
3
教我班外語的女教師剛剛研究生畢業,懷抱著一腔教育理想,從書本上學到的教育理念在她胸腔小鹿般跳躍,急于在現實中操練驗證。
“我會跟你們成為朋友,做你們的知心姐姐。”她的宣言得到了高一孩子們的熱烈響應。她跟學生一起跑操,一起打排球。周末,跟學生一起約看電影,泡吧,去KTV。
她的課堂饒有趣味,氣氛活躍。從導語設計到提問方式,從課堂小結到作業布置,環環相扣,嚴謹自然。為了直觀性和趣味性,她課余時間用心做PPT。看得出來,她非常熱愛自己的職業。
開學不久,學校組織了“青年教師匯報課”活動,她得了年級一等獎。在隨后舉行的“教師基本功大賽”中,她又得了板書和教學設計的一等獎。領導們都覺得她簡直天生就是當老師的料。
她信心倍增,身上每天都帶著光芒。
然而,很快,一次又一次的月考成績卻狠狠地打了她的臉。我班的外語成績穩居年級倒數第一。每次年級開月考總結會,無論是平均分還是名次段,她都在被批評的“黑名單”里。有的老教師或明言或暗語提示她,與學生過于親近隨意,勢必被動;課堂花哨形式化,影響效率。她心里對這些勸告不以為然,反以為老教師古板迂腐,偏執于講究師道尊嚴,與學生有代溝,跟不上年輕人思維。
盡管她熟諳心理學和教育學,在實際教學中卻派不上多大用場。她的課堂雖互動熱鬧,卻疏于課后反饋和鞏固。她布置的作業不多,批改又少,課余忙于做課件,對不完成作業和課前提問不會的學生不忍責罰,學生一撒嬌求放過,她就主動退讓。學生自習課習慣性先把外語撇到一邊,忙乎其他科作業。
她沒有想到學生最是“欺軟怕硬”,她眼看著好言相勸比不過諷刺挖苦,諄諄教誨比不過硬性罰寫,心里很是困惑、失落。而學校關注的唯有成績、排名。成績與生源掛鉤,排名與榮譽相關。課上得再好,沒有成績一切都是枉然。
高一期中考試,我班的外語平均分被同組第一名拉了十五分。領導給她派了外語組成績第一名的老教師做她師傅,專門帶她。學校要求她的講課進度比老教師慢一兩節,聽一節課仿講一節課。老教師全日制師專畢業,函授本科。課堂從不給學生笑臉,除了知識點絕不說一句廢話,學生提問答不上來的,整節課站著聽課。至于小測不合格或作業未完成的,則一律罰寫。她起初聽到老教師說,錯的單詞罰寫一百遍時,竟還懷疑自己耳朵聽錯了。她不解且不屑,教育怎能如此簡單粗暴、機械僵化呢?可不解歸不解,不屑歸不屑,成績結結實實擺在那兒,由不得她不服。
她越來越沉默了。理想撞了南墻,年輕的她成了霜后的月季,心不覺變得冷硬。
一旦深諳所謂教學捷徑,學生成績不提高幾無可能。她再也不耗時耗力做課件了,課前固定小測,小測不合格的學生大課間一律帶到實驗室“過篩子”(一個一個提問)。嚴肅代替了和悅,懲罰代替了教育。臨近期末前的一次月考,我班外語成績突飛猛進,雖仍倒數第一,但與其他班距離明顯縮小至可以忽略不計。她嘗到了甜頭,變本加厲起來。動輒大面積罰寫一百遍,寫檢討、寫試卷分析、寫失分原因、寫提高措施更是家常便飯。
有天早課,我剛進樓,就聽到一陣變了調的尖利訓斥聲。待走到我班門口,發現她一手叉腰,一手抵在我班一名男生眉間,點了男生腦袋幾下后,順勢變成拳頭,連捶男生胸口。男生被推得一個趔趄,頭撞在墻角,疼得他“啊”一聲捂住腦袋。我趕緊詢問緣由,說是男生英語早讀時做數學題,她批評時反遭惡聲頂撞。男生也覺委屈,數學題做到一半,思路被老師粗暴打斷,自是不耐煩。我勸她回辦公室,男生交由我處理。我安慰了男生幾句,問他有沒有受傷,他說無妨。
我隱隱覺得不安。
第二天一早,男孩父母找到校長室,說孩子被英語老師打得胸口痛,直喊惡心頭暈,頭還鼓了個包,要求學校嚴肅處理,否則就告到教育局。我與男孩家長雖并不熟,但確信對方并非無理取鬧之人,定是看到孩子受了委屈和傷害內心難掩憤怒,從家長的角度,我感同身受。
校長硬著頭皮百般安撫家長,她則驚慌失措,“啪啪”掉眼淚,畢竟還是個比學生大不了幾歲的年輕人,心理承受能力有限。家長看到她哭得厲害,也就消了氣。
事情不了了之。只是她漸漸對教學失了熱情,我常見她課余時間一個人坐在實驗室看書學習。不久,她考上了外地公務員。
責任編輯? ?楊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