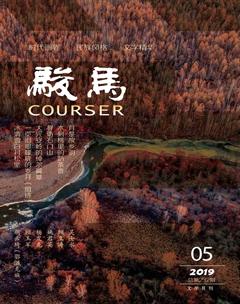于師傅和他的那掛大車
劉朝江
一年仲秋季節,我從外地出差回林業局,突然得知老于師傅病故了,真遺憾未能親自為他老人家送葬。
于師傅是我在林場二十多年的老鄰居,他很平凡,很普通,以至于沒有留下任何文字記載。然而,他又極不平凡,極不普通,甚至應該永載史冊。因為,他是內蒙古大興安嶺林區的一名早期創業者,是林業企業的一位奠基人,是數百名支援林區開發建設榮轉革命軍人的優秀代表。他雖然長眠于內蒙古大興安嶺的綿綿群山之中,只有那滿山的蒼松與他常年相伴,我想,從他登上這高高的大興安嶺山脈,他就將根牢牢地扎在了這茫茫的林海雪原里,就將全身心的摯愛和血汗都傾注給了這里,“獻了終身,獻子孫”,“老死青山不留墳,終有青山伴我眠”,如果在天有靈,于師傅他不會感到孤獨和遺憾。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內蒙古大興安嶺林區正處在開發創建時期,生產和生活條件非常艱苦,當時我與于師傅同在距局址約八里路的林場居住。林場當時沒有機械運輸車輛,全場千余口居民的衣食等日用品,全靠僅有的一掛由三匹馬拉的大板車,負責從局址往林場運輸。
于師傅從曾參加過抗美援朝的部隊轉業,同許多戰友一起來到林區。由于在部隊時就同馬打交道,對擺弄馬有一套業務,自從采伐作業砸傷了腰以后,他就被安排當上了林場的車老板。
當年,于師傅才二十多歲,風華正茂,血氣方剛,為人直率,干活干脆利落。他把三匹馬裝扮得十分漂亮,馬韁繩、籠頭、搭腰一律是銅環花腰雙穗,每匹馬頭上都戴著銅鈴。于師傅趕車大鞭子的鞭梢上,總系著鮮紅的棕繩鞭穗。夏天,他穿一身勞動布工作服,胳膊上套著套袖,胸前扎一件很長的灰色帆布圍裙。冬天,他頭頂貉皮棉帽,腳蹬一雙黑色長筒毛氈靴,身披白茬大皮襖,穿著厚厚的粗布棉褲,最惹眼的是他腰里別著的一尺多長的旱煙袋,紅瑪瑙的煙嘴,黃銅的煙鍋,黑羊皮帶穗的煙口袋,一年四季不離身。那時候,于師傅的大車每到一處,他都會抽空來上一口關東煙兒,招引許多路人駐足觀賞。
于師傅的大車,曾給林區小鎮帶來無限歡樂。那時,林區文化生活非常貧乏,沒有秧歌沒有戲,也沒有什么娛樂設施,山場居民最大的文化享受,就是盼望每月能看上一場露天電影。于師傅接放映隊的大車還沒有進村,全村的人們都已經知道了,孩子們都早早在村口等候了。
林場場部大院一側有一個“井”字形的木架子,那是掛銀幕的地方。天還沒黑,孩子們已從家里搬來板凳、木墩、板皮等占座位,各家也都早早吃完晚飯,陸續來到大院里等著,大人們借此機會嘮嘮家常;孩子們聚在一起亂耍,整個大院就像過年一樣熱鬧。
天完全黑下來了,人們的眼神都凝聚在銀色的映幕上,夜幕中星光閃爍,遠處的群山密林已經隱去,影片的聲音引發出群山和諧的回響,大家完全沉浸在影片的故事之中,時而歡笑,時而悲憤,時而竊竊私語,時而歡呼雀躍。每次,無論刮風下雨,人們一直到“劇終”還遲遲不肯離去。
電影放映完以后,當人們已經進入甜蜜夢境的時候,于師傅正在夜幕中,趕著他的大車往局址送放映隊,大興安嶺的夏天夜很短,等到大車再返回林場時,又一個黎明已經來臨了。
于師傅的大車,也曾給林場小鎮送來物質享受。當時林場居民所用的油鹽醬醋茶,一律靠大車從局址往林場運送。林場人多車少,一年三百六十多天,天天馬不停蹄,越是過節越忙乎。
記得有一年秋季,連陰雨足足下了五天,還沒有停的意思,林場糧店已無米可售了。于師傅只好趕著大車,冒著雨到局里拉糧,那天正趕上跟車的徒弟家里有事沒上班,在拉糧回來的路上,有一座涵洞被從山上下來的洪水沖垮了。車上裝有五十多個大麻袋,每袋都裝有180斤的玉米米查子,天生倔強的于師傅,硬是把麻袋從車上卸下來,一袋一袋背過涵洞,又一袋一袋重新裝回大車上,星夜趕回了林場。
于師傅自部隊轉業來林區,就將根牢牢地扎在了大興安嶺的山林中,成家后,相繼養育了兩兒兩女,遺憾的是次子生下來就患小兒癡呆癥,不僅有語言障礙,而且走路也一瘸一拐的。于師傅對呆兒子特別關愛,每次到局里出車回來,都為呆兒子捎點好吃的。誰知“船破偏遇頂頭風”,呆兒子長到13歲那年,寒冬臘月的一天傍晚,突然走失了,正當老兩口焦急尋找的時候,林場突然有一少婦難產,急需到林業局局址大醫院搶救,當場領導找到于師傅時,他二話沒說,就冒著漫天大雪,趕著大車向局址奔去。等到半夜返回林場后,于師傅又急匆匆同鄰居們在村子四周深一腳淺一腳地繼續尋找他的呆兒子。第二天早上9點多鐘,于師傅在距林場十多里運材路的一個涵洞里終于找到了走失的呆兒子,孩子當時已經處于昏迷狀態,手指和腳趾都凍成了冰棍,后來在醫院做了截肢手術,呆兒子舊疾未除又添新患。
據熟人講,在于師傅去世時,呆兒子一直守在于師傅身旁,一連三天都沒有吃東西。還聽說,在為于師傅穿壽衣的時候,人們發現于師傅因長年從事重體力勞動,積勞成疾,受傷的腰椎嚴重變形,身上還始終穿著在天津醫院配的“鐵支架背心”。
于師傅離我們而去了,他就像在寒風中赫然倒下的一棵枯老的落葉松樹,只有山林中那厚厚的植被才感覺到他的存在,才領悟到他對青山綠樹的實在意義。于師傅的那掛大車,也滿載著主人的畢生情感和希冀,駛離了那個令人刻骨銘心的時代……
在于師傅去世的第一年春節前,我到山場撫育伐小隊去慰問一線生產職工,遇到了于師傅的長子,真沒想到,他也干起了同馬打交道的差事,在用馬爬犁為小隊集材。緊握著“小于師傅”那雙粗壯且布滿老繭的手,看著他那憨厚黝黑的面孔,我仿佛又看到了年輕時的老于師傅,我一時不知道用什么話語去安慰他,看著那漸漸遠去的馬爬犁,淚水模糊了我的雙眼,我仿佛又看到了當年老于師傅的那掛大車……
我在心里默默地祝福:但愿“小于師傅”他們這一代,別再像老于師傅那樣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