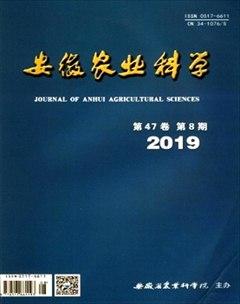糧食主產區耕地保護補償意愿及其影響因素研究
黃烈佳 程佳 張波清
摘要 [目的]為了更好地完善耕地保護補償的有效性與公平性。[方法]以糧食主產區為例,運用305份地方國土管理人員調查數據,采用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方法,系統分析了國土管理人員對耕地保護補償意愿及其影響因素。[結果]地方國土管理人員的耕地保護補償意愿偏低;經濟發展狀況、農業建設條件、耕地保護任務和耕地保護認知對耕地保護補償意愿的重要性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效應;耕地生產效益對耕地保護補償意愿的重要性具有反向影響效應;經濟發展狀況和農業建設條件因子對耕地保護補償意愿占據主導作用。[結論]為保證糧食主產區耕地保護經濟補償的有效性,建議關注地方國土管理人員,提高其耕地保護補償認知,結合耕地保護任務,制定差異化的耕地保護補償政策,重視各地區經濟發展狀況和農業建設條件,降低耕地保護難度。
關鍵詞 耕地保護;補償意愿;地方國土管理人員;結構方程模型;糧食主產區
中圖分類號 F323.2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517-6611(2019)08-0231-06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19.08.061
Abstract [Objective] To better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and fairness of the compensation funds for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Method] The study takes the main grainproducing area as an example,uses 305 local land managers survey data,combin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willingness of land managers to participate in compensation for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Result] The study concludes:The low willingness of local land managers to protect and compensate for cultivated l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tus,agricultural construction conditions,farmland protection tasks,and cognizance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farmland protection and compensation participation; The benefit of cultivated land production has a reverse effect on the importance of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and compensation willingnes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gricultural construction conditions play a leading role in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and compensation.[Conclusion] In order to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economic compensation for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in the main grainproducing areas,it is recommend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land and state management personnel and farmers,establish a reasonable compensation mechanism,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ditions and agricultural construction conditions in various regions,so as to reduce the difficulty of farmland protection.
Key words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Compensation willingness; Local land management cadre; SEM; 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
糧食主產區在保障國家糧食生產和安全中的貢獻巨大,但其發展也面臨諸多資源約束[1]。近年來,工業化、城市化的高速發展,耕地“非農化”、農地“非糧化”強烈沖擊著耕地資源和糧食安全。因此,建立糧食主產區耕地保護補償機制逐漸成為政府和學界的共識。自2005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建立糧食主產區利益補償機制”以來,學術界在糧食主產區的補償機制、耕地生產力、糧食安全等方面進行了大量研究[2-9],付若嵐等[10]認為,當前糧食主產區的農地利用效率較低,謝向向等[11]認為要重點推進主產區的土地整治,提高新增耕地質量和綜合生產力,吳玲等[12]實證分析了糧食主產區和主銷區的經濟發展差距,提出必須實施糧食主產區利益補償。在耕地保護補償機制上,國內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耕地保護補償制度的建立,余亮亮等[13]、牛海鵬等[14]、李林等[15]分別從經濟補償和生態補償制度為中國耕地保護補償機制研究指明了具體的方向;二是耕地保護補償模式的研究,如趙凱[16]的“三級三循環”模式、周小平等[17]的“雙縱雙橫”模式為構建耕地保護補償模式提供了典型借鑒;三是耕地保護補償標準測算,如牛海鵬等
[18]、陳會廣等[19]、廖和平等[20]、雍新琴等[21]、曹瑞芬等[22]、周小平等[23]的研究為耕地保護補償測算提供了理論參考。綜上,前人對糧食主產區利益補償、糧食安全及耕地保護補償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這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但已有研究主要從農戶和政府的角度對耕地保護意愿進行了探討,而農戶對于補償政策的理解較為狹隘,更多的是只關心自身利益,地方國土管理人員作為耕地保護政策的直接執行者,其對耕地保護補償的認知更加公平宏觀全面[24],決定了耕地保護政策實施的有效性。因此,基于以上現實背景,采用問卷調查的方式,系統研究糧食主產區的地方國土管理人員對耕地保護補償的意愿及其影響因素,為調動糧食主產區發展糧食生產和提高耕地保護補償效率提出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議,也為耕地保護補償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和研究內容。
1 數據來源、研究區域及研究方法
1.1 數據來源
課題組通過問卷設計,有針對性地向地方國土管理人員發放問卷的方法來獲取研究數據。調研范圍包括糧食主產區、歷史文化旅游景區等31個省市(區 ),調研時間為2016年3—9月,課題組共發放問卷787份,其中電子問卷187份,紙質問卷600份。回收問卷767份,整理得到有效問卷563份,有效率為73.4%。筆者選取糧食主產區的305份問卷數據進行研究。調查問卷的內容主要由3個部分組成:第1部分是有關國土管理人員的基本情況,包括調查對象的工作性質、工作區域及該區域的農業生產條件、區位、生態環境、經濟產業特征及耕地保護情況等內容;第2部分是有關耕地保護補償資金分配方式、影響因素;第3部分是有關耕地保護分配對象以及不同對象的補償方式等內容。第2、第3部分內容均采用Likert(李克特)量表,按照9點正向積分法統計(1-9分別表示非常不重要,很不重要,比較不重要,有點不重要,一般,有點重要,比較重要,很重要,非常重要)。
1.2 研究區域
我國糧食主產區主要包括長江中下游地區5省(蘇、贛、皖、湘、鄂),黃淮海(冀、魯、豫)3省,東北3省(黑、吉、遼)以及內蒙古、四川2省,共13個省份。糧食主產區是我國農業生產的重要基地,2003—2017年糧食總產量增加43.4%,年均增幅2.89百分點,其中糧食主產區的糧食產量增加了48.2%,年均增幅3.23百分點(圖1)。糧食主產區作為我國的糧倉,為國家貢獻了約75%的糧食,但自身的經濟發展較為落后,據有關調查數據顯示,糧食主產區中的國家級貧困縣占1/5,糧食促產將拉大地區經濟差異,因此為了協調糧食生產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中央一號文件多次提出關于“完善糧食主產區的區域發展綜合補貼政策”,為研究提供了典型區域。
1.3 研究方法
1.3.1 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是指從眾多的可觀測變量群中將相同本質的變量歸入幾個有代表性的因子,并能最大限度的解釋原有觀測變量的信息。這里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對量表的信效度進行檢驗,提取影響耕地保護補償資金分配的主要因子。
1.3.2 結構方程模型。
結構方程模型是在相關理論基礎上,用合適的線性方程系統探索事物間因果關系并將這種關系用因果模型、路徑圖等表述,一般由測量模型和結構模型組成。結構方程模型中變量可分為觀測變量和潛在變量,觀測變量是指能夠直接獲取到數據的變量,潛在變量是指無法直接觀察到,但可以通過外在的、可觀測的指標來間接測量的變量[25]。測量模型用來解釋潛在變量與觀測變量之間的關系。結構模型用來解釋外生潛在變量與內生潛在變量之間的關系。技術路線如圖2。
2 實證分析
2.1 變量選擇
為研究糧食主產區耕地保護補償意愿及影響因素,筆者基于國土管理人員對耕地保護補償意愿及其影響因素指標評價得分的基礎上,選取以下20個觀測變量,變量描述如表1。
從表1可以看出,糧食主產區地方管理人員對于耕地保護補償的意愿偏低,對其影響因素得分評價較為一致,波動較小,這也體現了對地方國土管理人員調查問卷信息的真實性和宏觀性高于農戶。
2.2 信度和效度檢驗
利用SPSS 20.0對數據進行信度檢驗,結果顯示:耕地保護補償意愿影響因素變量(X1-X14)、耕地保護認知變量(W1-W3)、耕地保護補償認知變量(Y1-Y3)的基于標準化項 Cronbachs α值范圍在0.73以上,KMO值都在0.69以上,Bartlett 球形檢驗統計量的 Sig.<0.00(表2),可以看出數據的信度較高。且調查問卷在有關專家的指導下經過多次討論修改完成,問卷實際檢測效果與原設想也基本一致,問卷效度較高。綜上,可以認為各個變量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性,適合進行因子分析。
2.3 探索性因子分析
2.3.1 耕地保護認知及耕地保護補償意愿認知。
如表3和表4分別為利用因子分析來提取耕地保護認知和耕地保護補償意愿變量的公因子,采用特征值大于1的原則來確定因子的個數,根據累計方差貢獻率提取1個因子,這一個分公因子別解釋了方差變異中的69.394%和66.521%,包含了大部分信息。
2.3.2 耕地保護補償認知影響變量因子分析。
基于耕地保護認知及耕地保護補償意愿認知分析的基礎上,運用主成分分析法對耕地保護補償意愿的14個影響變量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其中,所有指標變量的標準因子載荷值均大于0.5,4個公共因子對整體調查問卷的解釋率達到63.82%,公因子提取有效,其成分矩陣如表5。
因子分析結果表明,14個指標變量可提取出4個公因子,因子1包括生態環境、糧食產量、耕地質量、耕地保護狀態,因子2包括總體經濟狀況、是否為規劃重點發展地區、農民富裕程度、耕地占有量,因子3包括農作物生長環境、農田及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投入情況、農產品銷售、運輸條件,因子4包括耕地破壞與違規占用情況、承擔耕地保護補償工作的情況、耕地保護任務量。根據變量共性和研究主題,可以用耕地生產效益、經濟發展狀況、農業建設條件、耕地保護任務4個因子作為耕地保護補償意愿影響因子。
參考文獻
[1]陳璐,胡月,韓學平,等.國家糧食安全中主產區糧食生產及其貢獻的量化對比分析[J].中國土地科學,2017,31(9):34-42.
[2] 魏后凱,王業強.中央支持糧食主產區發展的理論基礎與政策導向[J].經濟學動態,2012(11):49-55.
[3] 宋戈,柳清,王越.基于耕地發展權價值的東北糧食主產區耕地保護補償機制研究[J].中國土地科學,2014,28(6):58-64.
[4] 叢勝美.糧食主產區利益補償機制研究[D].北京:中國農業大學,2016.
[5] 張鵬巖,龐博,何堅堅,等.耕地生產力與糧食安全耦合關系與趨勢分析:以河南省為例[J].地理科學,2017,37(9):1392-1402.
[6] 丁文恩.新常態下糧食安全隱憂及保障機制研究[J].農村經濟,2016(9):20-24.
[7] 楊祥祿.強化農業資源保障能力與確保糧食生產穩定發展:以四川省為例[J].農村經濟,2015(4):20-24.
[8] 李政通,姚成勝,梁龍武.中國糧食生產的區域類型和生產模式演變分析[J].地理研究,2018,37(5):937-953.
[9] 康雄華,黃烈佳,宋彥.糧食安全視角下的中國農地資源“非糧化”傾向及其影響因素分析[C]//中國土地資源開發整治與新型城鎮化建設研究.北京:新華出版社,2015:266-275.
[10] 付若嵐,朱小盼.糧食主產區農地利用狀況分析[J].當代經濟,2017(34):77-79.
[11] 謝向向,汪晗,張安錄,等.土地整治對中國糧食產出穩定性的貢獻[J].中國土地科學,2018,32(2):55-62.
[12] 吳玲,劉騰謠.糧食主產區實施利益補償的價值判斷與政策導向[J].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2017,38(7):1-9.
[13] 余亮亮,蔡銀鶯.耕地保護經濟補償政策的初期效應評估:東、西部地區的實證及比較[J].中國土地科學,2014,28(12):16-23.
[14] 牛海鵬,張杰,張安錄.耕地保護經濟補償的基本問題分析及其政策路徑[J].資源科學,2014,36(3):427-437.
[15] 李林,李海燕.耕地保護生態補償現狀及政策建議[J].現代農業科技,2015(11):240-241.
[16] 趙凱.論“三級三循環”耕地保護利益補償模式的構建[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2,22(7):120-126.
[17] 周小平,柴鐸,宋麗潔.“雙縱雙橫”:耕地保護補償模式創新研究[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10(3):50-56.
[18] 牛海鵬,王文龍,張安錄.基于CVM的耕地保護外部性估算與檢驗[J].中國生態農業學報,2014,22(12):1498-1508.
[19] 陳會廣,呂悅.基于機會成本與Markov鏈的耕地保護補償基金測算:以江蘇省徐州市為例[J].資源科學,2015,37(1):17-27.
[20] 廖和平,王玄德,沈燕,等.重慶市耕地保護區域補償標準研究[J].中國土地科學,2011,25(4):42-48.
[21] 雍新琴,張安錄.基于糧食安全的耕地保護補償標準探討[J].資源科學,2012,34(4):749-757.
[22] 曹瑞芬,張安錄,萬珂.耕地保護優先序省際差異及跨區域財政轉移機制:基于耕地生態足跡與生態服務價值的實證分析[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5,25(8):34-42.
[23] 周小平,李曉燕,柴鐸.耕地保護補償區域間分配的指標體系構建與實證:以福州市為例[J].經濟地理,2016,36(5):152-158.
[24] 周小平,李小天,黃烈佳,等.耕地保護補償資金分配認知及其影響因素探究:基于全國563份地方國土管理人員調查問卷的實證分析[J].中國土地科學,2018,32(2):6-11.
[25] 孫連榮.結構方程模型(SEM)的原理及操作[J].寧波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5,27(2):31-34,43.
[26] 王安濤,吳郁玲.農戶耕地保護補償意愿的影響因素研究[J].國土資源科技管理,2013,30(1):78-83.
[27] 馬文博.糧食主產區農戶耕地保護利益補償需求意愿及影響因素分析:基于357份調查問卷的實證研究[J].生態經濟,2015,31(5):97-102.
[28] 胡蓉.耕地保護的經濟補償研究[D].重慶:西南大學,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