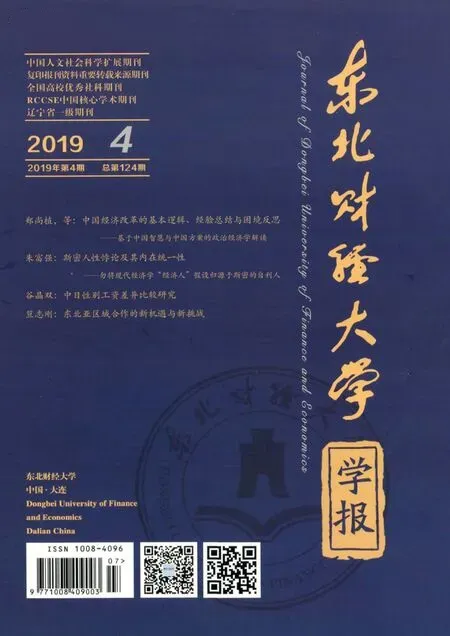財會與法律背景董事對企業違規行為的影響
周 博
(東北財經大學金融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5)
一、引 言
企業違規行為涉及虛構利潤、虛列資產、虛假記載、推遲披露、重大遺漏、欺詐上市、違規買賣股票、操縱股價以及違規擔保等方面,這些違規行為與財務、會計以及法律領域緊密相關。完善的公司治理機制能夠有效抑制企業違規行為[1]-[2]。董事會是公司治理的核心[3],董事會成員依靠自身的專業知識背景,在董事會決策中發揮著信息咨詢與監督約束的作用[4]。隨著我國企業管理制度的不斷完善,財會與法律背景董事在董事會中的比例越來越高。那么,作為約束企業行為的重要力量,財會與法律背景董事在企業違規行為中扮演著什么角色?是發揮了行業專長抑制了企業違規行為,還是與企業內部合謀助長了企業違規行為?考慮到獨立董事與執行董事在董事會中的角色差異,具有財會與法律背景的執行董事與獨立董事在企業違規行為中是否具有同樣作用?此外,董事會(主要是針對執行董事)的股權激勵以及獨立董事工作地點與上市公司地址的一致性是否會影響上述作用的發揮?
與現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貢獻體現在以下三點:首先,現有研究主要從諸如董事會規模、獨立董事比例、獨立董事津貼、兩職合一等董事會特征角度研究企業違規行為[5],鮮有研究從董事專業知識背景角度研究企業違規行為。本文從董事的財會與法律背景角度考察其對企業違規行為的影響,拓展了從董事會特征角度研究企業違規行為的研究范疇。并且,董事會作為公司治理的核心,其主要依托成員的專業知識背景發揮作用[6],因而相比其他董事會特征的研究視角,從董事的財會與法律背景視角研究其對企業違規行為的影響具有更為嚴謹的理論支撐。其次,現有關于董事會特征與企業違規行為的研究主要基于歐美國家資本市場的經驗證據,由于歐美國家資本市場運行機制更為完善,法律機制更為健全,因而以歐美國家資本市場為經驗證據并不適合于法律制度基礎較為薄弱的新興市場。現有研究發現,在法律機制較為完善的歐美國家資本市場中,董事會能夠有效抑制企業違規行為[7],而在我國的新興資本市場中,諸如獨立董事比例等董事會特征對企業違規行為不僅沒有抑制[5],反而發揮了促進作用[8]。本文以財會與法律背景董事為視角,發現財會與法律背景董事對企業違規行為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這為新興市場國家關于董事會與企業違規行為的研究將豐富新的內容。最后,現有研究表明,董事成員主要依托自身專業知識背景發揮作用[9]。比如,Güner 等[10]發現具有銀行背景的董事能夠提高企業債務融資的比例;劉浩等[11]發現銀行背景的獨立董事能夠改善企業的信貸融資,特別是在金融市場不發達的地區其作用更為顯著。本文主要考察財會與法律背景董事對企業違規行為的影響,研究結論將豐富關于董事會成員專業背景影響企業行為的研究范疇。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董事會特征與企業違規行為
作為股東與管理層之間的聯結紐帶,董事會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其對于約束和規范企業行為具有重要作用[3],因而關于影響企業違規行為因素的文獻主要以董事會特征為切入點進行研究。然而,國內類似的外關于董事會特征與企業違規行為之間關系研究的結論存在差異。國外基于歐美等國家數據的研究發現,董事會能夠抑制企業違規行為。Beasley[12]研究發現,董事會中獨立董事比例越高,企業發生財務方面違規行為的概率越小;董事會規模越大,企業發生財務方面違規行為的概率會越大。Dechow等[13]研究發現,當董事會由管理層主導,并且董事長與CEO二職合一時,企業違規行為發生概率越大;當董事會設置審計委員會時,企業違規行為發生概率越小。Klein[7]和Uzun[14]研究發現,董事會中獨立董事比例越高以及設置審計委員會,都會降低企業違規行為發生概率。然而,國內研究沒有得到相同的結論。比如,蔡志岳和吳世農[5]研究發現,董事長與總經理二職合一能夠顯著降低企業違規行為概率,而董事會規模擴大將增加企業違規行為概率,獨立董事比例以及審計委員會的設置會降低企業違規行為發生概率,但統計上卻不顯著。陳維政等[15]研究發現,獨立董事津貼與企業違規行為正相關,即獨立董事獲取的津貼越多,企業違規行為概率越大。鄧可斌和周小丹[8]研究發現,較高的獨立董事比例顯著增加了企業違規行為概率,說明獨立董事未能有效抑制企業違規行為。
法律制度和市場環境不同是國內外研究結論差異的重要原因。歐美國家的法律制度較為完善,資本市場較為發達,良好的市場環境有助于董事會發揮監督約束企業行為的作用。而在新興的資本市場,法律制度不甚健全,市場環境也有待完善,這些都不利于董事會對企業行為進行監督[16]。因此,不能照搬西方學者的研究結論,需要在我國情境下對董事會特征與企業違規行為之間關系進行研究。此外,現有研究主要關注諸如董事會規模、獨立董事比例等董事會特征,忽略了董事自身的特征,表現為“只見董事會,不見董事”,而董事會發揮監督約束或信息咨詢作用的真正主體是董事,因而董事特征將是更有效解釋企業違規行為的關鍵因素。鑒于董事主要依靠自身專業知識背景發揮咨詢與監督作用[4-8],企業違規行為多是違反財務、會計等方面的法律法規,本文主要考察財會與法律背景董事對企業違規行為的影響。此外,鑒于獨立董事和執行董事角色的差異,本文還進一步考察財會與法律背景獨立董事和執行董事對企業違規行為影響的差異。
(二)財會與法律背景董事與企業違規行為
董事成員依靠自身專業知識為企業提供信息咨詢與監督約束的服務[4]。根據Demb和Neubauer[9]的調查數據,董事在其作為專家所擅長的領域為企業經營提供指導。本文認為,財會與法律背景董事可通過監督約束與信息咨詢兩種途徑對企業違規行為產生影響。監督約束是董事的重要職能,也是企業引入董事制度的初衷。然而,學術界近年來對董事監督功能的質疑卻越來愈多[17]。一方面,董事是由大股東或高管提名任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他們不愿意董事在董事會中發出不同的聲音,因而董事更像是他們的“朋友”,即使依靠自身的專業知識,財會與法律背景董事能夠發現一些問題,卻也很難有效發揮監督作用,甚至其投票僅僅是“橡皮圖章”。另一方面,董事的監督需要一定的信息,但有些董事(特別是獨立董事)很難獨立地獲取這些信息,其中能夠獲取信息的董事往往與高管聯系緊密,不愿意實施有效監督,而與高管關系不甚緊密的董事(特別是獨立董事)難以獲取信息,無法實施有效監督[13]。
董事會中包括獨立董事和執行董事。就獨立董事而言,在我國法律制度仍不完善的情況下,不利于其監督作用的發揮。比如,唐清泉和羅黨論[18]通過調查問卷研究發現,51%的受訪獨立董事認為法律制度不完善是影響其發揮作用的重要原因。并且我國法律對于獨立董事監督失職的懲罰較輕[16],這也弱化了獨立董事的監督意愿。因此,我國企業更傾向出于信息咨詢目的任命獨立董事[13],從而獨立董事更像是大股東或高管的“朋友”[8]。一些研究表明,獨立董事不僅未能顯著減少企業違規行為,甚至助長了企業違規行為。另外,由于我國法律法規對違規企業或個人的懲罰較輕,增大了財會與法律背景獨立董事與大股東或高管合謀違規的風險。在法律違規成本較低的情況下,作為大股東或高管的“朋友”,財會與法律背景獨立董事可能會利用自身的專業知識為大股東或高管出謀劃策,進而增加了企業違規行為。
相對于獨立董事而言,執行董事的獨立性更低,其對企業違規行為的監督作用更弱,導致既使執行董事具備財會與法律背景,也很難對企業違規行為實施有效的監督,并且由于其在企業擔任其他職務,更容易受到來自高管的壓力。相對于其他類型執行董事而言,財會與法律背景執行董事具備更多的專業知識,更可能應高管或大股東的要求為企業違規行為提供“指導”。由于法律對違規企業或個人的處罰成本較低,降低了財會和法律背景執行董事的違規成本,因而他們更傾向參與企業違規行為的謀劃,從而使企業更容易發生違規行為。依據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設:與不擁有財會與法律背景董事(包括獨立董事和執行董事)的企業相比,董事會中擁有財會與法律背景董事(包括獨立董事和執行董事)的企業更可能發生企業違規行為。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樣本與數據來源
為了考察董事會中財會與法律背景董事對企業違規行為的影響,本文選取2007—2016年滬深A股非金融類違規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企業違規行為包括虛構利潤、虛列資產、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推遲披露、重大遺漏、披露不實(其他)、欺詐上市、出資違規、擅自改變資金用途、占用公司資產、內幕交易、違規買賣股票、操縱股價、違規擔保、一般會計處理不當以及其他等類型。在數據庫中剔除缺失數據后,共獲得770個違規企業觀測數據。為了控制樣本自選擇可能導致的內生性問題,本文采取構造參照組的研究方法[5],為每家違規企業選取未違規企業組成對照樣本組。選取標準為樣本期內與違規企業處在同一行業且資產規模最為接近的未違規企業。配對后樣本共包括1 540個觀測值。本文所使用數據均來自國泰安CSMAR數據庫。
(二)回歸模型與變量說明
本文使用模型(1)檢驗財會與法律背景董事對企業違規的影響:
Fraud1(Fraud2、Fraud3)=a0+a1Indirect(Direct)+a2Control+Yeardummy+ε
(1)
其中,ε為殘差項。Fraud為被解釋變量。由于在一些違規企業在同一年份可能會出現多次違規行為(大于等于2)的情況,并且違規行為嚴重程度也存在較大差異,因而本文借鑒蔡志岳和吳世農[5]、鄧可斌和周小丹[8]研究方法,使用以下三種測量方法:違規概率(Fraud1),樣本期企業是否發生違規,是為1,否則為0;違規頻率(Fraud2),樣本期企業違規次數;違規程度(Fraud3),沒有違規為0,批評、警告為1,譴責為2,罰款及以上為3。
解釋變量為Indirect、Direct,分別表示企業是否擁有財會與法律背景的獨立董事(Indirect)或執行董事(Direct),若擁有則相應變量計為1,否則為0。本文根據國泰安數據庫中上市公司高管的個人簡歷,分別查詢獨立董事、執行董事是否具備財務、會計及法律背景。
Control為控制變量。借鑒蔡志岳和吳世農[5]、陳維政等[15]和鄧可斌、周小丹[8]的研究,本文的控制變量包括公司治理指標、財務指標以及其他指標等。公司治理指標包括:董事會規模(Board),董事會中的董事數量;獨立董事比例(Ratio_Dire),為獨立董事占全部董事的比例;二職合一(Dual),董事長與總經理二職合一時該值為1,否則為0;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Top_Share),第一大股東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財務指標主要包括:企業成長性(Growth),企業營業收入增長率;資產規模(Size),年末企業資產規模的自然對數;資產負債率(Lev),年末企業的資產負債率;總資產收益率(Roa),企業年末凈利潤與總資產的比值。其他控制變量包括:企業是否設置審計委員會(Audit),設置則該值為1,否則為0;企業是否選擇四大會計師事務所(Account),是則該值為1,否則為0。此外,為控制宏觀因素的影響,本文還控制了年度虛擬變量。
由于企業違規行為概率(Fraud1=0,1)是二分類變量,本文采用二分類Probit回歸分析方法;企業違規行為頻率(Fraud2)是連續變量,本文使用OLS回歸分析方法;企業違規行為程度(Fraud3=0,1,2,3)屬于有序分類變量,本文使用排序Probit(OPR)回歸分析方法。
四、回歸結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與樣本分組的差異性檢驗
本文對違規企業(樣本組)與非違規企業(控制組)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并使用t檢驗和Wilcoxon符號秩檢驗,對兩組樣本的均值和中位數進行單變量比較分析。其中,樣本組與控制組的企業規模(Size)的均值t檢驗和中位數Wilcoxon檢驗均不顯著,說明樣本組與控制組的企業規模不存在顯著差異,配對選取的樣本不存在系統性偏差。在財會與法律背景董事方面,無論是財會與法律背景的獨立董事(Indirect)還是執行董事(Direct)的均值,樣本組都顯著大于控制組。獨立董事比例(Ratio_Dire)在樣本組要顯著大于控制組,說明企業的獨立董事比例越高,企業越容易發生違規行為,這與鄧可斌和周小丹[8]的研究結論一致。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

表1描述性統計與樣本分組的差異性檢驗結果
注:*、**、***分別表示在10%、5%和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下表同。
(二)多元回歸分析結果
對財會與法律背景董事與企業違規行為進行回歸分析。在以違規行為概率(Fraud1)為因變量時,財會與法律背景執行董事(Direct)和財會與法律背景獨立董事(Indirect)的回歸系數都顯著為正,說明擁有財會與法律背景董事的企業更容易發生違規行為。在以違規行為頻率(Fraud2)為因變量時,財會與法律背景執行董事(Direct)與財會與法律背景獨立董事(Indirect)的回歸系數也都顯著為正,說明擁有財會與法律背景董事的企業容易發生更多的違規行為。在以違規行為程度(Fraud3)為因變量時,財會與法律背景執行董事(Direct)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具有財會與法律背景執行董事的企業的違規行為程度會更嚴重,而財會與法律背景獨立董事(Indirect)的回歸系數雖然也為正,但沒有達到顯著性水平,說明財會與法律背景獨立董事對企業違規行為程度沒有顯著影響。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
(三)穩健性檢驗
財會與法律背景董事對企業違規行為的影響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內生性問題,正如鄧可斌和周小丹[8]研究所顯示,獨立董事會增加企業違規行為,同時違規企業也會聘用更多的獨立董事,即二者之間存在反向因果關系的內生性問題。為此,本文參照Yeyati等[19]的做法,使用財會與法律背景董事變量的一階滯后值作為替代變量,以此降低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測試結果表明,財會與法律背景獨立董事與執行董事都會增加企業違規行為概率和違規行為頻率,但對于違規行為程度而言,財會與法律背景執行董事有顯著影響,而財務與法律背景獨立董事沒有顯著影響。與前文實證結果一致。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

表3滯后一期財會與法律背景董事與企業違規行為的穩健性檢驗結果
考慮到財會與法律背景獨立董事和財會與法律背景執行董事影響企業違規行為的類型可能有所不同,本文按照違規行為將違規行為程度概率分為違規行為程度較弱的違規行為概率和嚴重的違規行為概率,進一步檢驗不同樣本中財會與法律背景獨立董事與執行董事對于企業違規行為概率的影響。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在模型(1)和模型(2)中,財會與法律背景執行董事(Direct)對于違規程度較弱的違規行為概率和嚴重的違規行為概率都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在模型(3)和模型(4)中,財會與法律背景獨立董事(Indirect)對于違規程度較弱的違規行為概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對于違規行為程度嚴重的違規行為概率影響方向雖然為正,但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平。上述回歸結果意味著,財會與法律背景獨立董事和財會與法律背景執行董事影響企業違規行為的類型存在差異,財務與法律背景執行董事有顯著影響,而財務與法律背景獨立董事沒有顯著影響。與前文實證結果一致。分析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基于違規行為程度分組的穩健性檢驗結果
五、關于董事會股權激勵和工作地點一致性的檢驗
從理論角度來講,董事會是由股東選舉產生,服務于股東利益,并負責監督管理層。為了使董事會的利益與股東利益保持一致,公司治理中一個通行的做法是對董事會實施股權激勵。企業違規行為往往導致企業股價的大幅下挫,降低企業價值,使股東利益受損。既然股權激勵能夠擬合董事會與股東的利益,那么企業對董事會實施的股權激勵是否會減少財會與法律背景董事對企業違規行為的促進作用呢?在本文樣本中,有一半左右的企業對董事會實施了股權激勵,這也為本文考察董事會股權激勵對財會與法律背景董事與企業違規行為之間關系的調節影響提供了現實依據。由于我國企業對董事會實施的股權激勵主要是針對執行董事,鮮見有對于獨立董事實施的股權激勵,因而本文主要考察董事會的股權激勵對財會與法律背景執行董事與企業違規行為之間關系的調節效應。關于董事會股權激勵變量(Share)的數據來自國泰安數據庫,在具體測量時,如果企業為董事會提供了股權激勵,則該變量取值為1,否則為0。回歸結果表明,財會與法律背景執行董事與董事會股權激勵的乘積項(Direct×Share)回歸系數為負,但均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平,說明企業對董事會實施的股權激勵,并沒有削弱財會與法律背景執行董事對企業違規行為的促進作用。回歸結果如表5中模型(1)、模型(2)和模型(3)所示。
與執行董事不同,獨立董事通常不在企業擔任其他職務,因而很多獨立董事的工作地點與上市公司地點不一致。獨立董事僅僅是在公司召開董事會的時候才會出現,導致其參與公司決策程度較低。而工作地點與上市公司地點一致的獨立董事,由于自身所處工作地點的便利性,其參與公司決策的程度會相對較高。并且由于我國獨立董事制度施行相對較晚,運行機制仍有尚待完善的空間。唐清泉和羅黨論[18]研究發現,56%的獨立董事認為,投入時間對其作用的發揮有非常大的影響。本文關心的問題是,財會與法律背景獨立董事的工作地點一致性是否會影響其對企業違規行為的正向作用?或者說,那些工作地點一致的財會與法律背景獨立董事是否由于地理位置的便利性,更容易成為高管的“朋友”而更加積極地參與企業違規行為呢?由前文實證結果表明,財會與法律背景獨立董事主要對程度較弱的企業違規行為產生影響,因而本文隨后主要在違規行為概率、違規行為頻率兩個測量中考察獨立董事工作地點一致性的調節效應。獨立董事工作地點一致性變量(Place)的數據來自國泰安數據庫,在具體測量時,如果企業獨立董事工作地點與上市公司地點一致,則該變量取值為1,否則為0。回歸結果說明,財會與法律背景獨立董事與工作地點一致性的乘積項(Indirect×Place)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說明相對于工作地點不一致的財會與法律背景獨立董事而言,工作地點一致的財會與法律背景獨立董事對企業違規行為的促進作用更強。這可能是由于,當獨立董事與上市公司工作地點一致時,獨立董事與高管的接觸更多,更容易成為朋友,從而更便于其參與企業違規行為。回歸結果如表5模型中(4)和模型(5)所示。

表5董事會股權激勵和獨立董事工作地點一致性與企業違規行為的調節效應檢驗結果
六、結論與啟示
董事會在公司治理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特別是那些具有專業知識背景的董事,對企業決策具有重要影響。我國企業的違規行為近年來呈現不斷增加的趨勢,由于這些違規行為主要違反了財務、會計相關的法律規定,因而本文檢驗財會與法律背景董事對企業違規行為的影響。本文實證研究發現:首先,財會與法律背景董事(包括執行董事和獨立董事)對企業違規行為有顯著促進作用。其原因有二:一方面,我國獨立董事制度仍有待完善,獨立董事仍然存在獲取信息困難以及獨立性不高等問題,有時甚至成為高管或大股東的“朋友”,導致財會與法律背景獨立董事更容易與高管或大股東合謀,參與企業違規行為。而執行董事更容易受到高管壓力而參與企業違規行為。另一方面,我國法律對違規企業或個人的處罰較輕,造成財會與法律背景董事參與企業違規行為的違規行為成本較低。其次,財會與法律背景獨立董事和財務與法律背景執行董事對企業違規行為類型的影響不同:財會與法律背景獨立董事只對程度較弱的企業違規行為具有促進作用,而財會與法律背景執行董事對程度較弱或嚴重的違規都具有顯著促進作用。這可能是因為,相對于獨立董事而言,執行董事在企業內任職,本身更容易受到高管的壓力影響。最后,本文進一步實證研究發現:董事會股權激勵不能降低財會與法律背景執行董事對企業違規行為的促進作用,這可能是由于我國上市公司給予董事會的股權激勵比例較低,導致董事會的股權激勵作用沒有得到發揮所致。獨立董事工作地點與上市公司地址一致時,財會與法律背景獨立董事對企業違規行為的促進作用會更強。這可能是因為,當獨立董事工作地點與上市公司地址一致時,獨立董事與企業高管或大股東更容易成為“朋友”,導致其更可能積極參與企業違規行為。
以上研究結果表明,當前我國董事會的監督作用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一方面,需要加強法律法規對違規企業和違規董事的懲罰力度,提高他們的違規成本,從而降低他們參與企業違規行為的意愿。另一方面,完善獨立董事的產生機制,也是提升獨立董事獨立性的重要方式。那些由大股東或高管提名任命的獨立董事,可能由于是他們的朋友而難以發揮監督作用,完善獨立董事的產生機制,可以弱化獨立董事與大股東或高管的“朋友”關系,進而提升獨立董事的監督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