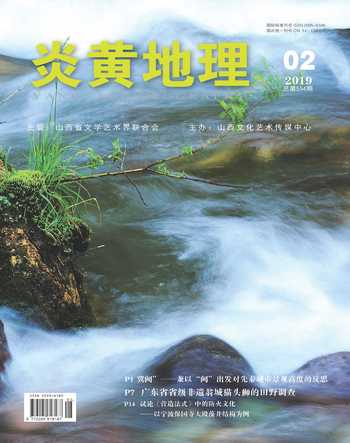桑志華的中國科考活動
金同桐
提起桑志華這個名字,可能很多人會感到陌生,但是說起天津自然博物館,那么相信很多人就熟悉了。天津自然博物館正是在桑志華這個法國人于1922年所創北疆博物館的基礎上建立的,里面的化石遺跡也大多繼承了當年所采集的原貌。
桑志華(Emile Licent,1876-1952)1,法國人,法國著名地質學家、古生物學家、考古學家。他之所以聞名考古學界,大部分由于他38歲那年來中國之后的科考活動,是中國這片土地成就了桑志華,而他本人也把人生的26年時光留到了中國,為中國的考古博物界做出了巨大貢獻。
桑志華從小就對身邊的動植物感興趣,正是由于這種興趣,使他從讀大學期間一直圍繞著動植物方面展開學習,以至于后來取得了生物地質學博士2。對于20世紀初的法國民眾來講,中國這片古老的東方土地還充滿了神秘與未知。1912年桑志華在與一位曾經到達過中國的天主教教士交流時3,偶然得知中國有大片未被探索開發過的地區,并且由于自然環境的差異,使中國產生了很多不同于法國的獨特物種,而這些對于一個渴望獲得成就與探索自然的他來說是充滿吸引力的。
1914年,在冰雪消融萬物復蘇的春天,桑志華帶著理想迎著春風,獨自一人乘從歐洲經西伯利亞來華的火車,不遠萬里來到這個尋夢的地方。3月21日桑志華到達滿洲里,3月25日順利抵達天津,由此正式展開了他早已醞釀兩年的探索之旅。來華后,桑志華便尋找落腳點,在得知了桑志華此行的目的后,天津獻縣教區的天主教耶穌會會長金道宣給予他很大幫助,不僅安排食宿,還幫助他申請考察活動的經費。在籌得獻縣教區、法國尚柏涅教省及法國外交部提供的經費后4,桑志華的科考活動開始順利展開。
科學探索的路是艱難而漫長的,起初桑志華本人也沒有料想到會在中國呆這么久,實際到達后卻欣喜發現原來這個地方值得探索的地方竟然這么多。在最初的幾個月,桑志華先是對獻縣周邊進行了小規模初步探索,熟悉中國的氣候環境和風土人情,這是起點也是重要的一步,因為抵達一個陌生環境,首先是要對當地的有一個初步的認識,才能在未來的道路中循序漸進越走越寬。而正是由于這最初的探索,使得他在腦海中形成了一個科考活動的最初方案,即“較為系統地考察所有注入渤海灣的水系如黃河、白河、灤河、遼河等及其流域地區,收集地質學、巖礦學、史前學、古生物學、植物學、動物學、人文學、經濟學等方面的資料與標本。”有了方向的正確指引,剩下的就需要花時間去做了。
1914年——1917年,是桑志華科考的探索摸索階段,這一時期他主要是在北京天津河北山西等地進行考察,采集的動植物以及魚類標本是小規模和不成體系的,并且這個時候采集的標本多是現生的生物,并且大多數是中國自然環境下特有的。而正是這種初步的往返探索為他后來的中國腹地考察奠定了基礎。采集到的動植物及魚類標本,這個時候放置在天津教區的財務管理處,即法租界圣路易斯路的崇德堂(今營口道天津市總工會大樓)。
1918年6月3日,以抵達寧夏北部鹽池為標志,桑志華開始了對中國北方腹地的探索,采集和發掘到的標本化石開始豐富起來。也正是這個時候,桑志華第一次在甘肅發掘到了上新世化石,這個發現使得他驚喜,也進一步堅定了要在中國繼續考察去的決心。1920年10月6日——11月20日,桑志華在山西永寧至太原一帶發掘,由于所收獲標本很多,于是通過沙漠商隊將其運回天津,有資料顯示“裝載這批標本就用了83頭駱駝”,可見標本數量的可觀。也正是在1920年,在甘肅慶陽幸家溝發掘出土的一件石核,是當時中國境內首次出土的舊石器時代打制石器。舊石器的出現,打破了自1882年以來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提出的中國北方不可能有舊石器的論斷,將我國的文明史上推了幾十萬年,也由此揭開了中國古人類的研究序幕。
1922年,由于標本的巨量增加,使得崇德堂房間不夠用,桑志華決定建立新館舍,而這個想法也得到了教會的肯定與支持。于此同時,恰逢法國天主教直隸耶穌會準備在天津籌建一所工商大學1(即河北大學前身,現舊址在天津師范大學內),經過討論,教會一直決定將桑志華的博物館與工商大學同時興建,博物館就建在工商學院旁邊,此后又經過1925年和1929年的兩次擴建2,北疆博物館形成了現在所保存的樣子。由于其采集發掘以及號召興建博物館的突出貢獻,桑志華于1927年4月獲得由法國政府頒發的“鐵十字騎士榮譽勛章”,而北疆博物院也被當時譽為世界上“第一流的博物院”3。
1923年,由巴黎博物館與北疆博物館聯合組成“桑志華——德日進法國古生物考察團”8在中國河北山西內蒙甘肅寧夏等地區進行了為期兩年的科學考察,期間最主要的發現是在寧夏水洞溝人牙(即后來聞名世界的河套人牙)與在河北宣化泥河灣發現的三趾馬動物群化石。泥河灣是中國考古界的一處寶庫,一直到1929年,桑志華曾7次到訪采集標本,里面包括三趾馬、板齒犀、劍齒虎和原始鬣狗等一系列富有重大考古價值的化石。1935年,桑志華在山西的榆社盆地采集到豐富的上新世哺乳動物化石,“以質量、數量論,都超過了他采集過的任何一個地點的化石”4,這也是桑志華在中國26年的科考活動中的最后一次重要發現。
1938年,歐洲和中國皆陷入戰火,桑志華此時也不得不停止已進行多年的考古活動,迫于形勢,他于1939年做出一個艱難的決定,離開已生活了26年的中國,重返法國,此時對于時年63歲的桑志華來說,心情一定是復雜的。
風雨26年,從今天看來,桑志華留給我們的,不僅是一座博物館與為數眾多的化石標本,還有他對科學探索的精神,用南開大學邱占祥教授在《桑志華與中國的古哺乳動物學》一文中的話來說:“中國今天還有如此豐富的可提供對比和進一步研究的新生代晚期的哺乳動物化石,這主要歸功于桑志華。”4這也許是對于桑志華在中國26年成果的最好注解。
參考文獻
[1]沈士駿.參觀北疆博物院以后、人生與藝術.[J],1928
[2]劉東生,盧演儔.德日進對中西科學交流的貢獻[A].見:王鴻禎.中外地質科學交流史[M].石油工業出版社,1992
[3]河北大學史[M].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
[4]房建昌.天津北疆博物院考實[J].中國科技史料,2003(01):10-19.
[5]王嘉川,王珊.天津北疆博物院補考[J].中國科技史料,2004(01):40-51.
[6]邱占祥.桑志華和他的哺乳動物化石藏品—試談桑志華藏品中哺乳動物化石的歷史及現實意義[A].孫景云主編.天津自然博物館建館90(1914-2004)周年文集[C].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2004.6-10.
[7]王平.天津自然博物館5次改擴建歷史紀實[J].安徽農業科學,2015,43(08):188-190.
注釋:
[1]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譯室編.近代來華外國人名錄[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2]王嘉川,王珊.天津北疆博物院補考[J].中國科技史料,2004(01):40-51.
[3]房建昌.天津北疆博物院考實[J].中國科技史料,2003(01):10-19.
[4]王嘉川,王珊.天津北疆博物院補考[J].中國科技史料,2004(01):40-51.
[5]河北大學史[M].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
[6]王平.天津自然博物館5次改擴建歷史紀實[J].安徽農業科學,2015,43(08):188-190.
[7]房建昌.天津北疆博物院考實[J].中國科技史料,2003(01):10-19.
[8]劉東生,盧演儔.德日進對中西科學交流的貢獻[A].見:王鴻禎.中外地質科學交流史[M].石油工業出版社,1992
[9]沈士駿.參觀北疆博物院以后、人生與藝術.[J],1928
[10]邱占祥.桑志華和他的哺乳動物化石藏品—試談桑志華藏品中哺乳動物化石的歷史及現實意義[A].孫景云主編.天津自然博物館建館90 (1914-2004)周年文集[C].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2004.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