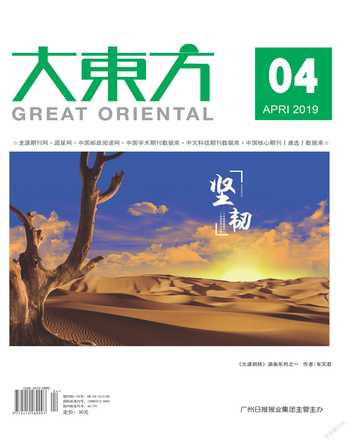人格物精神損害賠償探析
姜淑明 歐陽凱玲
摘 要:人格物是物質屬性與人格利益屬性有機融合的典型形態。因人格物遭受損害一般采取精神損害賠償予以救濟。在責任認定上既要符合侵權責任的一般構成,同時還須符合權利人遭受精神損害且其精神損害由人格物受損牽連而引發的特別構成條件。
關鍵詞:人格物;人格利益;精神損害
一、人格物精神損害賠償之理論紛爭
人與物作為民事法律關系主體與客體的典型形態,本是各自獨立而對應存在的。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法律制度的完善,人與物在民法中的二元劃分變得不再那么涇渭分明,具體表現為人格的物化與物的人格化。其中,物的人格化如特定人的婚戒、遺物、畢業證書等,相對于這類物品本身的經濟價值,權利人往往更重視它們所蘊含的紀念性、情感價值等人格利益。有學者以獨特視角將這類財產定義為人格物,具體而言是指與人格利益緊密相連,體現人的深厚情感與意志,其毀損、滅失造成的痛苦無法通過其他替代物得到補救的特定物。1
我國學者對于人格物精神損害賠償一直存在分歧,其焦點在于人格物受侵害時是否具備精神損害賠償的法理基礎。大致有如下三種主張。
肯定說。持肯定觀點的學者認為,作為人格利益延伸載體的人格物應當被列入精神損害賠償制度保護范圍,當侵權行為同時導致人格物及其物上人格利益的損害,加害人就負有賠償受害人全部損失的責任。隨著社會的發展,公民權益保護范圍勢必不斷擴大,當富有人格利益的物遭受侵害,不僅首先要在民法基礎上認定特定物本身的物質價值,同樣也要正確認識主體正當的人格利益,肯定人們精神利益的價值追求與傳承意義。人格物是經過特定化并由權利人寄予深厚感情的特定意義物,一旦造成永久性毀損或滅失,權利人所受精神打擊及損害無法單純通過物之毀損賠償予以彌補。
否定說。持否定觀點的學者認為,在民事權利體系中,只有不涉及財產利益因素的人身權益才能因民事侵權之發生適用精神損害賠償,以物質屬性為基礎的人格物當然不能拉入精神損害賠償的范圍。2但是現實生活中的大量實例表明,人格物因維系了權利人的特定人格利益,當它受到侵害時,權利人往往產生心理上的痛苦,使情感處于極不安寧的狀態,而且從內在性質和外在表現形態上看,這種情況下產生的精神損害與由于一般人身權益受損害而引發的精神損害并無不同。因此,從當代人文主義基本價值和對自然人權利完整保護的角度出發,其同樣應該得到合理法律救濟,而不應該在精神利益保護程度逐漸上升的今天,不加考察地對人格物精神損害賠償予以全盤否定。
嚴格限制說。嚴格限制說是我國人格物精神損害賠償理論研究中的主流學說。該觀點認為在人格物侵權糾紛中不應完全排斥精神損害賠償,承認人格物受侵害時權利人可以適當要求精神損害賠償有利于我國精神損害賠償理論與制度的發展。還有學者具體指出,民法應當在物的損害與精神損害賠償之間建立關聯,但應限于所有權的客體,并為之確定范圍或標準,把這種引發精神損害賠償的財產范圍限制在“人格象征功能的物”和“具有情感寄托功能的物”3,亦即本文所論述的人格物。本文反對否定說的過度保守,也不贊成毫無限制地全面放開人格物侵權精神損害賠償,現階段我國應當結合社會實踐需要與學理發展,肯定人格物精神損害賠償的理論意義,在一定條件下對人格物給予合理適當的保護。
二、人格物精神損害賠償之構成條件
人格物的核心價值是人格利益,但其表現形式首先是物,這就決定了人格物精神損害賠償之認定首先要參照一般物的侵權責任認定標準。但鑒于人格物的特殊法律屬性,其精神損害賠償之認定還需滿足其他特別構成要素。
(一)一般責任構成
1、侵權行為以人格物為對象。人格物精神損害賠償成立的重點在于侵權行為侵害的對象是否為人格物。在以物為客體的侵權糾紛中,往往只限于一般物的財產利益,沒有涉及民事主體的人格利益因素,所以不存在精神損害賠償的適用問題。人格物由于承載了權利人特別的情感和精神寄托而與一般物有別,其成為了對權利人獨具意義且不可替代的特定存在,使權利主體的人格利益與物相互交融、渾然一體。在這類侵權責任認定中,物上人格利益屬于人格物侵權的標尺,只有在侵權行為以這類具有人格利益的特定物作為客體時,才會發生從一般物的民事侵權到人格物侵權的轉化,人格物精神損害賠償的認定才具有現實理論基礎。當然在司法實踐中,若權利人提起侵權之訴主張人格物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應該率先由原告一方當事人舉證證明被告當事人侵權行為所指向的對象屬于人格物,明確案件爭議標的物所具有的特殊法律屬性,否則只能按照一般物的侵權規則進行處理。如楊潤昌等訴宣威羊場煤礦遺失骨灰盒一案4,原告方在宣讀起訴狀時提出的首要觀點就指出了案件爭議標的骨灰屬于人格物而不是一般物,應該在此基礎上適用人格物的侵權責任構成理論和人格物特別保護機制。最終其得到法院支持,獲得了相應精神損害賠償。
2、存在人格物遭受永久性損害的特定事實。永久性毀損或滅失是物受侵害的兩種外在表現形式,是物在物理形態上所發生的不可逆的毀損或滅失。運用到人格物中,也就是指當人格物作為客觀事物的狀態有了質變,權利人就該物享有的特定利益將發生缺失或不復存在,人格物作為人格利益的特定載體,其寄托的情感價值意義也會隨之變得殘缺或消失。嚴格來說,目前我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維護自然人因具體人格權、一般人格權以及身份權受侵害導致的精神利益損害,常以精神損害賠償金的形式,由侵權行為人對受害人所受精神痛苦做出特定物質補償。那么,在人格物精神損害賠償責任的認定中,還應嚴格考察爭議標的人格物的客觀損害程度。當侵權損害后果僅限于人格物的細微破損,而物上人格利益仍然存續時,一般認為該人格物破損之事實不足以造成權利人精神利益的嚴重損害,那么基于當前社會基礎和人格物的適度保護理念,就不宜再認定成立人格物的精神損害賠償,以免本末倒置,因過分保護物格而輕視了人格的社會主體能動地位。因此,只有存在人格物因侵權行為遭受永久性毀損或滅失時,其物之人格意義隨之消失或減損,侵權行為人的人格物精神損害賠償救濟才具有事實基礎,權利人才可以主張物質、精神的雙重救濟。
3、因果關系的認定。因果關系最初是一哲學概念,是指事物與現象廣泛聯系、相互作用的關系,但侵權法中的因果關系,通常指的是侵權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所存在引起和被引起的客觀聯系。它不僅是侵權責任得以確立的重要依據,使行為人客觀上因為其侵權行為致使權利人承受不利后果而被歸責,同時還擁有排除行為人錯誤承擔非本人責任的法理功能,保障了侵權責任承擔的正當性與嚴謹性。因為權利人具有特定意義的人格物是否受侵害是認定侵權責任成立的關鍵,同時也是確認精神損害賠償的根本前提,那么侵權行為和損害事實的因果關系就順理成章的成為法院案件審理的重點內容。要求行為人進行精神損害賠償,就必須證明其侵權行為確實造成了人格物的相應毀損或滅失,并從行為本身導致人格物嚴重損害的理論可能性和事實因果關系等方面展開雙重驗證,否則行為人可以以不具有因果關系為由進行抗辯,拒不承擔相關責任。這樣既有利于維護受害人的合法權益,還有利于防止行為人背負不當責任,對人格物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發展有積極意義。
4、行為人主觀過錯的認定。人格物精神損害賠償要求行為人存在主觀過錯。不宜采無過錯責任原則,一方面,僅根據行為人對人格物造成損害即可直接追究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而不考慮行為人的主觀態度,未免會使人格物保護范圍失去邊界和限制,陷入權利濫用的危機;另一方面,無過錯責任原則的適用應當經由法律明文規定,然而我國侵權責任法律體系并沒有對人格物侵權設置相應條款。因此應根據《侵權責任法》第六條適用過錯責任原則。此外,過錯在具體形態上還可分為故意與過失兩種類型,這在人格物侵權糾紛中均有存在。故意是行為人明知行為后果,并且希望或放任后果發生的心理狀態,行為人這種故意而為之的心態主觀惡性大,對損害事實的發生持追求態度,在案件審理中往往容易確定。過失則表現為行為人對注意義務的疏忽與懈怠,主觀惡性相對較小,而實踐中因過失導致人格物損害發生的案件比例更大,實際情況認定更為復雜。因此,在行為人過失狀態的認定上,還可以細化到違反普通人注意義務的重大過失、違反自己事務上應盡注意義務的具體過失和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的抽象過失等方面,以此綜合評判行為人的主觀過錯類型。
(二)特別構成要件
在認定人格物精神損害賠償時,其標準不僅應當滿足普通民事侵權成立所需的一般責任構成要件,還要按照人格物侵權的特點,對人格物的精神損害賠償認定給予更嚴格的限制,要求同時具備如下特別構成要件。
1、權利人遭受精神損害
在我國民事法律體系中,并不是所有損害類型都能得到公力救濟,只有依法律規定受保護的權利或利益遭他人侵害并達到法律救濟啟動條件時,受害人才得主張由侵權人就損害后果承擔法律責任。細化到人格物問題,該侵權責任關系發生的依據首先是人格物損害事實的客觀存在,而權利人所受精神損害與打擊則是人格物精神損害賠償責任的前提與基礎,所以在司法實踐中還要著重考察精神損害的事實。一般而言,精神損害主要是指自然人精神活動受到侵害而導致的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的減損,它給權利人帶來的傷害往往會超越生活中的物質財產損失,而救濟民事主體精神利益的損害也是法律制度進步的體現,彰顯了人類主體地位的社會文明理念。具體如父母的遺照、夫妻間保存多年的定情信物、個人獨具紀念意義的學歷證書等,這些人格物永久性毀損或滅失造成的損害事實同時包括財產損害和精神損害,不過對比之下,物質層面的財產損害已不值一提,因為就算進行實物鑒定也難以為其估值定價,而人格物權利人遭受的悲傷、痛苦等精神損害顯然具有更大沖擊力,應當作為人格物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認定中最為核心的事實依據。
人格物首先是一般物,其物質屬性與一般物并無差異,只是經由權利人獨特精神利益和人格價值的寄托而被賦予人格利益因素。因其成為權利人深厚情感利益之載體而被賦予了不可替代的屬性,不可與其他僅用于物理功能的物品等量齊觀。故而在案件涉及具備人格利益因素的特定物受他人侵害的情況下,人格物作為權利人享有特定人格利益的唯一載體,只有當它發生永久性毀損、滅失,其物上精神利益嚴重貶損甚至不可再現,并造成權利人情感缺失和巨大精神痛苦時,才能認定人格物精神損害賠償責任的成立,進一步啟動相關法律保護機制。
2、精神損害由人格物受損牽連引發
人格物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初衷,是順應民法理論與社會發展的迫切需要,明確人格物侵權損害的救濟渠道以加強對物上人格權益的法律保障。但人格物保護不是沒有限制的,要真正確立侵權人的人格物精神損害賠償責任,還要在滿足以上必備要素的基礎上,對構成要件之間的整體因果關系進行驗證,證明加害行為與受害人最終的精神損害后果有因果關聯。
在侵權人以人格物為直接指向對象的基本提前下,侵權行為和被侵權人精神損害后果之間應以人格物本體的毀損滅失為橋梁,由此架構人格物侵權案件中的整體邏輯因果關系。人格物因加害行為而受損,在物形成永久性毀損并不可修復,甚至發生人格物滅失等嚴重損害后果時,人格物的不可替代性特點就決定了權利人物上人格利益缺損的同步發生。就像在一般人看來,有些物品可能極為普通且毫不起眼,寄托的豐富感情與紀念意義并不為人所知曉,但對權利人來說,一旦這些作為權利人特定情感載體的人格物發生毀損、滅失,勢必會使權利人遭受嚴重精神損害。那么此時人格物侵權行為已然經由人格物受損這一基礎事實,牽連引發了自然人主體人格利益的損害,進而使權利人由于人格物侵權所造成的負面后果承受精神痛苦,形成了侵權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要求的實際邏輯關聯,可以最終認定成立人格物精神損害賠償責任。
參考文獻
[1]冷傳莉.論民法中的人格物[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 60.
[2]曾世雄.損害賠償法原理[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1.369.
[3]常鵬翱.論物的損壞與精神損害賠償的關聯--一種功能主義的詮釋[J].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學院學報, 2005, 23(1):22-27.
[4]中國審判案例要覽·2006年民事審判案例卷[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465-470.
[5]湯瀟瀟.侵權法因果關系芻議[J]. 理論界, 2010(3):61-63.
[6]袁麗紅.論精神損害賠償——兼評《侵權責任法》第22條[J]. 新余學院學報, 2011, 16(4):24-26.
作者簡介:
姜淑明(1963—),女,湖南師范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歐陽凱玲(1993—),女,湖南省桂陽縣人民檢察院。
(作者單位:1.湖南師范大學法學院;2.湖南省桂陽縣人民檢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