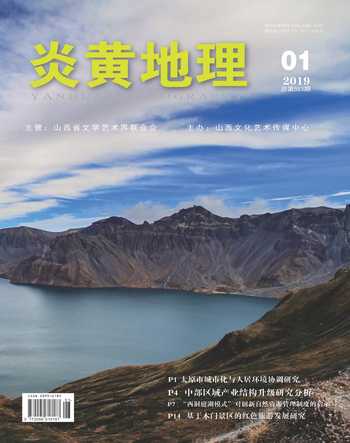黃土中探尋“古洪水”
樊雙虎 楊懷鵬 張天宇
摘 要:全新世以來,我國乃至全球發生過多期古洪水事件,古洪水作為一種環境驅動力對古文化的興衰演變具有重要的影響。即使在科學技術如此發達的今天,洪水依然會給我們的生命和財產造成重大威脅。遠超歷史調查洪水重現期的萬年尺度的古洪水研究對于生態環境以及全球氣候變化的認識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本文從認識古洪水入手,通過介紹古洪水的年代和水文學研究方法,認識萬年尺度古洪水的危害,以期能讓大眾了解洪水,認識自然,增強大家對生態環境的認識,提高災害防控意識。
關鍵詞:黃土;古洪水;古文化;生態文明
Since the Holocene,there have been many palaeoflood events in China and the world.As an environmental driving force,palaeoflood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rise and fall of ancient culture.Even today,wh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so developed,deluge still pose a major threat to our lives and property.The palaeoflood study on the scale of ten-thousand year far beyond the flood return period in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global climate change.Therefore,this article begins with an understanding of palaeoflood,introduces the age of palaeoflood and hydrological research methods,and recommends the dangers of palaeoflood on the millennial scale,in order to let the public recognize the flood and nature,enhance everyones understanding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and improve poeples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wareness.
Keywords:loess,palaeoflood,ancient culture,ecological civilization
“黃天厚土大河長,溝壑縱橫風雨狂”,這是詩人眼中的黃土高原,展現的是一片荒涼而又充滿著堅持的景象。正是這片遍及長城以南,秦嶺以北,烏鞘嶺、日月山以東,太行山東麓以西面積約44萬km2的黃土高原孕育了古老的生命與記憶,書寫了中華民族的歷史長卷,銘刻著華夏文明的長度與厚度。從六千年以前的半坡遺址文化,到其后的仰韶文化,馬家窯文化,大汶口文化及龍山文化等,厚達50~500 m的第四紀黃土地層就猶如一部天然史書,記錄了中華民族的文化演變和歷史變遷。而“古洪水”作為一地質災害,一種環境驅動力,在中華文明的興衰演變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今天我們就以“古洪水”為主旨,講講如何在地質歷史記錄中探尋它的蹤跡,講講如何去了解它發生的時間和規模,講講它在人類文明歷史進程中的“功”與“過”,以期今天與明天,我們人類能與自然和諧相處,構建和諧人地關系,共筑生態文明社會。
1、古洪水的蹤跡
古洪水是指第四紀全新世以來(1.17萬年)至可考證的歷史洪水期以前的這一時期內發生的大洪水,也可以理解為史前發生的,缺乏文字記載,只能依賴地質沉積記錄探究的洪水[1-2]。關于古洪水,人類的史書上有著不少的記載,世界上的古老文明初期都流傳著洪水肆虐的故事與傳說[3],在我國最著名的莫過于“大禹治水”的傳說,《山海經·海內經》記載:“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鯀復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島。”《莊子·天下》也提到“昔者禹之煙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雖然今天流傳著許多幾千年前古洪水的傳說,也保存著大量文字記載,但僅依據這些傳說和記載,我們無法確定其真實性,更不能恢復古洪水發生的確切時間與流量。要科學的探究古洪水,首先,我們要找到古洪水的蹤跡—古洪水沉積物。說到這里,我們不得不再次提起黃土地層,作為一種典型的風成沉積物,黃土主要是由石英質的粉塵顆粒組成,粒徑只有0.005~0.050 mm大小,有色淡灰黃、疏松、均質及無層理等典型特點[4]。與其截然不同的古洪水沉積物往往由于其形成的水動力強、沉積時間短、沉積物成分復雜等成因特征形成以砂粒、淤積粘土為主的顏色、結構和粒徑具有明顯垂直變化的沉積組合,古洪水沉積物中往往可能存在瓦片、動物骨骼等人類文化遺物,在山坡等位置往往會有大的礫石等坡積物[5-8](圖1)。找到這些古洪水的記錄,我們就可以研究其形成的時間,估算古洪水的流量,探討古洪水與古人類生活的關系等等。當然,我們還可以進行更細致的研究來揭開這些古洪水沉積物的神秘面紗。比如,我們可以進行粒度分析,看一下某次洪水到底攜帶了多大的砂粒[9];我們還可以給這些小小的砂粒做個電鏡掃描,認識下這些在洪水相互撞擊的小沙粒獨特的形態[3];我們還可以研究它們夾雜的植物孢粉(孢子和花粉)[10],了解洪水發生時的氣候濕熱特征等等。
2、古洪水的年代和規模
當我們確定了古洪水沉積以后,怎么才能研究它的時間,怎么才能知道洪水規模多大呢?我們的地質學家、地理學家等早已經研究出了多種科學的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現在我們就來看看到底有哪些可以穿越時空的“高、大、上”的科學測年方法吧。
2.1 古洪水研究的地質年代學方法
古洪水研究的年代學方法有很多種,我們主要講一下常用的絕對年代方法。絕對年代學方法主要是利用同位素進行分析測試的,其中碳同位素測年為首選[11-13]。大氣層中天然存在的14C通過動植物的呼吸作用,會留存在生物體中,由于新陳代謝作用使活著有機體內14C濃度與大氣中的濃度保持大致平衡,動物或植物死亡后,停止與外界交換,生物體中14C處于封閉狀態,原始14C濃度隨著時間的推移按一定規律減少,這樣根據樣品現存的14C含量,可以反推生物死亡年齡,當然具體的測試過程還涉及到很多的科學方法。目前,利用加速質譜儀(圖2)可以實現快速、高效的測定,精度可達2%或更好,而樣品需求量甚至可以少于1mg(西安加速器質譜中心:http://xaams.ieexa.cas.cn/)。這樣我們就可以利用洪水沖積埋藏的植物果實、種子、木頭、骨頭、貝殼等物質進行準確的測年,甚至地下水、海水和空氣含有的14C也可以來進行測試,從而在地球科學、宇宙化學、環境科學、考古學、海洋科學、生命科學等領域發揮重大的作用。
那如果洪水沉積物就像我們在河邊常見到的沙子一樣干干凈凈缺乏含碳物質的沉積該怎么辦呢?光釋光(optically stimulated luminescence,OSL)測年技術就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另外一種常用測年方法[14-16]。沉積物中的礦物顆粒(對OSL測年有意義的主要是石英或長石)被掩埋之后不再見光,同時不斷接受來自周圍環境中的U、Th、K等放射性物質的衰變所產生的α、β、γ宇宙射線等的輻射,導致晶體的電子發生電離而脫離晶體形成自由電子,之后被晶格中參雜的雜質原子或者其他因素所導致的晶格缺陷所形成的“電子”陷阱所俘,變成“俘獲電子”而儲存,長期的埋藏輻射過程使得礦物晶格中的“俘獲電子”越來越多,即礦物顆粒隨時間的增長不斷累積輻射能。這些礦物顆粒在天然環境受熱或者光照及實驗室用加熱或光束照射時,可以使累積的輻射能以光的形式激發出來,即釋光信號。通過加熱而激發出的釋光信號叫熱釋光(thermolumi-nescence,TL),通過光束激發的釋光信號叫光釋光(OSL)。天然環境中的曝光、熱事件等使積累輻射能的礦物顆粒的釋光信號被清空或降低到可忽略的水平,釋光信號歸零(釋光“時鐘”歸零),之后在埋藏過程中不斷積累釋光信號。這些釋光信號的強度與樣品所吸收到的輻射劑量成函數關系,可以用于檢驗樣品所接收的輻射劑量,此時所測的釋光信號為樣品最后一次曝光后至今所累積的。
除了這些以外,我們還有宇宙成因核素法[17]、氨基酸外消旋法(AAR)[18]、古地磁及樹木年輪法等多種測年技術[19],這些方法不僅有“高、大、上”的名字,而且也確確實實在我們的科學研究中發揮著重大的作用。比如: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年代研究中宇宙成因核素法的應用[17],元謀人年代研究中古地磁方法的應用等[19]。
2.2 古洪水的水文學重建
我們在知道了古洪水發生的時間之后,不僅要問,洪水的流量有多少呢?當我們明確了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會對某次古洪水事件有個比較清晰的認識了。接下來,我們看看如何該回答這個問題呢。古洪水水文學重建是在古洪水發生時間、歷史斷面考證和洪水水位確定的基礎上恢復古洪水行洪時的洪峰流量等信息,是古洪水研究中最重要的環節之一[3]。常用的洪峰流量計算方法有比降法、控制斷面法、回水曲線法、水位流量關系法等,實際應用中,要根據不同河段的河流斷面形態、實測水文資料和歷史調查痕跡等具體信息,用恰當的水文學計算方法。當然具體的計算過程還要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科學手段。這些遠超歷史調查洪水重現期的河流萬年尺度洪水水文數據對于我們今天的防洪設計以及認識河流的發育史、古氣候、古地貌和古生態環境以及全球氣候變化都具有重要的意義。例如,科學家研究發現黃河中游晉陜峽谷龍門段在商代末期-西周初期(距今約2800—3000年),曾發生4次古洪水事件,洪峰流量介于46280~48800m3/S 之間,遠超該段龍門水文站自1934年建站以來實測最大洪峰流量21000m3/S[20];再如,位于青藏高原上具有“東方龐貝”之稱的喇家遺址,科學家認為是地震暴雨導致的堰塞湖潰決導致毀滅的,潰壩導致了洪峰流量近35000m3/S的異常洪水,這樣的洪峰相當于該河段萬年一遇洪水流量的3倍多[21](齊家文化網:http://www.qijiawenhua.cn/)。
3、古洪水在古文化演變中的“功”與“過”
說起洪水我們不禁想到山洪咆哮、傾盆大雨、毀壞房屋及侵吞農田等可怕的場景,真是談之色變,避之而不急啊。在科學技術如此發達的今天,洪水都會給我們的生產生活帶來毀滅性的打擊,可想而知,在遠古時期,沒有科學預報,沒有堅固房屋,沒有快速轉移交通工具的情況下,洪水帶來的是多么可怕的后果。科學研究發現,全新世以來(距今約1.2萬年)全球發生過多次全球性的氣候突變,并且影響了古文化的發展演變。其中最為明顯的就是4000年前左右的大洪水事件,也就是大禹治水時期。這次事件在中原地區二里頭、周家莊、西金城等遺址均發現古洪水記錄,并且對龍山文化向華夏文明的演變過渡具有重大的影響[22];在關中渭河流域的楊官寨遺址同樣也發現該遺址的毀滅與這個時期的古洪水關系緊密,在該流域的漆水河等地也有同樣的發現,這次古洪水可能導致隴山文化晚期的先民們由河谷階地遷向了黃土高原[9]。另外,山東龍山文化的衰落以及長江三角洲良渚等古文化的消亡均由大洪水造成[23-24].盡管不同的學者基于不同的領域對古文化興衰的認識不盡相同,但環境因素對無疑是古文化演變的重要驅動力,其在對古文化形成危害,導致古文化衰退的同時,另一個角度來說,也促進了古人類生產力的發展,促使古人類不同文化之間交叉融合,提高抵御自然侵害的能力,促使古人類向更高級的文化過渡。
4、人地和諧,共筑文明
洪水被認為是三大自然災害之一,其帶來的破壞作用不僅在其自身還在于其引發的滑坡、泥石流及堰塞湖潰壩等次生災害。在這樣的自然力和自然過程面前,我們人類太過渺小,無法與自然抗衡,更無法逆轉這些地質作用過程。而自人類出現以來,我們的生存和發展就要不對的與自然對抗,向自然索取,比如,毀林開荒、漫灘種地等,這些往往放大了洪水等災害的破壞性。面對洪水等災害,人們唯一能做的是尊重自然、重視自然、順應規律,改變我們自己的生產生活方式,盡可能的把洪水災害的危害降到最低。
在黃土高原地區,降雨多集中,地形溝多坡陡、起伏破碎(圖3),河流支流較多,河床較陡,匯水快速,極易形成洪水,形成的洪水含沙量高,而黃土高原地區以黃土為主要的組成物質,易于沖蝕,形成滑坡或泥石流導致大量次生災害,破壞性強。在我們的生產生活中,毀壞植被,陡坡耕種,過度放牧及工程建設中的不合理利用土地等導致和加劇了洪水災害。為了預防洪水災害,我們應盡可能做好洪水的防治工作,從長遠來說我們應該加強洪水預警教育;大力種草種樹,搞好水土保持;制定避災規劃;明確治理措施;落實防御方案;完善保障政策。
5、結語
洪水既是一種自然現象,又是人類社會發展對土地利用相互作用的結果,洪水將永遠伴隨著人類文明共生。我們只能積極有效地應對洪水,而無法消滅洪水。“給洪水以出路”,尊重、敬畏自然,力求人與自然間最大程度的和諧相處,努力建設生態文明。
*中國地質調查局基礎性公益性地質礦產項目“特殊地質地貌區填圖試點”子項目“陜西草碧鎮(I48E008021)等六幅黃土區填圖試點”。
參考文獻
[1]謝悅波,江洪濤.古洪水研究—挖掘河流大洪水的編年[J].南京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1,37(3):390-394.
[2]詹道江,謝悅波.古洪水研究[M].北京: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2001.
[3]楊凌,千河流域古洪水沉積與水文學特征研究[D].陜西師范大學,2012.
[4]孫建中,黃土學(上篇)[M].香港:香港考古學會,2005.
[5]BakerV R,Paleoflood hydrology and extreme flood events[J].Journal of Hydrology,1987,96:79-99.
[6]Yang Dayuan,Yu Ge,Xie Yuebo et al.Sedimentary records of the large Holocene floods from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J].China Geomorphology,2000,33(1-2):73-88.
[7]Diane Saint Laurent.Palaeoflood hydrology:an emerging science[J],Progress in Physical Geography,2004,4(28):531-543.
[8]謝悅波,楊達源.古洪水平流沉積基本特征[J].河海大學學報,1998,26(6):6-11.
[9]查小春,黃春長,龐獎勵.關中西部漆水河全新世特大洪水與環境演變[J].地理學報,2007,62(3):292-300.
[10]張玉蘭.從孢粉、藻類分析探究良渚文化消亡的原因[J].同濟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8,6(3):402-405.
[11]仇士華,蔡蓮珍.關于考古系列樣品碳十四測年方法的可靠性問題[J].考古,2001(11).
[12]仇士華.夏商周年表的制訂與14C測年[J].第四紀研究,2001,21(1),79-83.
[13]方燕明.河南龍山文化和二里頭文化碳十四測年的若干問題討論[J].中原文物,2005(2).
[14]黃春長,龐獎勵,查小春,周亞利.黃河流域關中盆地史前大洪水研究—以周原漆水河谷地為例[J].中國科學:地球科學,2011,41(11):1658-1669.
[15]王恒松,黃春長,周亞利,龐獎勵,査小春,顧洪亮,周亮.關中西部千河流域全新世古洪水事件光釋光測年研究[J].中國科學:地球科學,2012,42(3):390-401.
[16]張克旗,吳中海,呂同艷,等.光釋光測年法—綜述及進展[J].地質通報,2015,(01):183-203.
[17]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的年代綜述兼評該遺址的鋁鈹埋藏年齡[J].人類學學報,28:285–291.
[18]吳佩珠,錢方.用氨基酸測年法對“元謀人”年代的初步研究[J].人類學學報,1991,(03).
[19]李普,錢方,馬醒華,浦慶余,邢歷生,鞠石強.用古地磁方法對元謀人化石年代的初步研究[J].中國科學,1976(6),579-591.
[20]石彬楠,黃春長,龐獎勵,查小春,周亞利,張玉柱,劉雯瑾.黃河龍門段商周轉折時期的古洪水事件及氣候背景[J].湖泊科學2017,29(1):234-245.
[21]吳慶龍,張培震,張會平,葉茂林,張竹.黃河上游積石峽古地震堰塞潰決事件與喇家遺址異常古洪水災害[J].中國科學:地球科學,2009,39(8):1148-1159.
[22]張俊娜,夏正楷.中原地區4000年前后異常洪水事件的沉積證據[J].地理學報,2011,66(5)685-697.
[23]俞偉超.龍山文化與良渚文化衰變的奧秘[J].文物天地,1992,3,27-28.
[24]張明華.良渚文化消亡的原因是洪水泛濫[J].江漢考古,1998,66,62-65.
作者簡介
樊雙虎(1962-),男,副教授,陜西寶雞,研究方向為構造地質學、工程地質災害等。
通訊作者:楊懷鵬(1996-),男,碩士研究生,山東濟南,研究方向為新構造運動、第四紀環境演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