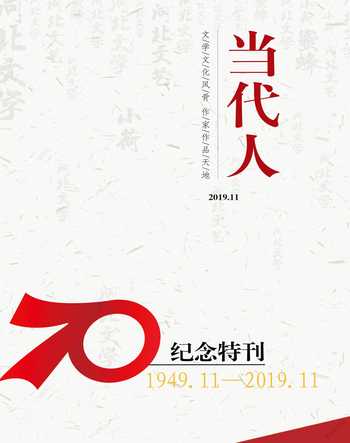任性聊文學的日子
1986年下半年,我從廊坊師專文學班畢業,來到向往已久的河北省文聯大樓。
那時的文聯大樓其實只有四層,但在我內心它卻是高大的,因為它是屬于文學的,還因為它集中了省內的作家、詩人、編輯、評論家等各路精英。當時,《河北文學》和《長城》編輯部都設在三樓,編輯室一間挨了一間,誰想找誰聊個話題,推門就進,進門就聊,且話題一定是文學的,所有的人都像是為文學而生的。
值得一提的是,那時復刊不久的雜志已更名《小荷》,而1987年的1月,也就是我到《小荷》半年不到,《小荷》又改回了《河北文學》。《河北文學》自然是更眾望所歸的名字,我覺得它也應是好的文學氛圍的產物。
當時《河北文學》的主編是王洪濤先生,他對辦刊有熱情,有主見,敢于聘用新人,編輯部除了他和一位女編輯是《河北文學》的老人外,其他全是樓外的新人。后來證明,新人確有新人的優勢,人際關系簡單、明朗,工作起來有熱情有干勁兒,更重要的是,都因了文學而來。對文學的熱愛成為這群人聚集的基礎,在今天看來,還真是十分難得。
那真是個文學的好時期,大家聚在樓里談的是文學,走出去約稿、開筆會談的仍是文學。一本口口相傳的好書,也不知從哪里開始的,漸漸地,幾乎人人都在看了。比如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當代美國短篇小說選》,比如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比如塞林格的《麥田里的守望者》,比如納博科夫的《洛麗塔》,比如博爾赫斯的《博爾赫斯短篇小說選》,比如馬爾克斯的《加西亞·馬爾克斯中短篇小說集》等等。不斷地有新書、好書的傳遞,說明了出版市場的日益開放,也更說明了中國作家學習、成長中的如饑似渴。在這期間,文學編輯和作家幾乎是同步成長的,作家們讀的書,編輯們也會千方百計地找來,因為文學編輯就是和作家們打交道的,跟不上作家學習、思考的節奏,編輯工作就難免被動。另一方面,初學寫作者也是很重要的部分,從大量來稿中一眼發現好作品,既是作者的幸運,也體現著編者的眼光。眼光從哪里來?正是從扎實又開放的讀書中來的,而當時的文學氛圍,對這種讀書實在是十分有益的。當然現在回想起來,也不是每本書都適合自己,但重要的是個氛圍,在這氛圍中會有更多的相通感,會更增強讀書的動力。
我自己,那時除了做編輯,也沒忘了寫作,1986年底發表在《長城》上的中篇《綠》被認可,心中可說也是一片綠色,生氣勃勃。《綠》的責任編輯是今已過世的王澤震老師,在她的指導下《綠》曾改過兩稿,她對稿子的專注、投入為我樹立了永久的榜樣。到《河北文學》當編輯后,幾乎每天都能見到她,常常地,就和她老人家站在樓道里聊起小說來,該下班了,該吃飯了,可她像是沒感覺,一切都沒有小說的話題重要似的。
由于編輯和寫作,我和許多作家也都有過交往,省內如徐光耀、鐵凝、賈大山、陳沖、張學夢等,省外如史鐵生、李敬澤、余華、池莉、周大新、馮秋子、韓石山等,從他們那里我自覺受益頗多,特別是省內作家,交談的機會就更多些。其中和徐光耀老師雖交談不多,但他曾做過兩件讓我終生難忘的事,一件是為我的《綠》寫評論,一件是在我轉為《河北文學》正式編輯時,為我寫了頗有說服力的專家鑒定。我想強調的,是這兩件事發生時,我和徐老師還不認識。可那時候就是這樣,老一輩作家和編輯對文學新人無條件地好,發現了新人好像比新人自個兒還高興。還有鐵凝,省內作家里與她的交談可說是較多了,我感覺她對文學有一份發自內心的虔敬,和她談小說和編她稿紙上的小說都能感覺到她的虔敬。我也編過不少賈大山的小說,他的字寫得一絲不茍,就像一幅鋼筆書法作品一樣,一筆一畫都似存了他的真情實感。陳沖的字,寫得雖說有些龍飛鳳舞,但清晰、帥氣,帶了他那一代人的漢字功夫,字和小說都如同他的人一樣,有較強的自得和自信。張學夢呢,是很棒的詩人,但時而也寫小說,小說稿涂改得很多,詩人的思維躍然紙上,但他的真純的哲理性思考一直教人欽敬不已。
說這些我是想說,做一個文學編輯雖說不易,卻也大有益處,只要努力,只要對文學真心熱愛,和作家、作者、編輯的一切交往都可能成為促進你成長的因素,成為促進刊物成長的因素。
到了上世紀90年代,由于種種原因,《河北文學》改成了綜合性刊物《當代人》,雖說遺憾,但它的底子到底是《河北文學》,改來改去終究沒離文學太遠。記得在我離開《當代人》的一些年里,我還應約為它寫過小說。令人欣慰的是,現在的《當代人》,又已是一派文學面目了,小說、散文、詩歌、評論等等,改回得很徹底,透了某種令人欣喜的堅決。作為《河北文學》曾經的編輯,也作為《河北文學》曾經的作者,在《當代人》創刊70周年之際,我由衷地祝愿她徹底下去,文學下去,成就更多的編輯和作家,聚集起更多的文學讀者。
(何玉茹,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曾任河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河北文學》小說編輯、《長城》副主編、河北省作協創作室主任。已出版和發表長篇小說《冬季與迷醉》《葵花》《前街后街》等7部,中篇小說40多部,短篇小說150多篇,多篇小說獲獎或被選載。)
編輯:劉亞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