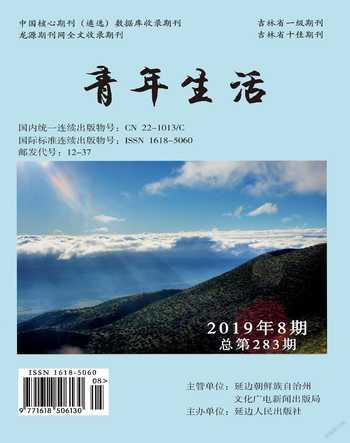論歷史認識的客觀性
高乾
摘要:敘述并說明人類過去發生的事情是歷史研究的基本目的之一。對于歷史學家而言,盡可能地保持客觀中立,真實地將歷史重新展現出來,是他們工作中最為重要原則。但我們會發現,對于相同的歷史事件,不同的人、以及身處不同的環境和時代往往會有不一樣的解讀。這就涉及歷史哲學中的一個基本問題——歷史認識的客觀性。本文嘗試對這一問題做出一些討論。
關鍵詞:歷史認識;客觀性;歷史學者;材料;解釋體系
一、歷史學者的主體性影響歷史認識的“客觀性”
歷史是人寫成的歷史。因為歷史都是人遺留下來的,史料與著作都是人撰寫的,獨立于人的意識之外的歷史是不存在的。因而歷史學者的內在經驗對于歷史認識的解讀有著重要的影響,就像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撰寫《歷史研究》這部書的時候,“他憑借親身的體驗第一次了解到修昔底德字里行間流露出的深意,這種深意是他以前很少乃至完全不能理解的。”[1]
對于歷史事實來說,也決非存在于人頭腦之外的原始事物或者事件。“歷史不是一連串的事實,歷史著述也不是對這些事實的敘述。歷史學家必須不斷地通過分類,判斷什么是真實的、有意義的。”[5]在英國歷史學家卡爾看來,“認為歷史事實是獨立于歷史學家的解釋之外的客觀存在的想法是十分荒謬的。”[2]湯因比則認為,“歷史學家都是他們所觀看的歷史這出戲的演員。歷史學家能擺脫這種自身相關聯的狀態是一種幻想。”[5]
因此,從歷史學者的主體性來看,歷史認識的客觀性是相對的。在歷史研究當中,若希望取得一樣的客觀條件,達成共同而一致的理論和認識,是件極為困難的事情。面對相同的史料與歷史事實,不同的歷史研究者秉持著自己的立場,可能會有不同的排列組合方式,最后也必然會得出不一樣的解釋和認識。
二、材料的局限性影響歷史認識的“客觀性”
歷史研究是基于事實的實證研究,其結論性的意見要立足于事實材料。如檔案作為一種再現歷史真實面貌的文獻載體,對于歷史研究就具有獨特的價值,因為檔案屬于第一手材料,沒有太多的篡改和修飾,更加具備客觀性。但是,檔案畢竟是“當時的人”所記錄的,不免帶有“當時的人”的觀點和傾向,真實性也只是相對的。因此,在研究中要盡量避免被檔案所迷惑和誤導,如訴訟案卷中對道德色彩的評價就一定要秉持謹慎的態度,“只有剝下文獻中的虛構成分,才能得到真正的事實。”[3]
從史料的完整度上來看,受制于所處的時代條件影響,研究者能夠獲取的史料往往只是部分材料,所以推論出的結論并不是完全正確的。“任何現象都有眾多側面,人類能夠把同一現象按照它所顯示的各個側面進行多種分類。因而,任何一種分類所把握的都只不過是它所拼湊的現象的一個片段。”[5]如美國歷史學家裴宜理的專著《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它的完成就“完全依賴于臺灣、日本和美國的圖書館和檔案館文獻”[4],因為當時(1978年)“對美國學者來說,要在中國大陸展開學術研究實為可望不可及的事情。”[4]裴氏由于客觀條件的限制,未能更多地開展實地調查,她對淮北共產主義革命的論述就不免給人留下了遺憾的感覺。
“歷史事實并不是像一塊磚頭或者一塊石頭那樣的可以撿起來撫摸的具體東西。”[5]換言之,歷史事實的重建不是一個固化的整體,而是通過人們篩選原始資料后才得以完成的。因此,從材料的層面上來看,歷史認識的客觀性是相對的。
三、時代與解釋體系影響歷史認識的“客觀性”
一切歷史都是人解釋的。價值觀、知識結構、人生閱歷等決定了研究者對歷史的解釋體系,它是一種主觀的判斷,這影響到了歷史認識的客觀性。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認識的客觀性還會受到時代影響。歷史作為一種多元性的存在,在認知中會不斷發生變化,因為不同時代的人對歷史的理解是不盡相同的。一個時代的人解釋的歷史都是那個時代的歷史,是那個時代下誕生的產物。
因此,歷史認識的客觀性不可能是事實的客觀性,而只能是一種關系的客觀性,即事實與解釋之間關系的客觀性。另外,時代的風尚、追求等也都對歷史認識有影響。從這個層面上看,歷史認識的客觀性也是相對的。
四、余論
由于主客觀條件的雙重影響,歷史認識的客觀性只能是一種相對的客觀性,試圖分毫不差地復原過去是不可能做到的。但需要厘清的是,不應該以自然科學的視角來審視歷史認識的客觀性。歷史研究要揭示的規律,并不等同于自然科學的“嚴格”客觀,它更多表現為一種概率性的趨勢,正所謂“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歷史研究學者的解釋也是由一套概念體系所組成的,這與他們的理論儲備和價值立場密切相關。“歷史研究是歷史學家和他所研究的歷史事實的互動。不管在什么時候、什么地方,對歷史的觀察都會伴隨歷史學家觀察的立足點的改變而改變。在這種意義上,相對性是所有關于人類事物的研究的一個局限,這是由人的思想活動的環境造成的。”[5]
既然相對性的局限無法克服,我們就抱著平常心去面對,不必對此抱有恐慌,認為全部的歷史認識都是主觀的,沒有任何客觀性或者真實性,那只會對歷史研究的工作產生阻礙。歷史研究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實證”之外,總歸要加上一些主觀的認知判斷與形而上的思維,虛實相生,共同證史。于我們而言,在具體的歷史研究工作的過程中,嚴格恪守學術規范,盡可能多地搜集資料作為依據,盡量克服自身的偏見或者偏好,充分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盡可能準確地“揭示歷史真相”也就可以了。
參考文獻
[1][英]阿諾德·湯因比著,郭小凌等譯:《歷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2][英]卡爾著,陳恒譯:《歷史是什么?》,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
[3][美]娜塔莉·澤蒙·戴維斯著,饒佳榮、陳瑤等譯:《檔案中的虛構:16世紀法國的赦罪故事及故事的講述者》,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4][美]裴宜理著,池子華、劉平譯:《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1845—1945》,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
[5]劉遠航:《湯因比歷史哲學》,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