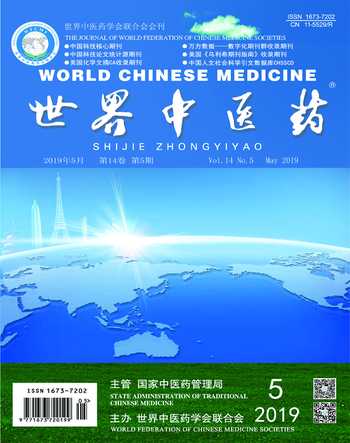永久性心房纖顫患者中醫體質類型與血漿D-二聚體相關性研究
謝冰昕 林謙 馬麗華
摘要 目的:探討永久性心房纖顫患者中醫體質類型與血漿D-二聚體之間的相關性。方法:選取2017年1月至2018年9月廣安門醫院和廣安門醫院南區收治的永久性心房纖顫患者150例作為研究對象,進行血漿D-二聚體水平檢測,填寫《中醫體質分類與判定表》,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結果:永久性心房顫動患者中醫體質涵蓋所有9種體質類型,其所占比例及血漿D-二聚體水平(%,ng/mL)分別為氣虛質(40.6%,292.48±334.58),痰濕質(18.0%,324.74±346.78),血瘀質(10.0%,643.3±1627.23),陽虛質(9.3%,396.64±404.01),陰虛質(8.6%,432.46±664.35),氣郁質(6.6%,133.7±79.37),濕熱質(3.3%,122.00±21.62),平和質(2.6%,252.00±263.03),特稟質(0.6%,13)。結論:永久性心房纖顫患者中氣虛質及痰濕質所占比例較大,血漿D-二聚體水平血瘀質>陰虛質>陽虛質>痰濕質>氣虛質>平和質>氣郁質>濕熱質>特稟質,男女患者血漿D-二聚體水平無明顯差別,患者血漿D-二聚體水平不受年齡的影響。
關鍵詞 永久性心房纖顫;中醫體質;D-二聚體;性別;年齡;血栓栓塞;風險評估;相關性分析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onstitution types of TCM and plasma D-dimer in patients with permanent atrial fibrillation.Methods:A total of 150 patients with permanent atrial fibrillation admitted in the inpatient department and the Southern Branch of Guang′anmen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7 to September 2018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Their plasma D-dimer levels were detected,each Classification and judgment table of TCM Constitution Type was filled in,and the data were analyzed statistically.Results:The TCM constitutions of patients with permanent atrial fibrillation covered all 9 constitution types.Their proportions and plasma D-dimer levels(%,ng/mL)were:qi-deficiency constitution(40.6%,292.48±334.58),phlegm-dampness constitution(18.0%,324.74±346.78),blood-stasis constitution(10.0%,643.3±1627.23),yang-deficiency constitution(9.3%,396.64±404.01),yin-deficiency constitution(8.6%,432.46±664.35),qi-obstruction constitution(6.6%,133.7±79.37),dampness-heat constitution(3.3%,122.00±21.62),balanced constitution(2.6%,252.00±263.03),and allergic constitution(0.6%,13),respectively.Conclusion:The proportions of qi-deficiency constitution and phlegm-dampness constitution in patients with permanent atrial fibrillation were larger.Plasma D-dimer level:blood-stasis constitution>yin-deficiency constitution>yang-deficiency constitution>phlegm-dampness constitution>qi-deficiency constitution>balanced constitution>qi-obstruction constitution>dampness-heat constitution>allergic constitution.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lasma D-dimer level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patients.The plasma D-dimer level was not affected by age.
Key Words Permanent atrial fibrillation; TCM Constitution; D-dimer; Gender; Age; Thromboembolism; Risk assessment; Correlation analysis
中圖分類號:R256.2文獻標識碼:Adoi:10.3969/j.issn.1673-7202.2019.05.057
近年來,隨著人們對房顫的研究逐漸深入,我們越來越認識到心房纖顫對機體所產生的各種不良結果。有研究表明,在房顫所引發的各種并發癥中,血栓栓塞是其中最嚴重的一種[1]。人們通過對血漿D-二聚體水平的研究發現,它可以反映房顫血栓前的狀態。了解其在血液中的情況,有助于了解房顫患者發生血栓栓塞的危險程度[2]。目前,人們對中醫體質學越來越關注。通過相關文獻檢索發現,有關心房纖顫跟中醫體質之間相互關系的的研究數量較少,與房顫相關聯的檢驗指標與中醫體質之間的研究更少。有鑒于此,本研究旨在通過了解永久性房顫患者中醫體質類型與血漿D-二聚體的相關性,探究不同體質類型的永久性房顫患者血栓栓塞的風險程度,以期在臨床治療中可通過中醫藥改善房顫患者的病理體質,發揮中醫中藥的治療特色,更加有效的預防血栓栓塞性疾病的發生。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7年1月至2018年9月收治的永久性心房纖顫患者150例作為研究對象,其中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安門醫院住院患者47例,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安門醫院南區門診患者31例,住院患者72例。
1.2 診斷標準
1.2.1 永久性心房纖顫診斷標準 由心電圖或24 h動態心電圖確診。根據《心房顫動:目前的認識和治療建議——2015》[3]中房顫的分類標準,確定房顫類型為永久性心房纖顫。
1.2.2 中醫體質分型標準 參照《中醫體質分類與判定》(2009版),將體質分為陽虛質、痰濕質、濕熱質、氣虛質、氣郁質、陰虛質、血瘀質、特稟質、平和質9種類型。
1.3 納入標準 1)年齡在18~80歲之間;2)符合永久性心房纖顫診斷標準;3)能夠理解量表內容所表達的含義;d.對調查問卷知情同意者。
1.4 排除標準 1)未成年人或年齡>80歲;2)妊娠、哺乳期婦女;3)近半年內有過嚴重外傷手術史,圍手術期,肺動脈栓塞,DVT,嚴重的動脈粥樣硬化閉塞癥等需要服用抗凝藥物的患者;4)有其他嚴重疾病如急性心肌梗死、主動脈夾層、急慢性心力衰竭(射血分數<50%)、腦血管意外、惡性腫瘤、肝腎功能不全、多臟器功能衰竭、嚴重血液系統疾病、嚴重感染的患者等;5)神志異常;6)長期或近期正在使用抗凝藥物(如華法林、肝素、其他新型口服抗凝藥物等);7)瓣膜相關性房顫。
1.5 脫落與剔除標準 1)不符合納入標準的病例;2)受試者未按要求填寫調查表或填寫不完整;3)臨床調查資料有明顯矛盾者。
1.6 研究方法 收集入組患者性別、年齡、相關病史等基本資料。入組患者于清晨抽血檢測血漿D-二聚體水平(空腹靜脈血)。在知情同意的基礎上,在專科醫師的指導下,客觀如實的填寫《中醫體質分類與判定表》。該量表填寫內容均由調查人員回收分析,并剔除無效問卷。根據心房纖顫的西醫診斷標準及臨床調查要求,結合實際需要,制定《基本病歷資料調査表》。包括;患者基本信息資料、實驗室結果、西醫診斷及中醫體質分型。對入組的每一位研究對象如實填寫《基本病歷資料調查表》,并記錄血漿D-二聚體結果。技術路線見圖1。
1.7 觀察指標 1)150例永久性心房纖顫患者的中醫體質類型分布;2)研究永久性心房纖顫患者中醫體質類型與年齡、性別、血漿D-二聚體水平的相關性。
1.8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2.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計數資料用頻率、頻數進行描述,用χ2檢驗;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比較采用方差分析,不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釆用非參數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 男80例,占53.3%;女70例,占46.7%;男女比例為8∶7。年齡25~80歲,平均年齡(68.09±8.70)歲。
2.2 永久性心房纖顫患者體質類型分布情況 收集的150例永久性心房顫動患者經中醫體質辨識涵蓋所有九種體質類型,其中,氣虛質61例,痰濕質27例,血瘀質15例,陽虛質14例,陰虛質13例,氣郁質10例,濕熱質5例,平和質4例,特稟質1例。所占比例分別為40.6%,18%,10%,9.3%,8.6%,6.6%,3.3%,2.6%,0.6%。
2.3 永久性心房纖顫各體質分型血漿D-二聚體水平比較 因特稟質數據量較少(1例),故只將其余8組體質類型的D-二聚體數據資料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經相關分析,Levene′s方差齊性檢驗提示各組方差不齊(Levene統計量=2.657,P=0.013<0.05),進行基于方差不齊的近似方差分析提示組間均值總體比較有顯著性差異(Welch=4.29,P=0.002<0.05),說明永久性心房纖顫患者各體質類型血漿D-二聚體水平不全相等。血漿D-二聚體水平血瘀質>陰虛質>陽虛質>痰濕質>氣虛質>平和質>氣郁質>濕熱質。見表1。
2.4 男性與女性血漿D-二聚體水平比較以及不同性別中醫體質分布情況 根據研究結果,男性與女性納入的總例數以及血漿D-二聚體水平2組患者總體方差齊(F=2.399,P=0.124>0.05)。將數據資料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t=1.141,雙側P=0.256>0.05,提示男女患者血漿D-二聚體水平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見表2。分析男性、女性不同中醫體質類型分布情況,男性以氣虛質(36.25%),痰濕質(23.75%)和陽虛質(11.25%)為多見,女性以氣虛質(45.71%)、血瘀質(12.86%)、痰濕質(11.43%)為多見。見表3。
2.5 永久性心房纖顫患者年齡與血漿D-二聚體的相關性分析 將永久性心房纖顫患者年齡與血漿D-二聚體應用二元變量相關性分析,得到Pearson相關系數為0.138,P=0.091>0.05,說明永久性心房纖顫患者血漿D-二聚體水平不受年齡的影響。見圖2。
3 討論
目前,體質醫學的研究尚處于摸索階段,在冠心病、高血壓等慢性心血管病中的研究相對較多[4-5],但是缺乏與房顫的相關研究,尤其是關于疾病與臨床客觀性指標之間的研究較少,這導致了中醫臨床辨質論治發揮的受限。在全國很多地方的社區醫療服務機構中都開展了中醫體質辨識服務[6]。許多醫療機構已經將中醫體質辨識作為一項中醫體檢內容開展[7-8]。社區醫療多以慢病防治為主,由于相關政策方面的扶持與推廣,很多社區級醫療機構開展了有關中醫體質方面的研究[9-10]。隨著中醫體質越來越受到臨床醫師以及社會大眾的關注和認可,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相關研究,真正使其成為服務臨床,應用于臨床的重要工具。
圖2 永久性心房纖顫患者年齡與血漿D-二聚體的相關性分析
2018年我國最新的房顫治療指南提出,臨床上對房顫血栓栓塞的風險主要用CHA2DS2-VASc評分來進行評估[11]。相關研究也提示,與傳統的CHADS2評分比較,CHA2DS2-VASc能更好的預測血栓栓塞時間[12]。從近幾年房顫權威治療指南的更新情況來看,西方醫學十分重視對房顫嚴重并發癥的評估,同時也在不斷的更新和改進評估方法。除了CHA2DS2-VASc評分方法外,在房顫相關的實驗室指標中D-二聚體也可作為一個敏感指標應用于臨床[13]。有研究發現,它在血栓剛剛開始形成時就會出現升高,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幫助臨床醫師評估房顫患者的預后以及血栓栓塞風險[14]。房顫在中醫學中多屬“心悸、怔仲”的范疇,中醫目前尚未建立系統性評價房顫患者相關并發癥尤其是血栓栓塞性疾病風險的評分體系。因此,通過此類有關中醫體質的研究,或許可以在中醫學方面為房顫患者并發血栓栓塞風險評估提供一定的思路。本課題通過研究永久性房顫患者的中醫體質類型,以及各種體質類型與血漿D-二聚體的相關性,有助于發現不同中醫體質類型的房顫患者血栓栓塞的風險程度,以期在臨床治療中可通過中醫藥改善房顫患者的病理體質,發揮中醫中藥的治療特色,更加有效的預防血栓栓塞性疾病的發生。但本項研究尚屬小樣本量的前瞻性研究,150例樣本量尚不足以完全說明其內在聯系,仍需更多的大樣本量多中心的類似研究進行印證。
缺血性腦卒中在房顫患者發生的嚴重血栓栓塞事件中占主要地位[15]。如何盡早的對房顫患者進行腦卒中風險評估,如何有效而及時的進行相關干預,如何通過有效的抗凝治療來減低患者的腦卒中風險,這些都是擺在醫務工作者面前亟待解決的問題。據報道[16],在對300例房顫患者進行的相關治療調查中,多數(73%)患者未按相關指南推薦使用抗凝劑,這種情況在房顫腦卒中高危患者中尤其突出。針對西醫經典治療,患者的主動預防意識及治療依從性不高,對該類疾病可能導致的嚴重后果尚無清醒的認識。一部分患者甚至存在因懼怕“不良反應”而抵觸相關治療。目前,國民保健意識逐年提高,中醫“治未病”思想已經深入人心。國家也將“治未病”納入基本公共衛生體系[17]。從中醫“治未病”角度對患者進行宣教,將中醫體質與疾病預防和風險評估緊密結合,更容易獲得患者的認同感,患者的依從性更高,能更好的達到預防與治療的目的。有鑒于此,本研究的目的性和指向性更加明確和清晰,或許在不久的將來,中醫體質辨識在中醫學針對房顫患者血栓栓塞性疾病的風險評估中將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這也就達到了本研究的最終目的。
根據本研究的研究結果,在150例永久性心房顫動患者中,氣虛質(40.6%)和痰濕質(18%)比例最高。也有研究發現[18],在社區中風病患者中,痰濕質和氣虛質也是其主要的體質類型。目前社區醫院對房顫合并腦梗死患者抗凝藥物知曉以及使用率仍然不高[19],不同級別的醫院之間存在較大差距。如前所述,社區醫院中醫體質辨識工作已經普遍開展,存在較好的前期工作基礎,如能重視此2種體質類型的房顫患者,積極的對其體質特點進行干預,或許有助于預防中風病的發生。也可以此為進一步的研究方向,探討永久性房顫患者對其體質干預是否可以有效降低中風發生率。在9種體質類型中,血瘀質的血漿D-二聚體水平最高。該結果只作為永久性心房纖顫一種疾病表現的一種參考,未必能夠反映所有疾病情況,有關血瘀質體質與血栓相關實驗室指標之間的聯系有待其他研究進一步探討。
參考文獻
[1]李奇,廖佳芬,孔彬,等.心房顫動患者左心耳與血栓栓塞關系的研究進展[J].中國心臟起搏與心電生理雜志,2016,30(5):446-448.
[2]馬立永,張盼,蘇亞楠,等.房顫患者微栓子與檢測血漿D二聚體的臨床意義[J].血栓與止血學,2018,24(3):450-451.
[3]中國醫師協會心律學專業委員會心房顫動防治專家工作委,中華醫學會心電生理和起搏分會.心房顫動:目前的認識和治療建議-2015[J].中華心律失常學雜志,2015,19(5):321-384.
[4]李玉華,陳春玲,蔡濤,等.中醫體質與高血壓病相關性的研究進展[J].中醫臨床研究,2017,9(36):12-15.
[5]尹琳琳,劉如秀.中醫體質學說與冠心病的相關性[J].河南中醫,2015,35(8):1785-1787.
[6]尉敏琦,余峰,諸光花,等.808例社區老年高血壓病患者中醫體質狀況與相關因素分析[J].中醫雜志,2016,57(3):228-232.
[7]楊玲玲,薛楊,王燕萍,等.中醫體質辨識在中醫治未病健康管理中的應用[J].中華中醫藥雜志,2018,33(10):4595-4598.
[8]謝冰昕,齊威.北京市某教育機構社區服刑人員雙心疾病患者的中醫體質辨識研究[J].成都中醫藥大學學報,2018,41(2):64-67.
[9]鄒學敏,鄧駿,陸娟,等.中醫體質辨識健康管理系統在社區老年人體檢中的應用[J].河南中醫,2018,38(11):1702-1705.
[10]王兆為,歐陽間英,雷波,等.中醫體質調攝對社區老年糖尿病患者治療效果與生命質量的影響[J].世界中醫藥,2016,11(8):1606-1609.
[11]黃從新,張澍,黃德嘉,等.心房顫動:目前的認識和治療的建議-2018[J].中國心臟起搏與心電生理雜志,2018,32(4):315-368.
[12]Chao TF,Liu CJ,Wang KL,et al.Using the CHA2DS2-VASc score for refining stroke risk stratification in ‘low-risk’ Asian patients with atrial fibrillation[J].J Am Coll Cardiol,2014,64(16):1658-1665.
[13]趙妥.檢測血漿D二聚體、B型鈉尿肽在預測房顫患者血栓形成中的價值[J].血栓與止血學,2018,24(5):838-839.
[14]張曉麗,吳倫寬.房顫波振幅、頻率與左心房內徑、房顫持續時間、D二聚體及腦鈉肽的相關性研究[J].中國現代醫生,2014,52(6):31-33,36.
[15]Hanon O,Assayag P,Belmin J,et al.Expert consensus of the French Society of Geriatrics and Gerontology and the French Society of Cardiology on the management of atrial fibrillation in elderly people[J].Arch Cardiovasc Dis,2013,106(5):303-323.
[16]林琳,包金麗,徐麗娟.房顫住院患者抗凝治療現狀及其影響因素分析[J].濟寧醫學院學報,2011,34(5):345-346,348.
[17]張金玉,王志偉,楊曼茹,等.將中醫“治未病”納入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的探討[J].世界中西醫結合雜志,2016,11(4):560-562,592.
[18]武曉林.基于北京健康鄉村示范社區的中風病二級預防現狀及中醫體質學研究[D].北京:北京中醫藥大學,2018.
[19]史朗峰,趙倩華,張苗怡,等.房顫合并腦梗死患者二級預防抗凝率的初步調查及影響因素分析[J].中國臨床神經科學,2018,26(4):412-417.
(2019-02-20收稿 責任編輯: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