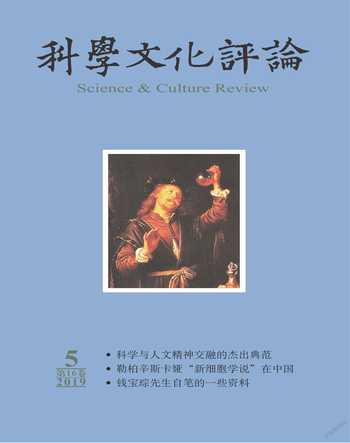致癌、抑癌,還是別的什么? 認識p53基因的40年
李昂
摘? 要? 回顧1979年前后發現P53蛋白的歷史過程,以及此后對該基因研究中的一些標志性的成果和應用。結合不同時期的社會背景和分子生物學的整體發展狀況,對P53研究中的工作方法、思維范式及其影響給出了一定解釋。
關鍵詞? ?p53? 抑癌基因? 分子生物學史
中圖分類號? ?N09
文獻標識碼? ?A
位于人類基因組第17染色體短臂的p53基因(也稱tp53),屬于最早被發現的腫瘤抑制基因(或抑癌基因)之一。它編碼的 P53蛋白(具有393個氨基酸,此處“P”大寫表示蛋白)能調節細胞周期和避免細胞癌變發生,因此被稱為基因組守護者。自1979年該基因被發現以來,人們對它的理解經歷了一次徹底反轉,相關的研究范式也歷經若干重要轉變。最初曾認為p53是個致癌基因,但它作為抑癌基因的本質被揭示出來之后,對其作用機理和參與生理過程的研究大量涌現。2009年,已經可以從Pubmed①中檢索到將近5萬篇相關文章,而到2019年達到近10萬篇,在以單個基因為對象的研究中,穩居發表物排行榜之首[1]。那么,對這個研究最多的基因,我們都知道了些什么,又是怎么知道的呢?本文嘗試對這個紛繁的過程做一梳理,借此管窺分子生物學發展之一斑。
一? ?前史
細胞癌變(惡性增生)是人類出現之前就存在于動物界的現象[2]。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由于人類普遍壽命不長,癌癥并非主要的致死疾病。對它的認知雖然可以追溯到古埃及([3],p.23),并且在現代之前的多位名醫著述中都能找到記載,但水平畢竟受時代的限制①。工業革命之后,一方面隨著人均壽命延長,癌癥發病率升高;另一方面歐洲主要國家的醫療衛生體系逐漸完善,醫院從中世紀那種依附于教會、單純看護病人的場所,發展成具有教育和研究功能的機構,對腫瘤、癌癥這類疾病,才終于開始形成基于現代科學的認識。
18世紀,法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所腫瘤醫院②,法國政府還為尋求癌癥的病因和療法設立了獎金。英國醫生希爾(John Hill,1716—1775)和波特(Percivall Pott,1714—1788)相繼提出某些環境中的化學品可能是引起癌癥的原因[4]。法國醫生德蘭(Henri Fran?ois Le Dran,1685—1770)則第一個推測原發腫瘤通過淋巴擴散到身體其它部位后才會致命[5]。19世紀,費爾肖(Rudolf Virchow,1821—1904)的細胞病理學理論③為現代癌癥研究奠定了一個重要基礎。20世紀初,一些主要工業國的人口壽命達到了50歲,癌癥研究逐漸成為顯學,專門機構陸續建立起來。例如,1902年成立的英國癌癥研究基金會(兩年后更名為帝國癌癥研究基金會,ICRF)④、1937年美國依據國家癌癥法案設立的國家癌癥研究所(NCI)等。大量經費被用以尋找癌癥病因以及研究診療方法。不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人們的認識并沒有顯著提高——很大程度上只是就不同化學制劑驗證希爾和波特的理論。而治療的方案除了手術切除,只有實驗性的X光照射⑤。直到勞斯(Peyton Rous,1879—1970)的病毒致癌說引起學界重視,才開辟了一條更富啟發性的進路,并使癌癥機理的研究從細胞向分子層面深入。
事實上,勞斯早在1911年的論文中就提出:病毒感染有可能導致正常細胞轉化為癌細胞[6]。不過當時病毒對很多人來說還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存在,沒辦法直接進行觀察。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無疑對各領域學術研究的走向和進程都產生了重要影響,病毒與癌癥的關系在此期間并不是個受關注的領域。二戰后隨著噬箘體①成為分子遺傳學的一個重要研究工具,人們對病毒的興趣逐漸提高。而電子顯微鏡的發明,則讓這種比細菌更小的有機體終于暴露在人類的視野下②。20世紀50年代,幾種重要的人類病毒(如水痘帶狀皰疹病毒)被分離鑒定;而1952年脊髓灰質炎在美國的嚴重疫情則促使更多人員經費投入到病毒學這個新興的熱門領域。勞斯在半個世紀前工作的重要性也終于獲得了確認,并于1966年獲得了諾貝爾醫學生理學獎。他的獲獎激發了不少研究者對病毒與癌癥關系的興趣。加上1971年尼克松簽署了新的美國國家癌癥法案,據此擴大了NCI的研究范圍和工作職權,并制定了國家癌癥研究計劃,一場轟轟烈烈的“抗癌戰爭”就此拉開序幕。
二? ?發現
20世紀70年代之前,癌癥研究大多集中于病源學(例如將吸煙與肺癌聯系起來的研究)和經驗性治療方法。然而,勞斯的影響令很多研究小組都忽然對致癌病毒感興趣起來[7]。一些人推測癌癥可能與基因有關。不過,要知道這個時候基因工程還處于襁褓中,人們能夠對基因進行的操作非常有限,而且過程復雜費時。如果利用致癌病毒,想要驗證這個猜想還是可能的,畢竟病毒只攜帶有限的幾個基因。
事實上,早在20世紀初,德國發育生物學家博韋里(Theodor Boveri,1862—1915)就提出過遺傳物質的變化與癌癥相關的概念[8]。1969年,美國NCI的研究人員第一次在論文中正式使用了“致癌基因”(oncogene)一詞[9]。1970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馬丁(G. Steve Martin)博士首次在會議中報告分離出了勞氏肉瘤病毒(RSV,即上述勞斯發現的病毒)中的致癌基因,這是第一個被確認的致癌基因,被稱為Src([3],p.32)。與此同時,很多研究小組也都在開展相關研究。加利福尼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畢肖普(Michael Bishop)和瓦慕斯(Harold Varmus)團隊發現:包括人類在內的許多生物體中都有與Src同源的基因,他們認為病毒中的癌基因來源于一種細胞生物的正常基因(原癌基因)①,病毒在其宿主細胞中復制時將其重組進了自己的基因組[10]。這個發現在1976年發表后,對腫瘤發生機制的認識產生了重要影響,人們很快就找到了多種不同的癌基因,畢肖普和瓦慕斯也因此獲得1989年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
不過,勞氏肉瘤病毒作為實驗工具有一大不足——它主要侵染禽類,而不是哺乳動物[11]。在后來的研究中,更為常用的一種病毒是簡稱SV40的猿猴空泡病毒40(Simian vacuolating virus 40)。這是一種DNA病毒,1960年首次發現于用來生產脊髓灰質炎疫苗的獼猴腎臟細胞中,因其使受感染細胞產生異常數量的液泡而得名。它在獼猴中通常處于不引起癥狀的休眠態,但是在鼠類中會引發多種腫瘤,因此被廣為用于建立實驗動物模型。
SV40表達的蛋白中,最初有兩個被認為與將正常細胞轉化為癌細胞的過程有關,分別稱為大T和小t抗原。在動物實驗中,觀察到它們與小鼠的未知蛋白結合[12]。因此,鑒定這些未知蛋白就成了研究腫瘤形成機制的重要一步。
較早開展相關研究的有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的特格特邁爾(P. Tegtmeyer)所在的團隊。20世紀70年代中期,他們使用SV40轉化細胞的提取物來制備抗血清,再用其免疫沉淀SV40感染細胞的蛋白質,然后通過凝膠電泳分離沉淀下來的蛋白質(混合物)。實驗結果中包括有分子量為50 kDa的蛋白質,后來認為就是P53②,可惜他們當時并沒有關注于此③。而另外六組研究人員,很快獨立觀察到了這種蛋白存在的更多證據,于是在1979年涌現出一系列關于這種分子的報道。
首先發表的是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的萊恩(David P. Lane,1952—)和克勞福德(Lionel V. Crawford,1932—)。他們的實驗思路與上述特格特邁爾的很相似,但是因為解決了制備抗血清的技術問題,大大減少了血清和細胞提取物之間免疫反應中的非特異性沉淀。他們使用純化的大T抗原生產抗T血清,然后與來自SV40轉化小鼠的細胞提取物進行免疫沉淀,獲得了兩種蛋白質:大T抗原和分子量為53 kDa的蛋白質。他們推斷53 kDa蛋白是由細胞編碼的,因為SV40基因組太小,除了已知蛋白之外不太可能有空間再編碼這么大的蛋白。這篇關于大T結合宿主蛋白(P53)的報告發表在1979年3月的《自然》雜志上[13]。
而此時,在大西洋的另一邊,普林斯頓大學的萊文(Arnold Levine,1939—)實驗室和紐約斯隆-凱特琳紀念醫院的奧德(Lloyd Old,1933—2011)研究組也在進行著類似的工作,他們在SV40轉化的不同動物細胞、人類癌細胞、以及用化學或放射性方法轉化的癌細胞中都觀察到了類似的蛋白,分別發表在兩個月后的《細胞》和《美國科學院院刊》上[14, 15]。
接著,紐約大學醫學院的卡羅爾(R. B. Carroll)團隊和法國國家癌癥研究所的梅(Pierre May)等人,各自獨立發現了在不同類型的癌細胞中,存在與大T抗原結合的約55kDa/50kDa的蛋白質,分別發表在8月的《病毒學》和《病毒學雜志》上[16, 17]。最后,在10月的《細胞》上,是倫敦帝國理工學院泊查(Eva Paucha,1949—1988)小組的研究[18]。此外,1980年的《病毒學雜志》上還有一篇麻省理工的洛特(Varda Rotter)為第一作者的文章,不過絕少被提到[19]。
總的來說,上述發現得益于前面十幾年病毒學知識的積累以及免疫學方法的成熟。雖然大部分結果是從SV40轉化的細胞系做出的,不過在用其它方式誘導產生的癌細胞和自然發生的癌細胞中也都找到了P53蛋白。當然,科學家們沒有立即認識到這些發現之間的聯系,每個實驗室都給各自的蛋白取了不同的名字并在后續發表的論文中繼續使用了一陣,因此在這個年輕的領域里制造了些混亂。幸而幾年后他們總算認識到每個團隊都在研究相同的蛋白質。1983年,在英國的瑪麗·居里研究所召開了第一次以這個蛋白為主題的研討會,期間,不同研究小組的代表討論后決定用“P53”來命名他們各自獨立發現的這個蛋白質[1]。此后,P53研討會大約每兩年召開一次,規模不斷擴大。
事后看來,這個發現的思路并不復雜。不過在分子生物學技術尚屬粗放的70年代,實驗中獲得的產物和分析的對象經常是一些混合物。純化抗原以及制備特異性更強的血清,是當時的工作難點。所以在同一年份爆發式的發現P53蛋白,首先是問題集中,其次當時研究手段也只有那么幾種。大多數團隊的工作都是基于SV40介導的細胞轉化,唯一的例外是一項關于腫瘤誘導的免疫反應的血清學研究[15]。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20世紀70年代癌癥研究的主流集中在病毒病因學,同時對腫瘤免疫反應的研究仍在繼續。
三? ?反轉
雖然科學家對P53的發現感到興奮,但一開始只是把它當作一種普通的致癌基因。當然,這也是一個合乎邏輯的推論。因為,在前一個時期的實驗中,觀察到的現象主要包括:(1)P53與SV40病毒的主要致癌蛋白(T抗原)結合,暗示它是大T抗原作用途徑的下游效應物;(2)P53在許多種類的癌細胞中高水平表達。
那么,要進一步研究它是如何起作用的,首先就得拿到cDNA①克隆。克隆(clone)一詞廣義上是指利用生物技術由無性生殖產生與原個體有完全相同基因組之后代的過程。作為名詞的時候,意思是擁有相同遺傳組成的不同個體。在分子生物學、細胞學或生態學等不同語境里,一個克隆可以指:選擇性地復制出的一段DNA序列(或包含這樣一段DNA的細菌所形成的菌落)、一個細胞或是個體。如今,分子克隆是個相對簡單的技術,不過在20世紀80年代初,還是個費時費力,又充滿挑戰的辛苦活兒②。并且,因為要用到重組DNA技術,雖然阿西洛馬會議③已經過去了幾年,人們對此仍然存在一些倫理爭議。
盡管如此,前輩分子生物學家們還是滿懷熱忱地投入到了克隆癌基因的工作中。到1982年為止,至少已經發現了10個癌基因[20]。那一年,若干個研究組相繼克隆到了人的ras基因④。同年,俄羅斯科學院的査莫科夫(Peter Chumakov)第一個克隆到了來自小鼠的p53基因[21]。不過,由于他的文章是用俄語發表的,在P53圈子之外很少為人所知。差不多同時,以色列維斯曼研究所的歐仁(Moshe Oren)也獨立拿到了他的小鼠p53克隆[22],這是他在萊文實驗室時啟動的工作,真正完成花了2年半的時間([3],p.60)。
之后,事情開始逐漸變得容易一些。因為1983年,PCR技術⑤誕生了;不久,DNA測序也實現了自動化。這些新技術令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生物學圈子非常興奮,P53的研究此時也進入了建構時期,在1984—1985年間,幾個研究組相繼克隆了人類的p53基因,并得到了基因全長的克隆[1]。人們普遍認為它是一個重要性和作用機制有待揭示的致癌基因,為其研究開發了大量動物模型和工具[1]。
不過,其實也有一些實驗結果不甚符合這個觀點,比如1984年沃爾夫(David Wolf)和洛特的研究,他們發現在一個小鼠白血病細胞系中,p53基因是被逆轉錄病毒插入失活的[23, 24]。后來其他人也在小鼠細胞中觀察到類似的現象[25]。此外,洛特等人還發現,在白血病來源的人類細胞系HL60中,p53的編碼區幾乎被刪除了,無法產生P53蛋白。對這個結果最簡單的解釋是:p53的丟失催生了癌變,暗含的意思就是——正常p53的功能是防止癌癥所必需的[1]。這些提示P53可能是腫瘤抑制因子的線索,事后看來很明顯,但當時要么被忽視,要么被用另外的方式解釋,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腫瘤抑制基因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還只是一種假設。
腫瘤抑制基因的概念來源于20世紀60—70年代的一些細胞雜交實驗。在這些實驗中觀察到,腫瘤細胞內的遺傳物質變異或損失,可被其他細胞的遺傳物質修補或替代,并使腫瘤細胞的致癌特性丟失或延緩。由此推測,腫瘤細胞內丟失了可抑制腫瘤生長的DNA[26, 27]。不過,這種基因的存在,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才通過對視網膜母細胞瘤的研究證實。視網膜母細胞瘤是嬰幼兒中常見的惡性腫瘤,具有明顯的家族遺傳傾向。關注腫瘤遺傳因素的研究者,很早就注意到了這個研究對象。1971年,卡納德森(AG. Knudson)提出了關于這一類基因的“兩次打擊”理論,認為:只有一個基因的兩個等位基因位點均受到變異或損傷時,基因的正常表達和功能才完全丟失。相對于導致癌基因病變的“一次性突變”學說,需要兩次打擊,才能使抑癌基因失活。因此,抑癌基因屬于隱性基因[28]。1983年,研究者發現視網膜母細胞瘤患者中的13號染色體發生了缺失,這就意味著抑制腫瘤發生的基因被刪除,從而確定了視網膜母細胞瘤易感基因(retinoblastoma susceptibility gene, RB1)作為一個腫瘤抑制基因,同時也證實了上述推測的重要性。1986年,RB1基因克隆成功。在隨后的幾年中,研究人員又發現了一些腫瘤抑制基因,例如人們比較熟悉的、與乳腺癌相關的BRCA1基因等。
此時,圍繞p53的工作也集中在克隆測序階段,各地的實驗室獲得了很多不同來源的p53克隆,并用于驗證其在細胞中的功能。最先意識到問題的是萊文實驗室——他們的一個p53克隆完全無法像其他克隆那樣將正常細胞轉化成癌細胞。他們最后對這個克隆以及之前使用過的,包括從其他實驗室獲得的p53克隆進行了測序,結果發現沒有兩個克隆在序列上是相同的,這說明先前實驗中的克隆至少有一些(如果不是全部的話)實際上在p53編碼區攜帶了突變。當來源于正常組織的小鼠野生型p53的序列被測定之后(1988),這一點得到了確鑿的證明。這樣一來事情就比較明朗了——癌細胞中的p53經常是突變的(包括許多實驗室使用的cDNA克隆),并且只有攜帶突變的p53 cDNA能夠在實驗中發揮轉化作用,野生型的p53不行[1]。
在約翰霍普金斯,另一個研究腫瘤分子生物學的重鎮,佛格施坦因(Bert Vogelstein)實驗室證明:在人類結直腸腫瘤中,野生型p53等位基因常常因突變,缺失或兩者兼有而失去功能。也就是說癌細胞不能保有正常的p53。這是一個里程碑式的發現[29]。同時,萊文和歐仁實驗室獨立開展的功能分析表明:在表達癌基因c-myc和H-Ras的培養細胞中,野生型p53的過表達能夠有效地抑制轉化(與腫瘤來源的P53突變體的轉化活動形成鮮明對比),即作為腫瘤抑制基因在起作用[30]。這兩項研究均發表于1989年,標志了P53研究的轉折點。
早先病毒學家的理論給癌癥研究帶來了一種主流思路,即:細胞癌變是一種獲得性的性狀(而非基因功能缺失造成的)。抑癌基因的發現則帶來了一種研究范式的轉換,破除了p53是致癌基因的思維壁壘。當然,必須指出的是,20世紀80年代初期克隆基因的效率很低。因此在當時的實驗設計中,從P53蛋白豐度高的細胞中提取相應的mRNA,是很自然的想法。可想而知最初成功獲得cDNA克隆的幾組人馬,使用的都是來自被轉化的細胞(癌細胞)而不是正常組織細胞中RNA。
四? ?大熱門
在把p53當做癌基因研究了10年之后,發現它其實是個腫瘤抑制基因,并且,是在人類癌癥中最常發生突變的一個[31]。那么進一步鑒定P53在癌癥、發育和其它生理過程中的作用,對于攻克癌癥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因此,在20世紀90年代,P53吸引了大量研究,甚至可以說誕生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
回到以色列維斯曼研究所任職的洛特,在其對歷次P53研討會的回顧中,曾經做了一個生動的比喻:1988年的 P53就像一只丑小鴨,大家對它是什么都還很困惑。而到了1991年的會上,它已經變成了眾人眼中的白天鵝①。那個時候,人們已經明確了有一種野生型P53蛋白和許多突變型P53蛋白。之前的十幾年,研究的都是p53突變基因。那么正常的p53在細胞中本來是起什么作用的呢?
其實早在1983年,就發現轉化細胞中的P53水平與快速細胞生長本身有關,推測它是一種與細胞周期有關的蛋白[32]。事實上,許多癌基因和抑癌基因都涉及到細胞周期的調節過程,比如上文提到的(視網膜母細胞瘤)RB蛋白。而接下來的一些研究則證明,P53是一種轉錄因子。
轉錄因子是指能夠結合在某個基因上游特異核苷酸序列上的蛋白質,這些蛋白質能調控該基因的轉錄。它們通常至少具有DNA結合結構域與效應結構域這兩個功能區①。1989年,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的菲爾茲(Stanley Fields)和博士生宋玉圭(Ok-Kyu Song)開發了一種稱為酵母雙雜交的實驗體系,用于驗證蛋白質分子存在相互作用②。隨即,多個實驗室利用此方法于1990年獨立證明了P53蛋白能夠發揮轉錄因子的功能[33, 34, 35]。
接著,通過總結1991—1992年間的一系列報道(以及之前的部分工作),確定P53在修復DNA損傷中的重要作用[36]。不過,更重要的一項工作是發現了P53與MDM2蛋白之間的負反饋調控回路。MDM2是一種泛素連接酶,最初在小鼠中發現它與P53蛋白形成復合物,并且可以抑制P53作為轉錄因子的活性[37]。后來知道當P53蛋白濃度高時,就會啟動MDM2基因表達,MDM2與P53結合后,將其與泛素連接。連接了泛素的P53遂進入蛋白降解過程,由此形成負反饋調節,使正常細胞中的P53蛋白一直維持在一個較低的基礎水平。此后,又發現許多其他分子參與P53蛋白的反饋調控環路,說明其擁有一個網絡化的調控系統[38]。
MDM2-P53負反饋環路,是細胞中調節P53濃度的重要機制,在1992年提出后,就被眾多系統生物學家和計算機生物學家所關注。并成為研究信號通路內調控途徑的經典模型。在實用研究領域,該環路也是眾多大有希望的抗癌藥物的作用靶點[38]。
此外,1992年的另一項里程碑是獲得了p53基因敲除的小鼠模型[39]。構建基因敲除(或突變)的生物模型,是研究某個基因功能的重要實驗方法。其基本思路是:用生物技術手段在某個模式生物中使感興趣的基因失活,觀察其生理和表型的變化,由此推測該基因的功能;后續還可以在這個模型中重新導入該基因或其產物,驗證前面的推測。這代表了分子生物學研究的一種范式,很多科學家致力于此類工作。在90年代,這是一項很有難度的工作,如果某個實驗室建立了一個重要的突變體模型,往往意味著確立了在該領域的領先地位。
基于上述進展,及其日益高漲的熱度,1993年,《科學》雜志將P53評為年度分子[40]。1994年,歐美的一些學者聯合構建了一個數據庫。通過文獻檢索,匯集了p53基因中的2,500多個突變。存放在EMBL數據庫中,并以電子形式免費提供[41]。后來,其它一些組織也建立了自己的P53數據庫①。
不同的突變體,表現不同的生理特征。通過對它們的研究,可以對單個基因做精細的解讀。在此,也許不應該拿太多的知識細節來轟炸讀者,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些前期工作中,也有中國的貢獻,即發現在黃曲霉素所引發的肝癌中,存在特異位點的P53突變[42]。此項工作的思路由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的孫宗棠醫生提出,樣品采集自江蘇啟東地區。但受實驗條件所限,當時只能與美國學者合作進行②。
2009年,《自然-綜述》組織了一個關于P53的特刊,描述當時對這一領域的理解。簡單說,P53在許多信號傳導途徑中起著節點的作用,從而調節從生殖、發育到維持基因組穩定性(DNA修復)和細胞老化、凋亡的各種重要生物活性。一些證據表明P53的單體或二聚體可以與同一家族的另外兩種蛋白P63或P73形成雜四聚體,這三種轉錄因子產生的組合可能具有更加復雜的調控功能[1]。由于其在協調細胞周期對DNA損傷和其它應激信號的反應中至關重要,P53蛋白在避免癌癥發生的機制中扮演了細胞守護者的角色。在超過半數的人類癌癥中,都會發現p53基因的突變[43]。這也是它受到特別關注的原因。
此后的10年里,關于P53不斷有新的調控因子、信號通路、代謝途徑被發現、解釋,并從中提出新的抗癌策略。文獻數量增加了數萬篇,并且隨著新的基因編輯技術成熟完善,構建動物模型變得更加方便、精確,可以料想研究文獻的產生速度還將進一步提升。在維基百科這樣的大眾知識來源中,已經給出了P53與上百種其他生物分子相互作用的鏈接。但是,對普通人來說,最關心的大概還是:知道了這些,到底對攻克癌癥有什么用呢?
五? ?基于P53的癌癥治療
鑒于P53在癌癥中的核心角色,圍繞其開發抗癌藥物和治療方法,在工業界和學術界都是一個重要的努力方向。早在1996年的P53研討會上,就已經開始討論基于P53的療法。那一年,德克薩斯大學安德森癌癥中心的杰克羅斯(J. A. Roth)等人率先嘗試了在人體內進行p53基因治療。他們通過直接注射表達人p53的逆轉錄病毒載體,治療非小細胞肺癌[44]。其思路簡單說就是用病毒載體將正常的p53基因導入癌癥患者體內,希望它能補償突變的p53所導致的功能缺失。后來的研究表明,使用腺病毒載體,更適合控制成本進行大規模規范化生產。德克薩斯州的Introgen Therapeutics公司就是采用了這個方法。其產品名為Advexin,在美國進行了不少臨床試驗,對多種癌癥都報道了頗有希望的試驗數據。然而,在2008年最后的審批環節該公司卻撤回了申請,產品未能上市①,公司隨后破產。
實際上,世界各地有好多機構都曾經開展過這方面的研究。幸運的是,同類藥物在中國受到了官方支持。1998年3月,在深圳成立了賽百諾基因技術有限公司,研發“重組人P53 腺病毒注射液”。同年12 月,這個藥物獲得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進入Ⅰ期臨床試驗。接著的幾期臨床試驗乃至生產都得到了來自科技部的項目經費支持②。2003年,產品名為“今又生”(Gendicine)的重組Ad-p53腺病毒注射液獲得藥監局頒發的新藥證書,2004年1月和3月,又陸續獲得準字號生產批文和藥品GMP認證,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獲得官方批準上市的基因治療新藥,作為治療頭頸癌的基因治療產品進入商業市場[45]。使用這個產品的病例不時在科學期刊上有報道[46],讓西方人頗感扭曲和受到挑戰的是,2009年Introgen Therapeutics進入破產程序之際,賽百諾公司卻得到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批準,開始了在美國的臨床試驗[47]。
與基因治療相比,更常規的新藥研發進路是尋找一些以P53系統為標靶的小分子藥物。比如抑制P53-Mdm2蛋白相互作用的Nutlins,以及可以使腫瘤細胞內突變的P53蛋白改變構象以恢復其正常功能的PRIMA1[47]。這些是比較成熟,已經進入臨床試驗的。然而大部分基于P53的新型抗癌療法,都還在實驗初期。部分問題是P53參與了如此多的細胞過程,提高其效果可能會導致不必要的副作用。總的來說,治療的思路很多,據2015年的統計,至少有114家公司正在積極開發針對P53信號通路的藥物③。除了治療上的應用,P53基因的表達狀態也是癌癥前期診斷的重要指標之一。
相對于早期腫瘤分子生物學家的謹慎[48],隨著對P53調控途徑的了解愈加充分,現在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對其應用前景表示樂觀,并對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做出了展望[49]。但爭論仍在繼續,認知也在對觀念的不斷重新審視中獲得推進。
六? ?結語
過去40年對P53研究的歷史,以豐富的例證說明了發現新知識的過程是如何充滿意外,以及研究范式和新的方法論突破如何使我們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感知相同的事實①。同時還可以看到對一個分子的深入研究如何引領了一個相當大的學科領域的發展。
可以說,p53是人們目前了解最多的一個基因,也恰恰因此,它為人們打開了更多的未知。2009年在紀念P53發現30周年的文章中,稱一個理性時代才剛剛開始,在其研究真正成熟之前,還將有很多個第一次[50]。2019年5月②,在紀念P53發現40周年的會議上,吳家睿教授又引用莎士比亞的名言“凡是過往、皆為序章”(What’s past is prologue),來表達對未來發展的期待。誠如會議中有學者所說:對P53的認識,有如盲人摸象,看到了多樣的局部,但還沒有揭開真實完整的全貌。
如前所述,從文獻數量來看,關于P53的新發現并未隨著時間的增長而下降,并且很多都發表在普通生物學者所仰視的CNS級③刊物上。參與過P53研究的團隊也越來越龐大。當我們置身其中的時候,每一步進展都曾經帶來巨大的喜悅和希望。但不久之后回顧,很多當時令人激動萬分的發現,就只是大屏幕上的一個小小的像素。這種以還原論為指導的生命科學研究現狀,大概還要維持一段時間。以生命現象之復雜多樣,能否達到像物質科學中那樣精準的規律性認識,仍屬未知。
伊芙琳·凱勒(F. Keller)在《基因的世紀》(The Century of the Gene)中,對主導20世紀遺傳學研究的還原論思想提出挑戰,試圖推動生物學家創造一套比“基因”概念更能處理生物組織之復雜性的術語[51]。雖然,她的建議當時(以及現在都)沒有可操作性,但是,結合P53的認識歷程,也許對現代分子生物學的基本方法進行反思也是有必要的。
在人類認識p53的40年中,出現了很多現象級的人物和教科書式的案例,筆者受能力所限,做此粗疏的整理,聊作紀念之外,也期待更多學人關注。
參考文獻
[1] Levine, J., Oren, M.. The first 30 years of P53: growing ever more complex[J]. Nature Reviews Cancer, 2009, 9(10): 749—758.
[2] Rothschild, M., Tanke, H., Helbling, M., Martin, D.. Epidemiologic study of tumors in dinosaurs[J]. Naturwissenschaften, 2003, 90: 495—500.
[3] Armstrong, S.. P53, the gene that cracked the cancer code[M].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Sigma, 2014.
[4] Hajdu, I.. A note from history: Landmarks in history of cancer, part 2[J]. Cancer, 2011, 117(12): 2811—2820.
[5] Faguet, B.. A brief history of cancer: Age-old milestones underlying our current knowledge databas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ncer, 2015, 136: 2022—2036.
[6] Rous, P.. A sarcoma of the fowl transmissible by an agent separable from the tumor cells[J]. Th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 1911, 13: 397—411.
[7] What Price the Crusade for Cancer Research?[J]. Nature New Biology, 1971, 230(16): 225—226.
[8] Calkins, N.. Book Review: Zur Frage der Entstehung maligner Tumoren[J]. Science, 1914, 40(1041): 857—859.
[9] Huebner, R., Todaro, G.. Oncogenes of RNA tumor viruses as determinants of cancer[J]. Proc. Nat. Acad. Sci, 1969, 64: 1087—1094.
[10] Stehelin, D., Varmus, E., Bishop, M., Vogt, K.. DNA related to the transforming gene(s) of avian sarcoma viruses is present in normal avian DNA[J]. Nature, 1976, 260: 170—173.
[11] Tsuchida, N., Murugan, K., Grieco, M.. Kirsten Ras* oncogene: Significance of its discovery in human cancer research[J].? Oncotarget, 2016, 7(29): 46717—46733.
[12] Tegtmeyer, P., Schwartz, M., Collins, K., Rundell, K.. Regulation of Tumor Antigen Synthesis by Simian Virus 40 Gene A[J]. Journal of Virology, 1975, (6): 168—178.
[13] Lane, P., Crawford, V.. T antigen is bound to a host protein in SV40-transformed cells[J]. Nature, 1979, 278(5701): 261—263.
[14] Linzer, I., Levine, J.. Characterization of a 54K dalton cellular SV40 tumor antigen present in SV40-transformed cells and uninfected embryonal carcinoma cells[J]. Cell, 1979, 17: 43—52.
[15] DeLeo, B., Jay, G., Appella, E., Dubois, C., Law, W., Old, J.. Detection of a transformation-related antigen in chemically induced sarcomas and other transformed cells of the mouse[J]. PNAS, 1979, 76(5): 2420—2424.
[16] Melero, A., Stitt, T., Mangel, F., Carroll, B.. Identification of new polypeptide species (48-55K) immunoprecipitable by antiserum to purified large T antigen and present in SV40-infected and -transformed cells[J]. Virology, 1979, 93: 466—480.
[17] Kress, M., May, E., Cassingena, R., May, P.. Simian virus 40-transformed cells express new species of proteins precipitable by anti-simian virus 40 tumor serum[J]. Journal of Virology, 1979, 31: 472—483.
[18] Smith, E., Smith, R., Paucha, E.. Characterization of different tumor antigens present in cells transformed by simian virus 40[J]. Cell, 1979, 18: 335—346.
[19] Rotter, V., Witte, N., Coffman, R., Baltimore, D.. Abelson murine leukemia virus-induced tumors elicit antibodies against a host cell protein, P50[J].? Journal of Virology, 1980, 36: 547—555.
[20] Reddy, P., Reynolds, K., Santos, E., Barbacid, M.. A point mutation is responsible for the acquisition of transforming properties by the T24 human bladder carcinoma oncogene[J]. Nature,1982, 300(5888): 149—152.
[21] Chumakov, M., Iotsova, S., Georgiev, P.. Isolation of a plasmid clone containing the mRNA sequence for mouse nonviral T-antigen[J]. Doklady Akademii Nauk SSSR (in Russian), 1982, 267(5): 1272—1275.
[22] Oren, M., Levine, J..? Molecular cloning of a cDNA specific for the murine p53 cellular tumor antigen[J]. PNAS, 1983, 80(1): 56—59.
[23] Wolf, D., Rotter, V.. Inactivation of P53 gene expression by an insertion of Moloney murine leukemia virus-like DNA sequences[J]. Mol Cell Biol, 1984, 4: 1402—1410.
[24] Wolf, D., Rotter, V.. Major deletions in the gene encoding the P53 tumor antigen cause lack of P53 expression in HL-60 cells[J]. PNAS, 1985, 82: 790—794.
[25] David, Y., Prideaux, R., Chow, V., Benchimol, S., Bernstein, A.. Inactivation of the P53 oncogene by internal deletion or retroviral integration in erythroleukemic cell lines induced by Friend leukemia virus[J]. Oncogene, 1988, 3: 179—185.
[26] Harris, H., Miller, J., Klein, G., Worst, P., Tachibana, T.. Suppression of malignancy by cell fusion[J]. Nature, 1969, 223: 363—368.
[27] Stanbridge, J.. Suppression of malignancy in human cells[J]. Nature, 1976, 260: 17—20.
[28] Knudson, G.. Mutation and Cancer: Statistical Study of Retinoblastoma[J]. PNAS, 1971, 68(4): 820—823.
[29] Baker, J.. et al. Chromosome 17 deletions and P53 gene mutations in colorectal carcinomas[J]. Science, 1989, 244: 217—221.
[30] Finlay, A., Hinds, W., Levine, J.. The P53 proto-oncogene can act as a suppressor of transformation[J]. Cell, 1989, 57: 1083—1093.
[31] Vogelstein, B., Sur, S., Prives, C.. P53: The Most Frequently Altered Gene in Human Cancers[J]. Nature Education, 2010, 3(9): 6.
[32] Winchester, G.. Tumor vorology: P53 protein and control of growth[J]. Nature, 1983, 303: 660—661.
[33] Raycroft, L., Wu HY, Lozano, G.. Transcriptional Activation by Wild-Type But Not Transforming Mutants of the P53 Anti-Oncogene[J]. Science, 1990, 249(4972): 1049—1051.
[34] Fields, S., Jang SK. Presence of a potent transcription activating sequence in the P53 protein[J]. Science, 1990, 249(4972): 1046—1049.
[35] O’Rourke, W., Miller, W., Kato, J., Simon, J., Chen DL, Dang CV, Koeffler, P.. A potential transcriptional activation element in the P53 protein[J]. Oncogene, 1990, 5(12): 1829—1832.
[36] Kastan, B., Kuerbitz, J.. Control of G1 arrest after DNA damage[J].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1993, 101(Suppl 5): 55—58.
[37] Momand, J., Zambetti, P., Olson, C., George, D., Levine, J.. The mdm-2 oncogene product forms a complex with the P53 protein and inhibits P53-mediated transactivation[J]. Cell, 1992, 69(7): 1237—1245.
[38] Brady, A.,? Attardi, D.. P53 at a glance[J]. Journal of Cell Science, 2010, 123(15): 2527—2532.
[39] Donehower, A.. et al. Mice deficient for P53 are developmentally normal but susceptible to spontaneous tumours[J]. Nature, 1992, 356: 215—221.
[40] Koshland, E.. Molecule of the year[J]. Science, 1993, 262(5142): 1953.
[41] Hollstein, M., Rice, K., Greenblatt, S., Soussi, T., Fuchs, R., S?rlie, T., Hovig, E., Smith-S?rensen, B., Montesano, R., Harris, C.. Database of P53 gene somatic mutations in human tumors and cell lines[J]. Nucleic Acids Res, 1994, 22(17): 3551—3555.
[42] Hsu, C., Metcalf, A., Sun, T., Welsh, A., Wang NJ, Harris, C.. Mutational hotspot in the P53 gene in 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s[J]. Nature, 1991, 350: 427—428.
[43] Toledo, F., Wahl, M.. Regulating the P53 pathway: in vitro hypotheses, in vivo veritas[J]. Nature Reviews Cancer, 2006, (6): 909—923.
[44] Roth, A., Nguyen, D., Lawrence, D., Kemp, L., Carrasco, H., Ferson, Z., Hong WK, Komaki, R., Lee JJ, Nesbitt, C.. et al. Retrovirus-mediated wild-type P53 gene transfer to tumors of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J]. Nature Medicien, 1996, 2: 985—991.
[45] Pearson, S., Jia H, Kandachi, K.. China approves first gene therapy[J]. Nature Biotechnology, 2004, 22: 3—4.
[46] Zhang WW. et al. The First Approved Gene Therapy Product for Cancer Ad-p53 (Gendicine): 12 Years in the Clinic[J]. Human Gene Therapy, 2018, 29(2): 160—179.
[47] Lane, P., Cheok, F., Lain, S.. P53-based Cancer Therapy[J]. Cold Spring Harbor Perspectives in Biology, 2010, 2: 1—24.
[48] Angier, N.. Natural Obsessions[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8.12.
[49] Levine, J., Hu W, Feng Z. The P53 pathway: what questions remain to be explored?[J]. Cell Death and Differentiation, 2006, 13: 1027—1036.
[50] Soussi, T.. The history of P53[J]. EMBO reports, 2010, 11(11): 822—826.
[51] Keller, F.. The Century of the Gene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Oncogene, Tumor Suppressor, or Something Else?
40 years of? p53 studies
LI Ang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review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discovery of P53 protein in 1979 and some landmark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this gene along with applications derived from them. Social and knowledge backgrounds are provided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tudy of P53 in the context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lecular biology. While how experiment methods and working paradigms effect P53 studies have been explained to some extent.
Keywords: p53, tumor suppressor, history of molecular bi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