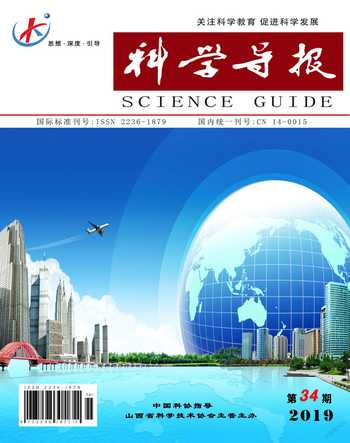淺談敦煌壁畫中的暈染法
敦煌石窟壁畫藝術包羅萬象,壁畫數量巨多,在內容上能通過不同的故事來表達佛教藝術;在表達方式上通過現實主義、抽象藝術、象征手法的結合來表現莫高窟壁畫藝術的特點。在布局結構上,以人物造型和線條勾勒以及賦彩上色等各方面系統地反映了各個時期的藝術風格及其演變和傳播,融匯了古今多文化影響下的繪畫技法,人物造型獨特,突出體現了各個時期下東西方文化藝術貫通融合的現象。吸收了來自西域文化色彩,又和中原文化特色不同,便出現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結晶,因此可以發現大量來自西域的凹凸暈染技法繪制的形象,可以說在當時畫家們接受外來藝術技法的意識十分開放。
一、佛教藝術東傳影響下的暈染技法
在中國繪畫史上,有很多表現色彩的獨特技法,其中就有凹凸暈染法(稱為“天竺遺法”),因為敦煌是古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樞紐,佛教及佛教藝術主要通過敦煌進入到內地,暈染法也從西域傳播到我國,在傳播過程中形式上發生了變化,成為十六國末期至北周時期敦煌壁畫賦色的重要特征之一。隨著向中原地區的不斷傳播和發展,西域式暈染法與當時敦煌的歷史環境、宗教思想、審美理想緊密結合。凹凸暈染法是中國古代畫家在學習吸收印度藝術而有所創新的一種暈染法。隨著佛教東傳,在敦煌早期洞窟壁畫中的人物形象受西域繪畫技法的影響,作為一種外來宗教藝術,傳播到中原必須要適應當地的民族風俗,要符合儒家倫理道德觀念的審美,同時會受到當地文化思潮的影響,否則不可能扎根發展。所謂的中原暈染法也就形成了。這種暈染法主要是在眼瞼、鼻子、面頰呈現胭脂或赭紅色,注重膚色的表現。我們稱這種方法為高染法。但這種方式是需要在已涂好的底層肌膚上一次性暈染,才能透出肌膚的血肉質感和輕薄色澤,這樣暈染的作品會富有鮮活的生命力。但就必要增強繪畫的技術,比如在人物的頭發等方面要表現出光彩,就要在黑色下涂石黃做底色,接著再涂黑色,兩種顏色滲透之后,這樣畫出的頭發豐富又有變化,這種技法稱為“對比度”。在填色過程中,一些畫家突破了線稿的束縛,大膽地用色蓋線,從而形成了一種新的線條色彩融合方式。雖然唐代在盛世時期鮮艷奪目,璀璨壯麗,能夠表現出健康、濃烈的色彩時代美已被列入繪畫史,但在衰落時期也會有其色彩風格來取代,形成一種新風尚。其實在中國早期就有對于暈染法的創新,可以說這是外來佛教中國化的體現。這種新的暈染技法一直延續到元代。
現如今我們在欣賞和觀看敦煌壁畫時,會有很多色彩是我們所不能理解的,例如,人的膚色從白膚色變為灰色或黑色。這種變色曾經被誤認為是古人在繪畫中使用的含鉛顏料。但在現代先進的科學技術考察后表明,敦煌壁畫色彩的變化并不是因為使用的原顏料中含有鉛的成分,而是有以下三個原因:一是顏料當時是用朱丹或用朱丹調和的顏色,使它經過一千多年的歲月打磨,不斷受到空氣當中的氧氣,濕度,二氧化碳,光照等綜合因素的影響最終使他變成現在所呈現出的非常不同的顏色。第二是因為含有植物色素的顏色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直接褪色。三是土壤問題,莫高窟的土壤是一種砂礫巖,經過河水上千年的沖刷,使大量巖體含有一種化學元素——“堿”,再與植物顏料和礦物質顏料發生化學反應才導致變色。所以我們把現在可以觀測到的暈染方法分為以下四種:
1.吸收凹凸暈染法并結合中原傳統繪畫形式,在人物臉頰部分暈染紅色,著重表現肌膚色澤與立體質感。從北魏后期開始,形成中西融合的畫風。
2.變中原傳統暈染法結合西域式疊染,分多次渲染,不同于在肌膚輪廓邊緣暈染,而是突出的部分(眉棱,鼻梁、上眼瞼、下巴以及兩頰)重疊暈染兩三次,使突出的部分更加紅潤,從原壁畫中能夠清楚的看到它的染色程序。
3.采用中原地區發展起來的暈染方法,僅在人物的面頰、上眼瞼、下巴略施赭紅以表現肌膚的顏色,有一定的立體感。
4.素面不施暈染。這四種風格也是傳播過程以及時代發展的必要結果。西域式和中原式風格逐漸成為統一的新民族風格。
二、西域式暈染法與中原暈染法的融合
(一)西域式暈染法
莫高窟的早期洞窟就是十六國北涼至北朝(北涼第268、272、275窟,北魏第248、251、254、257、435窟,西魏第249窟,北周第296、428窟)的洞窟。可以發現早期洞窟中人物形象大多頭戴寶冠,面容豐滿或是條長,神情溫婉恬靜,上身半裸,斜披天衣,下著長裙,身形動態不大;在服飾上明顯保留了西域和印度、波斯風俗。而凹凸法則適用于臉部和身體的著色,來表現立體感。以莫高窟北魏第254窟、北魏第254窟為例,可以看到佛、菩薩、天人和供養人形象雖然發生變色,但在暈染時,會先在人物的肌膚邊緣,用粗黑線或褐色粗線暈染,染兩眼周圍與鼻梁之間,臉蛋處及下頜,用一支干凈帶清水的毛筆暈開,暈染第一次,然后再涂一次色暈染第二次,再涂白色。最后在白眼上描繪雙眼,點眼仁。肌膚變色后,出現今天所看見的“小字臉”。這種暈染技法,尚未脫離西域畫風的影響。逐漸變化后的色彩,讓人感到神秘莫測。
(二)西域暈染法與中原暈染法的融合
敦煌石窟藝術從一開始就受到了西域,尤其是龜茲佛教藝術的影響。這種影響在敦煌進行了選擇和融合,已經發生了變化。如龜茲壁畫中的菩薩,(豐乳、細腰、大臀)一旦進入到生活習俗有差異、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敦煌,就必定會受到當地文化的影響,伴隨著暈染法也會發生改變,因此,在進入敦煌以后也將其鄉土色彩顯現出來。莫高窟壁畫具有其獨特的色彩特征,尤其是北朝壁畫與漢代傳統壁畫之間的區別。色彩濃烈夸張,對比很強,在整個壁畫藝術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壁畫通過統一的肅穆的色調襯托了佛教的莊重以及其宗教的神秘色彩。有些部分為了展現色彩的對比,往往大膽地在人物的皮膚、頭發采用藍色、綠色等。在北朝石窟第254窟中也可看到,中心塔柱東側的藥叉、婆藪仙形象有綠頭發、綠眉毛、綠胡須。畫工在給壁畫上色的時候逐漸開始大膽嘗試,創造出了許多違反自然規律的色彩形象,以強烈的色彩進行對比來烘托整個畫面,及具藝術美感。到了西魏、北周,一改凝重、肅穆的土紅底色,并以粉白色為底,畫面逐漸顯得明快亮麗、具有生機。在色彩運用上較為豐富,除了基本的純色外,還出現了一些簡單的復合色,畫面開始柔和起來。原本西域藝術的色彩分配也被突破,形成了中原風格。這主要也是由于中原魏晉之風的傳入,形成一種可以過渡西域和中原的色彩,其造型結構上顯露出一種向中原魏晉風格發展的過度性特征。這種糅合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分格后行成的新的風格,在莫高窟第249 窟南壁說法圖中就有提現,人物面部和身體的部分更加修長,與西域式暈染很好的結合統一了起來。但外來色彩藝術已經根深蒂固,在莫高窟西魏時期的第285號洞窟中就可以發現西域式和中原式兩種暈染藝術并存的現象,洞窟中除西壁佛龕外部的壁畫是西域風格外,其他面皆為中原風格,雖身體賦色仍用西域式暈染法,但面部卻是“清瘦”,身體修長,裝束華麗飄逸,有一種灑脫優美之風,這種風格有自己獨特的畫風及造型,其主要表現為人物面部清瘦,頭戴寶冠,冠飾繁瑣,復雜,長發皆為兩分式長發,長垂直至肩,秀麗的蘭葉描技法了。北壁七鋪說法圖中的協侍菩薩形象,也皆是頭戴寶冠,冠飾鮮花,插三尾孔雀羽,廣額秀頜,面相清瘦,表情和善,細長修眉、梅花狀的朱唇,八字形嘴髭,兩發為當時婦女流行的兩分式長發,發梢彎曲,長垂于肩膀,身材修長,外著封襟式的長袍,下身穿間色長裙,衣帶飄逸,腳著高履,整體造型已完全擺脫了西域風格的痕跡,為典型的“秀骨清像”式菩薩。自北魏晚期以來中原藝術才是對敦煌新風格最有力的影響。這種風格也結合了西域風格和敦煌本土色彩,所以在隋朝結束魏晉南北朝300多年以來的分裂局面完成統一后的這樣一個新歷史環境中,形成了一種新的統一的民族風格和時代特征。可見中原風格深受西方繪畫的客觀、明暗寫實方式的影響,但沒有固定的光源和陰影,具有主觀色彩,在莫高窟第409窟的東側墻的供養人畫像中主要采用了這種暈染法,然而在主要人物中這種暈染法仍然使用不多,但西域暈染法主要運用在佛和菩薩身上。這兩種暈染法并存在同一座石窟中是很常見的。北周時期是在探索和發掘新暈染法的時期,占據主要地位的仍然是西域暈染法。隋唐以后,賦彩方式吸收了更多中原特色,西域式則開始逐漸弱化,莫高窟藝術在這個時期更是體現出了本民族的風格。
(三)中原式暈染法的全面體現
莫高窟藝術從北魏晚期開始,不僅出現了新的內容,而且出現了褒衣薄帶、歡快自然、無拘無束的形象,顏色也從土紅色變得濃重靜穆,西域式暈染法被中原傳統繪畫而取代,因此出現明亮而生動的畫面和形象,形成這個時期新的藝術風格。我們稱之為中原式風格。從壁畫風格、面相服飾上看,表現的更深入細致。從造型藝術的角度來看,形成了“秀骨清像”和“褒衣博帶”的藝術特點。當然這和當時魏晉玄學所提倡的放蕩不羈愛自由的思想室友直接關系的。而且繪畫的手法豐富細微,人物性格的類型變化明顯。魏晉南朝文人的生活思想和審美思想是中國風格的基礎。在當時文人們飲酒、作詩、言談、以“苗條”為美,并且穿很寬大衣服,向往神仙般的生活,逐漸風靡全國。北魏晚期,這種風格開始傳到了敦煌。它體現了當時中國上流社會普遍存在的“脫俗瀟灑、內心智慧”得風貌。在莫高窟第220窟中《維摩潔經變》主人公維摩詰的面部肌肉用厚重的赭紅暈染,用西域式暈染法在額頭和眉弓凸起部分加以渲染,再加以線條蒼勁有力、溫和婉轉,塑造出這位長者與文殊菩薩辯論時的興奮,可以看到他目光炯炯有神,氣勢咄咄逼人。來自于寫實逼真的渲染,大大增強了造型的真實性和吸引力。在同一壁畫中的帝王和旁邊臣子的胡須經過線描與暈染結合,能夠顯示出蓬松柔軟的藝術效果。從莫高窟現存的第323號洞窟的佛教史跡畫中可以非常直觀的看出其中已褪色的山水壁畫,山水部分暈染了大片的綠色和赭色,山水和帆船交織在整個畫面的遠景處,正體現出“山在虛無縹緲間”的意境。這種渲染方式一直沿用到五代、宋初的許多屏風壁畫中,這種色彩表現的突破充分反映了中西文化融合所產生的繪畫色彩的新發展方向,中原暈染法全面體現出來了。
結語
敦煌佛教藝術借鑒了西域、印度佛教藝術和吸收了西域暈染法,起初僅是模仿,接著便會選擇吸收和改造它,可以用畫史上“依經鑄容”形容。后便從表現形式(整體人物造型、面相特征、衣冠服飾、神情風采以及思想內容)上做了基本改變,而西域暈染法也與民族傳統暈染技法相融合,逐漸創造出一種既能夠表現身體肌膚的立體感又可以表現肌膚色彩和光澤的中式暈染風格,在這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到唐代時期達到巔峰時期,形成自成體系的佛教文化藝術。反應出古往今來人們那種追求至高無尚的時代精神,體現出中華民族豐富的文化藝術底蘊、至上的精神涵養以及高尚的民族品質,它突破了時空和地域的差異,突破了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差異,最終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這就是敦煌壁畫藝術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之處。
參考文獻:
[1] 劉穎.淺談敦煌石窟壁畫的藝術魅力.東北師范大學碩士論文[D].2011:(03):32-40
[2] 劉學榮.略談凹凸暈染法對中國繪畫藝術的影響.美術大觀[J].2015:(03):47-47
[3] 黃曉霞.莫高窟壁畫賦彩中的外來因素.西北美術[J].2002:(04):34-35
[4] 萬庚育.敦煌壁畫中的技法之一暈染.敦煌研究[J].1985:(03):32-40
[5] 余遠花.淺析敦煌壁畫的藝術風格.中華文化論壇[J].2008:(S1):175-176
[6] 李翔.論“藝術皇帝”李隆基對唐代樂舞繁榮的貢獻.陜西師范大學碩士論文[D].2010
作者簡介:
王斐(1994.6-),女,漢族,籍貫:甘肅通渭人,陜西師范大學美術學院,18級在讀研究生,碩士學位,專業:美術,研究方向:國畫花鳥
(作者單位:陜西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