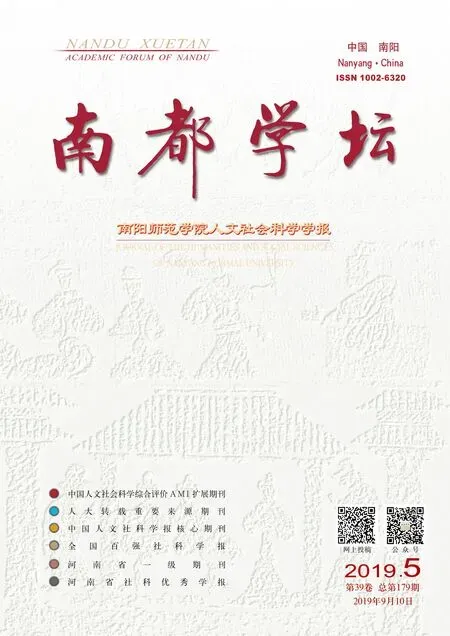漢陶文“小兒受賜”試解
王 子 今
(中國人民大學 國學院暨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北京 100872)
陳直《關中秦漢陶錄》著錄“漢小兒受賜陶蓋”,其中“小兒受賜”文意不明朗。對照相關歷史文獻,可知“小兒”應當理解為“受賜”所得。如此與下文“天佑世昌”及同組文字“長宜子孫”形成合理的邏輯關系。“小兒受賜”陶文與漢代常見的“宜子”“宜子孫”“長宜子孫”“永宜子孫”“保子宜孫”等富含社會意識史信息的文字資料有同樣的文化內涵。作為重要的文物實證,該陶文真切反映了當時社會在宗法制傳統影響下對于“子孫益昌”的普遍向往與深切期待,從而具有兒童生活史料的價值。
一、陳直著錄與“小兒受賜”疑義
陳直《關中秦漢陶錄》第一集《陶器類》著錄一件漢代文物“漢小兒受賜陶蓋”。有考證文字:
漢小兒受賜陶蓋
陶質青灰。出土地點未詳。現存劉漢基處。文外圍八字,“小兒受賜天佑世昌”。內圍四字,“長宜子孫”。系就原器考釋,較拓本為明晰。[1]
陶蓋外圍文字顯示對天賜、天佑的感動。而“小兒受賜”文意并不明朗。
“小兒受賜”之“小兒”,似可理解為“受賜”行為的主體。支持這種判斷的例證如《呂氏春秋·異寶》:“五員載拜受賜。”(1)奇猷案:“載、再通。”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校釋》,學林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551頁,第557頁。《史記》卷三二《齊太公世家》:“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2]1490《史記》卷三〇《平準書》:“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余萬斤。”[2]1422《后漢書》卷二九《郅惲傳》:“戶曹引延受賜。”[3]1028《續漢書·禮儀志中》:“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3]3130諸葛亮《又與李嚴書》:“吾受賜八十斛,今蓄財無余。”[4]《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裴松之注引《魏書》載公令曰:“昔趙奢、竇嬰之為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濟成大功,永世流聲。”[5]29依此類文例理解,“小兒受賜”即“小兒”承受了天賜。這樣說來,“小兒”即陶蓋制作者或陶蓋主人之自稱。而有行為自主能力者自稱“小兒”文例,漢代文獻似罕見。比較著名的故事有《后漢書》卷七〇《孔融傳》李賢注引《融家傳》:“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年四歲時,每與諸兄共食梨,融輒引小者。大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3]2261又《藝文類聚》卷八六引《文士傳》:“孔融年四歲,與諸兄食梨,輒取其小者。人問其故,答曰:‘小兒法當取小者。’”(2)《太平御覽》卷三八五引《孔融別傳》曰:“孔文舉年四歲時,每與諸兄共食梨,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由此宗族奇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中華書局用上海涵芬樓影印宋本1960年2月復制重印版,第1779頁。事又見《太平御覽》卷九六九引《大士傳》曰:“孔融年四歲,與諸兄食梨,輒取其小者。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此宗族奇之。”第4296頁。[6]孔融“年四歲”時自稱“小兒”,而“漢小兒受賜陶蓋”之“小兒”文字如果理解為此器主人自稱,似乎是不合適的。
前引“受賜黃金二十余萬金”“受賜八十斛”“受賜千金”等,“受賜”所得在“受賜”文字之后。甲渠候官遺址出土漢簡可見“……□□哉忽受賜□帛絮金銀青泉為矛鈴金輪大廄名馬政□而□□□為善急□勿緩政兆也”(E.P.T43:57A)簡文[7],所謂“受賜□帛絮金銀青泉為矛鈴金輪大廄名馬……”也是同樣的文序表述形式。但是上古文獻所見,也多有將“受賜”獲得書寫于“受賜”二字之前的。
如《孔叢子》卷二《雜訓》:“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8]《春秋繁露》卷一六《祭義》:“五谷,食物之性也,天之所以為人賜也。宗廟上四時之所成,受賜而薦之宗廟,敬之性也,于祭之而宜矣。”[9]又《鹽鐵論·貧富》:“大夫曰:‘余結發束脩,年十三,幸得宿衛,給事輦轂之下,以至卿大夫之位,獲祿受賜,六十有余年矣。’”[10]所謂“受賜”“膏雨”或“膏雨之所生”,“受賜”“五谷”或“四時之所成”,“受賜”“卿大夫之位”等,各種不同獲益的表述,均在“受賜”一語之前。出土文獻也有類似文例。如馬王堆漢墓帛書《戰國縱橫家書》之四《蘇秦自齊獻書于燕王章》:“……而王以赦臣,臣受賜矣。”[11][12]
對照相關文獻,陳直曾經關注的“漢小兒受賜陶蓋”之“小兒受賜”,“小兒”可以理解為“受賜”所得。如此與下文“天佑世昌”及內圍文字“長宜子孫”形成合理的邏輯關系,構成完整的文意。
二、“小兒”語義
秦漢社會稱謂“小兒”用以指代成年人時,有親昵義,也有輕蔑義。“小兒”因“人道未成”,受到社會普遍的輕視[13-14]。當然也有作為中性稱謂的情形,如《續漢書·禮儀志中》劉昭注補引《漢舊儀》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是為虐鬼;一居若水,是為罔兩蜮鬼;一居人宮室區隅,善驚人小兒。”[3]3128又《三國志》卷三二《蜀書·先主備傳》:“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小兒于樹下戲。”[5]871
然而在很多情況下,“小兒”又用以指代“愛”“善”與“恩慰”的對象。如《史記》卷一〇五《扁鵲倉公列傳》:“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2]2794《后漢書》卷一二《彭寵傳》:“寵謂守奴曰:‘若小兒,我素愛也……’”[3]504《后漢書》卷八〇下《文苑列傳下·禰衡》:“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修。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3]2653《后漢書》卷一九《耿弇傳》:“弇道聞光武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光武留署門下吏。弇因說護軍朱佑,求歸發兵,以定邯鄲。光武笑曰:‘小兒曹乃有大意哉!’因數召見加恩慰。”[3]704這些文例中,“小兒”語意均和善親切。
“小兒”又用以稱自家宗族晚輩。《后漢書》卷二四《馬援傳》:“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并肩側身于怨家之朝乎?”[3]833
明確稱自己的兒子為“小兒”者,也有文獻實證。如《后漢書》卷八二下《方術列傳下·劉根》:“(史)祈之亡父祖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坐。’顧而叱祈曰:‘汝為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靈!可叩頭為吾陳謝。’”[3]2746又《三國志》卷六《魏書·袁尚傳》裴松之注引《先賢行狀》:“公引見,謂配:‘知誰開卿城門?’配曰:‘不知也。’曰:‘自卿子榮耳。’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此!’”[5]206又《三國志》卷四七《吳書·吳主傳》裴松之注引《魏略》載孫權致書曹丕外交代表浩周,言“遣子入侍”事,稱孫登為“小兒”:“欲遣孫長緒與小兒俱入,奉行禮聘,成之在君。”“小兒年弱,加教訓不足,念當與別,為之緬然,父子恩情,豈有已邪!”[5]1128自稱親生子為“小兒”者,還有《三國志》卷四八《吳書·三嗣主傳·孫皓傳》裴松之注引《吳錄》:“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褥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5]1169李肅“其母”稱李肅為“小兒”。
依照當時稱謂習慣,推定“漢小兒受賜陶蓋”所謂“小兒受賜”之“小兒”指承“受”天“賜”所得子,是有一定可信度的。
三、“小兒受賜”與“天佑世昌”“長宜子孫”
漢代文物資料所見“宜子孫”主題,作為當時社會意識普遍傾向的反映,保留了鮮明的歷史文化記憶。

“小兒受賜”陶文與漢代常見的“宜子”“宜子孫”“君宜子孫”“長宜子孫”“永宜子孫”等出土文字資料有同樣的文化內涵。作為重要的文物信息,透露出當時社會在宗法制傳統影響下對于“子孫益昌”的普遍的關注與深切的期待,從而具有兒童生活史料的價值。作為當時社會意識與文化傾向的反映,也有值得重視的意義。
通過相關思想史分析可以確知,“漢小兒受賜陶蓋”外圍文字“小兒受賜天佑世昌”與內圍文字“長宜子孫”,意思是完全對應的。
四、“受福”“受賜”“受福賜”語式
上文指出“漢小兒受賜陶蓋”之“小兒受賜”,“小兒”可以理解為“受賜”所得,除前舉接受賜予之獲益在“受賜”二字之前陳說句式之外,其實還可以舉出其他旁證。例如《后漢書》卷三〇下《郎覬傳》:“《尚書洪范記》曰:‘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3]1073此“受福”之“福”,應當是包括“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天象的。此句式可以與前說“受賜”比照。“德厚受福”句,王先謙《后漢書集解》作“德厚交福”[23]。然而百衲本《后漢書》、《文選補遺》、《冊府元龜》、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鄭樵《通志》(4)相關內容可參見范曄:《后漢書》,百衲本景宋紹熙刻本;陳仁子編:《文選補遺》卷一五《郎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卷五三七《諫諍部·直諫四·郎覬》,中華書局據明刻初印本1960年6月影印版,第6430頁;王應麟著,張三夕、楊毅點校:《漢藝文志考證》卷一“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中華書局2011年1月版,第138頁;鄭樵:《通志》卷一〇七下《列傳二十下·后漢·郎覬》,中華書局據1935年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十通》本1987年1月影印版,第1551頁至第1552頁。等,均引作“德厚受福”。《漢書疏證》卷二四《藝文志一》言“《后書》郎覬奏便宜四事《尚書洪范記》”也引作“德厚受福”[24]。看來郎覬所言“受福”的文字記錄是大致可以確定的。
“受福”“受賜”語式存在一定的近似關系。文獻所見“受福賜”之說可以為證。《漢書》卷七〇《陳湯傳》載劉向上疏:“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于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劉向就吉甫故事,言“周厚賜之”,而“吉甫燕喜,既多受祉”,并為甘延壽、陳湯“未獲受祉之報”等境遇叫屈。就劉向所引《詩》,顏師古注:“《小雅·六月》之詩也。鎬,地名,非豐鎬之鎬。此鎬及方皆在周之北。時獫狁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吉甫薄伐,自鎬而還。王以燕禮樂之,多受福賜,以其行役有功,日月長久故也。”[25]由劉向言“周厚賜之”“吉甫燕喜,既多受祉”可知,“受祉”即接受了“厚賜”,也就是“受賜”,而顏師古解釋為“受福賜”。
顏師古“受福賜”之說,是不是唐代學者對漢代語言習慣因時代距離而形成的誤解呢?我們在確定的漢代文獻中,其實是可以看到“受福賜”的文字實證的。《隸釋》卷一《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寫道:“諸所造作,煥然成就。仲氏宗家,并受福賜。”[26]所謂“并受福賜”與“多受福賜”在語式上的近似是明朗的。
《說文解字·夕部》:“多,緟也。從緟夕。夕者,相繹也,故為多。緟夕為多,緟日為疊。凡多之屬,皆從多。,古文,并夕。”段玉裁注:“緟者,增益也,故為多。多者勝少者,故引伸為勝之稱,戰功曰多,言勝于人也。”“相繹者,相引于無窮也。抽絲為繹,夕繹疊韻。說從重夕之意。”對于“,古文,并夕”,段玉裁說:“有并與重別者,如棘、棗是也。有并與重不別者,、多是也。”[27]316《說文·竝部》:“竝,倂也。從二立,凡竝之屬皆從竝。”段玉裁注:“《人部》‘倂’下曰:‘竝也。’二篆為轉注。鄭注《禮》經古文竝,今文多作倂。是二字音義皆同故也。”[27]501漢代人習用文字“并”和“多”的關系,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并受福賜”與“多受福賜”語義的接近。那么,我們關于“受福”“受賜”的討論對于理解“小兒受賜”陶文的意義,也因此得到了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