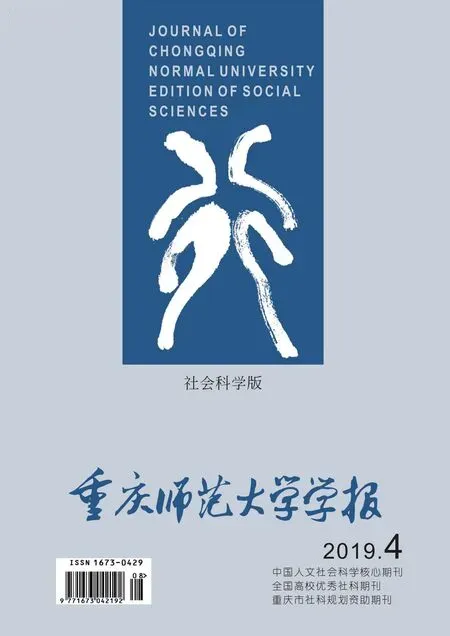《周易》對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影響
——以思維方式和言說方式為視角
張 紹 時
(湖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 長沙 410081)
中西古代文學批評在思維方式和言說方式上有著較大的差異。在思維方式上,西方重分析論證和理性歸納,中國重內省體驗和直覺感悟;在言說方式上,西方注重對術語、概念、范疇、命題的清晰定義及闡釋,中國古代文學批評較少對術語、概念、范疇、命題進行界定,多是以富有詩意的象喻方式予以圓活言說。總體來說,一種偏向邏輯推演與理論體系的建構,一種偏于詩性感悟與象喻妙譬,兩種文學批評根植于不同的文化土壤,呈現出兩種不同的批評路徑。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這些特征與誕生于中華文化濫觴期的《周易》有著密切關系,劉勰《文心雕龍·原道》就說道:“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贊神明,易象惟先。”[1]“易象”是中華文明最早的文化符號之一,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尤其是它所體現出來的思維方式和言說方式對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有著根本性的影響。
一、《周易》的思維方式和言說方式

《周易》“立象盡意”的言說方式能夠實現對不可言說之物的言說,具有一般語言所不具備的表達功能,主要是通過“象”的隱喻、象征功能實現的。《易傳》論述到這種言說方式的功能:“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10]《周易》六十四卦之所以能夠涵蓋宇宙萬物、窮盡天下之理,關鍵在于它“言曲而中”“事肆而隱”,這種言說效果是通過卦象這一特殊的言說方式實現的。關于這一言說方式,古今學者都進行了討論,如唐人孔穎達說道:“凡易者象也,以物象而明人事,若詩之比喻也”。[11]今人高亨進一步說道:“《周易》的比喻沒有特定的被比喻的主體事物,當然不出現于文中,僅僅描述做比喻的客體事物,因此,可以應用在許多人事方面。這實有類似于象征。”[12]學者對于《周易》表義方式雖然稱法不一,但他們所說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即都不直接言說,而是以“隱”的方式言說,人們可以通過卦象的比喻、象征之義比類出自己所在情境的吉兇禍福。
言說方式往往是思維方式的反映,《周易》的思維也是以“象”為中介的。王樹人將這樣一種思維方式稱為象思維,并指出“‘象思維’構成《周易》的思維之本”(見王樹人、喻柏林《〈周易〉的“象思維”及其現代意義》,《周易研究》1998年第1期。此外,王樹人在《“象思維”視野下的“易道”》(《周易研究》2004年第6期)、《回歸原創之思:“象思維”視野下的中國智慧》(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等論著中對《周易》的象思維進行了探討)。雖然象思維也是先秦《老子》《莊子》等哲學著作中的重要思維方式,但是它在《周易》中體現最為典型、最為成熟,并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易傳》對《易經》所體現的象思維進行了理論概括,圣人創設卦的“取象”“立象”過程就是象思維的典型體現,《易傳》說:“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13]這一思維過程始終伴隨著“象”,它以包犧氏所觀宇宙萬物之具象為思維起點,思維過程以“象”展開,最終又通過形象直觀的卦象將思維結果表現出來。在象思維過程中,“觀”和“取”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此“觀”不同于外在于事物的目視之觀,不是對象化之“觀”,而是類似于老子、莊子觀道的內在之觀,它是由具象之觀上升到整體之觀,在“觀”的過程中物我兩忘,在整體直觀中可以把握到宇宙萬物的本體之“道”。“取”就是要從萬物中進行“類”的概括,包犧氏創設的八卦之所以能歸類天下萬物的情態,就是因為八卦不只是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八種事物的取象,而是象征八類不同的意義。《說卦傳》對八卦的卦義進行了說明,乾義為健,坤義為順,震義為動,巽義為入,坎義為陷,離義為麗,艮義為止,兌義為說,每一卦的卦義是固定的,但其取象不是固定的,是可以不斷比類引申的。《說卦傳》對八卦中每一卦的多種取象進行了舉例說明,如《乾》卦有天、圜、君、父、玉、金、寒、冰、大赤、良馬、老馬、瘠馬、駁馬、木果等多種取象,后來象數派學者如虞翻等又對其進行了補充。由八卦之義推演出萬物之象,運用的是比類方法,《系辭》對此進行了描述:“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14]八卦“引而伸之”成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包含有三百八十四爻,這個卦象系統通過觸類引申能包含天下萬物之象,能窮盡天下萬事之理。這一過程中的“取象”是通過“比類”實現的,“比類”又是“取象”思維的一部分,二者密切相關。
由上可知,《周易》的象思維起源于觀萬物之象,這一過程中圣人以整體直觀的方式超越了具象之觀而把握形而上的道,并以感性、形象的卦爻符號將其所觀所感表達出來,力圖以隱喻、象征、比類的方式窮盡天下萬事萬物之理。《周易》的象思維有著鮮明的特征,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其一,具象性。象思維起源于觀具象,并以“象”為主要運思手段,最終又創設了具象性的卦形符號,不僅“觀物取象”如此,“立象盡意”“制器尚象”等都是象思維的體現,這一過程始終是以具象方式展開的。其二,直覺性。在《周易》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下,人與自然萬物是可以直覺感應的,《系辭》對這一過程進行了描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15]“無思”“無為”表示象思維過程不是邏輯分析過程,而是一種自然而然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中能夠實現直觀感應而達到道的層面。《老子》的“滌除玄鑒”“至虛極,守靜篤”的虛靜心態及《莊子》的“心齋”“坐忘”等也都是這樣一種直覺的體道境界。其三,整體性。象思維以整體觀來看待萬物,認為宇宙萬物都是由道(太極)所生,它們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人也是這一整體中的一部分。圣人“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此“觀”不是對天、地進行對象化的觀照,而是把自己融入天地之中,并與天地融為一體的整體之觀,這一過程就如莊子所說的“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16],在對萬物的觀照中走向合一。
《周易》的象思維是富有詩性的思維,實際上是原始思維的延續。意大利學者維柯的《新科學》認為史前人類思維大體相同,是以詩性的、想象的、類比的、以象喻義的方式看待世界,這種思維不同于文明時代人類的邏輯思維,維柯將其稱為“詩性智慧”。維柯指出,在原始時期“人類對于遼遠的未知的事物,都根據已經熟悉的近在手邊的事物去判斷”。[17]法國學者列維·布留爾的《原始思維》對原始人的思維進行了舉例:“為了表示‘硬的’,他們說:象石頭一樣;表示‘長的’就說大腿;‘圓的’就說象月亮,象球一樣。”[18]這就是以具體的“象”代替“類”概念的詩性思維。在《周易》的象思維中,圣人往往以身邊熟悉的事物喻指難以言說的深奧之理正是這一詩性思維的體現,如為了說明“大過”的道理,圣人以大澤淹沒樹木去表達,《大過》卦形上兌為澤、下巽為木,象征“大為過甚”。《周易》的象思維對原始思維又有所發展,作為“類”的卦象由具象上升至普遍的哲理,又能反過來概括這一類事物中的任何一物,這是一個由具象到抽象、由抽象再到具象的思維過程。而原始思維在總體上停留在外表的、個別的層面上,沒有達到對象深層的共性,就如黑格爾所說:“還談不上內在的和外在的,意義和形象,這兩方面的分別。”[19]《周易》的象思維具有形象性特征,與今人所說的形象思維相似,但又有所不同,形象思維是20世紀從蘇聯傳入的概念,又被稱為“藝術思維”。形象思維不脫離具體的形象,它的目的是通過想象、聯想去塑造藝術形象,想象和聯想中的兩個事物有著相似性。象思維所比類的兩個事物可能有相似性,也可能是完全不相及的事物,象思維的目的是實現對道的體悟,圣人將其思維結果用八卦表達出來,八卦具有“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的功能,《周易》之“象”是直接通向本體之道的。
二、《周易》的思維方式和言說方式對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影響
《周易》的象思維和“立象盡意”的言說方式對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產生了深遠影響。從言說方式來看,《周易》認為“言不盡意”,因而“立象以盡意”,這一觀點在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中得以繼承,批評家往往以象喻式方式言說。比起用理性邏輯分析的言說方式,象喻式言說方式在表意上有著特殊的優勢,更能表達批評家“只可意會,不能言傳”的直覺體悟。這在舊題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中得到很好體現,《二十四詩品》每品用十二句比喻式的韻語描述了一種審美風格,比如“沖淡”一品,什么是“沖淡”及如何實現“沖淡”,司空圖以象喻方式言說:“素處以默,妙機其微。飲之太和,獨鶴與飛。猶之惠風,荏苒在衣。閱音修篁,美曰載歸。遇之匪深,即之愈希。脫有形似,握手已違。”郭紹虞對此解釋說:“此詩在前面極寫沖淡之貌,最后四句始寫沖淡之神。沖淡本不可說,這樣一路說來,亦就活躍于紙上矣。”[20]如果用概念性的語言來解釋這些風格是有很大難度的,以象喻的方式言說“沖淡”卻有著梅圣俞所言“作者得于心,覽者會以意”[21]的言說效果。古代批評家對“言”與“象”的言說效果深有體會,李東陽在《麓堂詩話》就說道:“蓋正言直述,則易于窮盡,而難于感發,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寫,反復諷詠,以俟人之自得,言有盡而意無窮。”[22]“有所寓托”就是寓意于象,“形容摹寫”就是對文學創作及批評過程中取象的描述,以象喻的方式能暗示出語言所不能言說的無窮意蘊。
《周易》對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立象盡意”的言說方式的影響還體現在具體的“取象”方法上,古代文學批評根據《周易》創設卦象系統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的方式進行取象。首先,從“近取諸身”來看,古代批評家往往將文章看作人體,如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認為“文章當以理致為心腎,氣調為筋骨,事義為皮膚”[23],將文章的理致、氣調、事義分別看做人之心腎、筋骨、皮膚。正因如此,中國文學批評形成了諸如首、頷、頸、骨、體、脈、主腦等一系列與人之身體有關的術語,又形成了諸如肥、瘦、狀、病、美等一系列與人之外形特征相關的術語,還形成了諸如風骨、形神、氣韻、神韻等一系列與人之生命特征有關的范疇。不少學者認為中國文學批評缺乏體系性,這是從西方的邏輯體系而言的,其實中國文學批評是有體系性的,只不過是不同于西方文學批評呈現出顯在的邏輯體系,而是一個“潛體系”,即將作品看成一個生命體,每一篇詩文、每一個作家的作品、每一個時代的作品都構成一個生命體,每一部文學批評著作也是一個生命體,從整個文學批評體系來看,它是由以上所說與人之身體、外形特征及生命特征有關的一系列范疇所構成的生命體。中國古代文學批評“近取諸身”的象喻言說與將文學作品視為一個生命體是密切相關的,錢鐘書先生在《中國固有的文學批評的一個特點》中說道:“這個特點就是:把文章通盤的人化或生命化(Animism)。《易·系辭》云:‘近取諸身……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可以移作解釋:我們把文章看成我們自己同類的活人。”[24]古人之所以這樣作喻,是因為他們認為人體形式與藝術形式在本質上是相通的,都是生命性的表現,文學批評活動是直觀生命的活動,文學批評過程是一個生命體與另一個生命體的對話。
其次,從“遠取諸物”來看,《周易》“立象盡意”言說方式對文學批評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以人工之器物喻指作品。《周易》所說的器物制作與文章寫作有著相通之處,器物之喻成為一種文學批評方式。這在劉勰《文心雕龍》中表現最為突出,書名之“雕”的對象本是玉、石等器物,此用以喻指對文章的雕琢。全書貫穿著以器物制作喻指文章寫作的思想,如《文心雕龍》言及“附會”說:“若筑室之須基構,裁衣之待縫緝矣。”[25]“附會”對于文章的作用就如建筑房屋要打好基礎、裁制衣服要細針密縫一樣。《文心雕龍》一些重要的術語如雕琢、刻鏤、陶鈞、陶染、陶鑄、矯揉、镕鑄等都是這一思想的體現。第二,以自然之物喻指作品。在《周易》中,圣人“觀物取象”要“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文學批評家受此影響,善于從大千世界的日月星辰、花草樹木中吸取素材運用到文學批評中,如鐘嶸《詩品》評詩說道:“范詩清便宛轉,如流風回雪。丘詩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26]此以“流風回雪”“落花依草”分別將范云詩宛轉纏綿、丘遲詩情韻嫵媚的特點表達出來。這一言說方式在舊題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中運用非常普遍,如以“碧桃滿樹,風日水濱”形容“纖秾”風格,以“海風碧云,夜渚月明”形容“沉著”風格,以“月出東斗,好風相從”形容“高古”風格。[27]第三,以動物喻指作品。在《周易》中,圣人“觀物取象”的重要內容之一是“觀鳥獸之文”,文學批評繼承了這一觀物傳統,善于抓住動物的特征用以喻指作品特征,如《文心雕龍》談及文章之“風骨”說道:“其為文用,譬征鳥之使翼也。”[28]“風骨”對于文章的作用就好比征鳥使用有力的雙翼一樣。再如杜甫以詩論詩的《戲為六絕句》,以“龍文虎脊皆君馭”喻指初唐四杰才氣縱橫,以“未掣鯨魚碧海中”喻指當世一些人寫詩缺乏雄健才力和闊大氣魄。
以上是從言說方面探討了《周易》對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影響,而言說方式是由思維方式決定的,《周易》對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影響更體現在思維層面。從創作過程來看,文學批評活動也是“取象”的過程,古人并沒有今人這樣嚴格的學科意識,古人的文學批評活動本身也是文學創作活動,批評家最終通過“立象”的方式來言說批評過程中的直觀感悟與審美體驗。古代文論家論述創作構思的“取象”過程也同樣適用于文學批評構思的過程。陸機《文賦》對文學活動的“取象”過程作了精彩描述,在整個過程中需要“佇中區以玄覽”,即處于老子“滌除玄覽”的觀道狀態,文學批評開始時要“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游萬仞”,即排除一切雜念,忘卻物我,進入到“虛靜”狀態,這樣才能“情曈昽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即文學批評過程中作者情感的逐漸鮮明與構思中“象”的逐漸清晰是相互促進的。接著是進行“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的“取象”活動,可謂是上窮碧落、下及黃泉對萬物之象進行“萬取一收”。在“取象”運思過程中會出現兩種情況,一是“沉辭怫悅”難以覓象,二是“浮藻連篇”直觀得象,經過批評家精心取象,最終是“籠天地于形內,挫萬物于筆端”,以鮮明、生動的“象”表達作者之意。[29]劉勰《文心雕龍》對文學批評的“取象”過程探討更為深入,《神思》篇就是論述文學創作思維的專篇,《神思》認為“取象”要超越時空的限制,即達到“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的狀態,內心不受外物束縛而極為自由。《神思》篇接著所說的“寂然”“悄焉”“虛靜”等都是對“取象”心境的描述,這種狀態可以達到“神與物游”的境界,最終是“神用象通”“窺意象而運斤”,以“立象”方式表達作者情思。但在“立象”的過程中有時“密則無際”,即言、象、意達到混融,有時“疏則千里”,即面對著言不盡象、象不盡意的困境。[30]《文心雕龍》其他一些篇目也或多或少涉及“取象”問題,如《物色》篇的“流連萬象之際”[31]就是指文學創作與批評過程始終伴隨著象而發生,《養氣》篇的“紛哉萬象,勞矣千想”[32]指文學創作與批評過程因反復思考而出現紛紜復雜之象。
文學批評過程中出現的比興思維與《周易》“取象比類”思維在本質上是一致的,章學誠就說道:“深于比興,即其深于取象者也。”[33]比興本質上就是“取象”思維,并且也具有“比類”的特征。鄭玄注《周禮·春官》所載“六詩”之“比”時說:“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34]“比”是不直言,通過比類言之。劉勰《文心雕龍·比興》對“比”進行了更深入的闡釋,指出“比”具有“切類以指事”“取類不常”的特征。[35]關于“興”,王逸《楚辭章句·離騷序》將其界定為“引類譬喻”[36]。強調“興”是通過某一物的譬喻而使人聯想到這一類的事物。劉勰更是以《周易》取象比類的“稱名也小,取類也大”[37]的特點來闡釋興。可見比興都是對“類”的選取,皎然《詩式·用事》就指出:“萬象之中義類同者,盡入比興。”[38]不可否認,古代文學批評以比興方式言說一方面是受到《詩經》以來文學創作傳統中比興手法的影響,但另一方面也潛在地受到《周易》“取象比類”思維的影響,尤其是將比興與“類”相關聯起來,比興在文學批評中已不僅是一種修辭手法,而是成為一種“取象”思維。
不僅如此,《周易》象思維所具有的具象性、直覺性、整體性特征對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思維也產生了重要影響,并具有與此類似的特征。從具象性來看,文學批評過程是以象思維展開的,文學批評中的比興就是象思維的體現,批評家通過隱喻、象征的方式寓思想于形象之中。文學批評的象思維決定了它的言說方式,即較少運用理性分析方式言說,而是以象喻方式實現詩性言說。從直覺性來看,文學批評“取象”過程不是邏輯分析過程,更多的是一種直覺。鐘嶸《詩品》提出的“直尋”就是這一特征的體現,鐘嶸對“直尋”所得詩句進行了舉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39]“直尋”是以“即目”“所見”為基礎,實際上是在觀物過程中與物實現直覺感通,最終把握到本質之“象”,這一過程正是劉勰《文心雕龍·神思》所說的“神用象通”“窺意象而運斤”的過程。此外,如舊題王昌齡《詩格》所說的“神會與物”、司空圖《與李生論詩書》所說的“直致所得”、嚴羽《滄浪詩話》的“妙悟”說等都是象思維直覺性特征的體現。從整體性來看,批評家憑借直觀感悟的方式把握作品,在物與我的相互感應中打破了心與物的界限,個人體悟與審美對象合一,把握到作品的整體之美。批評家往往以象喻方式言說其對作品的整體把握,如鐘嶸《詩品》評謝靈運、顏延之的詩說:“謝詩如芙蓉出水,顏詩如錯彩鏤金。”[40]這就是基于對謝靈運、顏延之的整體風格的把握。由此可知,以形象的方式進行思維和言說是中國古代文學批評詩性特征的重要體現,這一種詩性傳統從根本上來說,是對《周易》的象思維方式和“立象盡意”言說方式的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