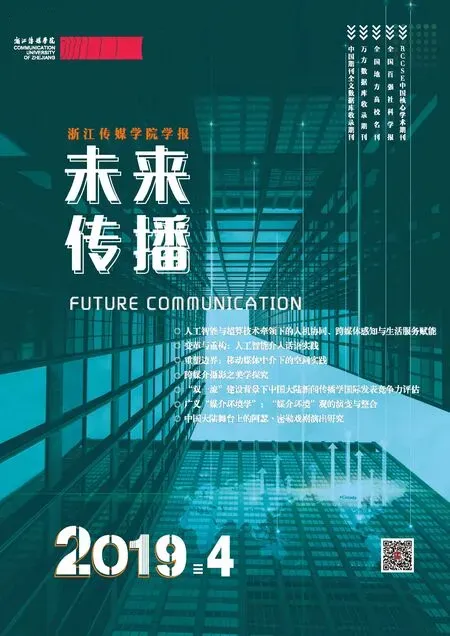跨媒介攝影之美學探究
——從伽達默爾與姚斯的理論切入
張寶儀 王汀若
2017年1月7日,《安迪·沃霍爾:接觸》在北京798木木美術館結束了為期五個月的展覽。展覽海報以“歡迎來到工廠”為題,以呼應沃霍爾(Andy Warhol)20世紀60年代在紐約的工作室——“工廠”,這里曾是藝術名流經常拜訪并舉辦前衛派對的地方。策展人普雷斯卡·安(Presca Ahn)以沃霍爾的影像、攝影、沉浸式裝置作品,把整個展廳打造成一間藝術工廠。各種媒材都有其獨特的貢獻,系統性地呈現,讓觀眾沉浸其中與內容互動。受眾進入展廳即可體會到獨特的視覺美感。從影像作品《試鏡》到寶麗來肖像攝影,再到裝置《銀云》,無一不貫穿著后現代美學對傳統美學的用力一擊,以及對各藝術門類“邊界”的不屑一顧和嗤之以鼻。沃霍爾的藝術創作理念時隔半個世紀,在跨媒介創作熱度不減的當下依舊具有啟發意義。
現今,跨界藝術的表現形式龐雜不堪,有些作品的跨界僅僅是不同藝術門類的拼貼,門類的“邊界”依舊清晰可見。本文所探討的跨媒介指利用多種媒介系統性地呈現同件作品,每種媒材的內容同時發展并相互串聯、互為一體。這與多媒體、跨平臺皆不同,后兩者多指同樣的訊息在不同平臺上的單一復制,例如漫威漫畫改編成的系列電影,彼得兔故事改編成的動畫、繪本等。20世紀末,克勞斯(Rosalind Krauss)便定義這種多媒介的混搭再創作為“后媒介狀況”[1],表征當代藝術更多采用混合媒介,擺脫了傳統藝術的媒介分類。由此可見,若討論“多媒體”“跨平臺”,我們依舊可以從創作本體出發,但探討“跨媒介”,其多種媒介雜糅的性質使得探討角度不能僅從創作者、作品本體、受眾任意一個角度出發,而應把三者看作彼此融合的一個整體來探討。在跨媒介作品中,哪個媒材起到了何種作用已經不是討論重點,所有媒介合作下如何展演了整部作品才是研究重點。
本文從爬梳攝影美學的歷史流變著手,展現當前攝影藝術所呈現的美學面貌。然后以游戲互動理論和接受美學為理論根基,通過具體跨媒介攝影案例,探究跨媒介攝影的美學成因與面貌,試圖彌補以往跨媒介攝影研究中過于關注影像本體而無切實的理論支撐,抑或僅談美學而忽略理論和實踐結合的現狀,也為日后攝影者跨媒介創作提供理論參考。
一、攝影美學流變:從傳統到跨媒介
攝影術在誕生的近半個世紀里始終扮演著輔助繪畫、記錄現實的角色,被譽為“自然的畫筆”,備受“技術性”與“藝術性”之爭,與古典主義繪畫有著相同的美學原則。19世紀90年代,大批攝影者開始為攝影的藝術性謀權,追求影像的藝術性,制造印象派美學效果,舉辦沙龍攝影展,成立連環會(1)連環會源于對英國皇家攝影學會的不滿和對“畫意攝影”的推崇,于1892年5月由艾爾弗雷德·馬斯克爾(Alfred Maskell)、艾爾弗雷德·哈斯勒·辛頓(Alfred Horsley Hinton)等人在倫敦發起。(Linked Ring)以喚起人們對“畫意攝影”的關注,將“畫意攝影”推向高峰。連環會分會分布于歐陸、北美等地,會員基數龐大。
20世紀初,美國分會會員斯蒂格利茨(Alfred Stieglitz)召集了愛德華·斯泰肯(Edward Steichen)、保羅·斯特蘭德(Paul Strand)等人成立了“攝影分離派”。起初其攝影美學與連環會保持一致,后因新興攝影的興起,斯蒂格利茨受超前“視域”驅使,“攝影分離派”的攝影觀念轉向直接攝影。重視記錄時代與生活的真實面貌,傳遞攝影藝術的寫實主義,追求攝影的純粹性,與連環會所秉承的畫意攝影美學大相徑庭而就此決裂。“攝影分離派”的改變作為導火索有力地沖擊了連環會的持續升溫,致其解體。連環會的解體使得攝影藝術擺脫了對繪畫的依賴,開始逐漸形成自己的美學特征,開啟了現代主義攝影之門。
現代主義時期涌現的攝影者多借助社會舞臺再現、記錄肉眼所見,追求純粹性與瞬間性的直接攝影美學,指意明確。如擁有“現代主義攝影之父”之稱的斯蒂格利茨的紐約影像,奧古斯特·桑德(August Sander)的20世紀德國人類影像,比爾·布蘭特(Bill Brandt)的倫敦眾生相,歐仁·阿杰(EugèneAtget)的巴黎都市舊影,羅伯特·卡帕(Robert Capa)從西班牙到中國的戰地影像,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決定性瞬間”的凝視,安塞爾·亞當斯(Ansel Adams)和愛德華·韋斯頓(Edward Weston)“F64小組”的力量與質感等等。
現代主義攝影者們所遵循的決定性瞬間、曝光精準、構圖杜絕裁切的攝影美學在20世紀50年代被一舉打破。羅伯特·弗蘭克(Robert Frank)與威廉·克萊因(William Klein)的攝影實踐開啟了后現代攝影的序幕。弗蘭克認為,決定性瞬間,除了美感和構圖外,對任何東西都沒有感受。[2]歐洲人羅伯特·弗蘭克以“異鄉人”的身份記錄美國人,透過怪誕的構圖、刻意模糊的焦點、后期裁減對美國進行異乎尋常的描寫,其畫冊《美國人》更像一本“影像詩”(2)影像詩是透過影像、聲音、文本以傳達詩意的作品,參見Konyves,Tom.Videopoetry:A Manifesto(PDF/Issuu),September 6,2011.from https://issuu.com/tomkonyves/docs/manifesto_pdf.,圖像間有嚴謹的邏輯關系,如同創作者的自白。同時代的叛逆者威廉·克萊因攝影風格隨性,通過粗大的顆粒、巨大的影調反差、反叛的構圖與模糊的焦點呈現了別具一格的紐約景象。羅伯特·弗蘭克與威廉·克萊以自身的攝影實踐批判了以往的攝影美學原則,改變了之后的攝影美學走向,后現代攝影美學揭開序幕。
后現代攝影打破了傳統美學原則,光影、構圖、色彩的精準控制都被拋之腦后,反而注重受眾的觀感和體驗。這與后現代思潮對“主體性”的重視是一脈相承的。同時超現實主義把“蒙太奇”帶入了攝影,曼·雷(Man Ray)的攝影作品即大量使用拼貼宣泄個人情感,具有濃厚的超現實主義色彩。另外,攝影作品呈現方式也開始由單一媒材演變為多媒材合作的形式呈現,文本、繪畫、裝置、影像、新媒體等媒材都成為攝影者使用的工具。克勞斯(Rosalind Krauss)定義這種多媒材的混搭再創作為“后媒介狀況”,表征當代藝術創作更多采用混合媒介,擺脫了傳統藝術媒介分類。其后又進一步分析“后媒介狀況”產生的原因是一項技術自身過時而衰退,新技術能提供技術支撐來取代傳統媒介。[3]羅伯特·弗蘭克深受美國新電影的影響,在畫冊Thank you(1996)中使用了明信片、信件、照片等素材,運用文本、影像等多種媒介,體現了跨媒介攝影的藝術表達。也不乏藝術家利用攝影的機械復制性,把攝影看作既成物進行創作,例如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與羅伯特·勞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的既成攝影實踐。
更重要的是,后現代攝影也改變了受眾的審美接受方式,觀眾從“靜觀”狀態逐漸“介入”到作品中的觀照方式。正如開篇安迪·沃霍爾的展覽中所體現的,受眾仿佛置身于藝術品中,與裝置中的云、照片中的人、影像中的建筑同處一時空,游戲互動。賦予受眾主動性,正是當前跨媒介攝影美學最突出的特征,即本文探討跨媒介攝影美學的切入點。
二、跨媒介攝影的美學探究
自蘇格拉底以降,“美”一直是西方哲人所探討的問題,直至康德,也在追尋無心之美、本體之美。伽達默爾(Gadamer)則不再追尋什么是美,轉而關注如何感受美、體驗美。這一問題的思考導向便是對互動過程的關注。伽達默爾的理論脈絡深深影響了20世紀60年代德國康斯坦茨大學的學者姚斯(Jauss)、伊瑟爾(Iser)等人,接受美學理論應運而生。
跨媒介攝影美學的研究方向已從“客體”(藝術品形式)是否引起美感體驗轉向討論受眾如何“創造”審美經驗以解讀作品。[4-5]跨媒介攝影高度的開放性、變化性、模糊性使得受眾與作品的互動成為作品完整表達的重要組成部分,受眾掌有很大的能動性。接受美學是關于受眾主動性探討的重要理論。[6]下文筆者從兩個方面展開論述,探尋理論根基與跨媒介攝影實踐的契合點,以檢視跨媒介攝影的美學面貌。
(一)藝術即游戲:跨媒介攝影的自我呈現
伽達默爾提出:“藝術即游戲,游戲即往返律動,游戲即自我呈現。”[7]在互動過程中,觀賞者(受眾)不同的視角會發散出不同的意義,展現出不同的面貌,游戲(藝術作品)被觀賞者(受眾)二次創造了。受眾這一原本的生命體驗或立足點被伽達默爾稱之為“視域”,他認為視域是將人們的主觀經驗強加于文本作為理解、獲得意義的基礎。由此,藝術作品的詮釋才能實現作者與受眾相互游戲的過程,透過游戲才能體現作品意義的完整性。
2016年“集美·阿爾勒攝影季”(3)“集美·阿爾勒攝影季”由阿爾勒國際攝影節主席與“三影堂”攝影藝術中心創辦人榮榮于2015年共同發起。是跨媒介攝影實踐的極佳案例,也較好地傳達了受眾與作品相互游戲的理念。首先,此屆策展組織模式依舊沿襲往年的“策展人邀請制”(4)“策展人邀請制”是首屆攝影季獨立策展人李振華先生發起的組織方式,策展團隊來自不同的領域,因而有助于展覽呈現不同的面貌。,有別于兩岸任何大型攝影展的“主策展人制”。30幾位策展人皆來自不同領域,如電影、新媒體、音樂、美術、攝影等,每位策展人依自身不同的學術背景制定展覽計劃與方式,使展覽形式和風格非常多元化。其次,此次攝影季“無界影像”單元凸顯的“無界”即跨媒介的命題,7位策展人從不同層面命題作文,展開跨媒介敘事,最終又回歸影像本身。
由青年攝影史學者、獨立策展人何伊寧在“無界”單元策展的“虛構敘事的轉向”(圖一)是她對以往藝術家的照片進行虛構敘事的一次嘗試,作品借助照片、裝置、文本、既成物、檔案等媒材實現了跨媒介特性。在展覽現場,一條印刷有影像的環形半透明紗布裝置懸掛正中,受眾可置身其中觀看與之互動,體會影像中的人物、建筑等與創作者間錯綜復雜的關系。在西班牙攝影師朱利奧·加萊奧特(Julio Galeote)的《熱帶裝飾》作品前,策展人則借用檔案的形式生動地還原了加萊奧特所收集的邁阿密歷史圖像文件。
圍繞此次展覽的構思與形式,筆者對策展人何伊寧進行了訪談,試圖挖掘她對當前跨媒介攝影現狀的思考,她表示:“此次展覽是通過考察8位青年攝影師/團體在近期攝影創作中運用虛構敘事所探討的豐富主題,思考照片被并置在真實和虛構的文化與歷史維度中的可能性,并探討攝影在虛構敘事空間里的功能。這些藝術家在不同文本間靈活轉換,從側面體現了他們對圖像的認知和理解,同時也表現出他們試圖打破限制攝影媒介性的障礙,更加自由地運用圖像進行創作的嘗試。我認為這一趨勢是釋放攝影能量的集中體現,順應了后媒介狀況的發展。”
同時,筆者也訪問了一位年齡26歲,碩士畢業于英國某藝術類大學,但無攝影相關背景,現在廈門從事新媒體行業的觀展者范小姐。問及她對“無界”單元不同媒介使用的直觀感受時,她的回答與影像從業者頗有偏差。她認為:“跨媒介影像的確更能吸引觀者,但也容易喧賓奪主,讓受眾只關注裝置的形式而忽略影像內容。創作者應給予受眾更多探索、互動的權利,讓受眾有興趣挖掘影像的意義,而非嘩眾取寵,用其他媒介吸引受眾注意力,反而削減了影像本身的力量。”
對于何伊寧策展的“虛構敘事的轉向”,范小姐則表示僅從影像上很難理解其中的意義。轉而談起“無界”單元中王歡策展的“被介入的對象”,藝術家蘇育賢的彩色有聲錄像作品《花山墻》(圖二),她認為,這個結合了多媒體、定格動畫、攝影元素的作品,涵蓋了民俗手藝扎紙,又配有滑稽的粵語旁白,作品顯得怪誕卻直入心底,讓她想到了福建當地的閩南語、歌仔戲和提線木偶。她認為這件作品更能激起她的思考與共鳴。
可見,因受眾背景不同,欲達到互動效果絕非易事。即使被業界認可的創作,依舊可能是披著“皇帝的新衣”,難以達到預期的互動效果。正如伽達默爾所述,一方面受眾需按照規則進行游戲,同時受眾不同的“視域”會產生不同的互動效果。只有受眾在互動過程中不斷地與作品對話,才可能接近創作者的視域。若能達到“視域融合”[7],受眾即可理解創作者的意圖,生成審美愉悅。當然,受眾也可由自身的美感體驗與喜好來閱讀作品。[8]這也正提醒策展人/創作者在構思與創作時,遵從自己內心的同時,也應站在受眾的角度考慮問題。
(二)審美重心轉移:從審美再現到審美互動
伽達默爾已經把審美愉悅放入了互動過程中,給予受眾主動性。姚斯(Jauss)師承伽達默爾,進一步延伸伽達默爾“視域”的理論脈絡,完善了受眾的主控性及生命經驗對欣賞藝術的作用,發展出接受美學理論。它強調美感體驗從審美再現論到審美互動論,美不是藝術作品靜態地再現,而是在受眾和作品的互動中體現。姚斯在《審美經驗與文學解釋學》(AestheticExperienceandLiteraryHermeneutics)中提出了審美互動三段論:“創造”“感知”與“凈化”,[9]以此劃分審美經驗的生產端、接收端與交流功能。下文將借姚斯的審美互動三段論,結合筆者創作于2014年的跨媒介攝影作品《十日談》(5)《十日談》曾展覽于2014 Goldsmiths,University of London Degree show、2015中國青年影像大展、2015麗水國際攝影展、2016臺北國際攝影展,2014年被英國約克現代藝術美術館收藏。展開具體論述。
《十日談》(圖三)是由現代主義肖像攝影、文本與聲音組成的跨媒介攝影作品。此專題藝術表現形式上的靈感來自交響樂,由幾個“樂章”獨立而成,章與章之間又互有關聯性。創作者基于人物肖像、空間與故事在不同國家、城市進行創作。被攝者為不同國家、不同宗教信仰與職業階層的普通人。首先,通過交換故事的方式進行訪談,被攝者先分享一個故事,這個故事可關乎生活、工作、政治、信仰或其他,拍攝者響應一個同主題的故事并為其拍攝一張肖像照。然后,依故事、人物、城市特點拍攝一張具有某符號意涵的空間。最后,寫一首短詩。人物肖像、空間與詩并置拼貼組成一張完整的影像。薄伽丘在《十日談》中,用現實主義筆法深描了10人10天內講述的百個故事。本人則用紀實手法,通過影像和短詩講了10個人的故事。拍攝結束后,本人把10張影像分別發給10位媒體工作者,讓其通過錄音設備錄下對影像的感受。背景聲則為10個不同空間的環境音,包括海浪聲、車水馬龍聲、清真寺眾人禱告呢喃聲、馬蹄聲等。
在展覽現場,本人掛置影像、耳機與錄音設備。觀者可以通過影像、文字、音頻選擇互動、評論或批判。此作既是創作者與被攝者之間的互動、創作者與空間的互動,也是受眾與作品之間的互動,從而實現三者聯動,較好地完成了審美互動的過程。
1.創造:“留白”與“反觀”
姚斯認為,受眾與創作者有同等的地位,可經由自己的解讀詮釋或創造。在《十日談》中創作者即把作品的詮釋權主動交給了受眾。作品中存在諸多不確定性,具有開放性和反思性,由受眾參與的語音創作是完整作品很重要的一部分。一方面,可以激發受眾走到白墻前,靜靜觀賞,而非遠觀;另一方面,也刺激受眾參與其中,可根據自身觀感、聽感填補創作者的“留白”,進行二次創作,為作品帶來了更廣闊的美學空間。
伊瑟爾(Wolfgang Iser)提出的“隱藏讀者理論”(The Implied Reader Theory)與姚斯有異曲同工之妙。伊瑟爾認為,文本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未書寫的部分”,受眾要從“已書寫的部分”讀出玄機,體會到“未書寫的部分”,這部分才是美學展現最豐富的部分。[10]如同中國古典詩詞歌賦或水墨畫,“留白”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其他藝術創作亦然。
此外,姚斯認為,受眾二次創作過程也是“反觀”的過程。也許某幅作品中的人、地、詩恰好勾起了受眾某段回憶、聯想、悸動。當受眾沉浸于愉悅感受后,若能進一步用“旁觀者”身份理解感動從何而來,就能進一步認知自我,姚斯把這種“反觀”稱為“二級閱讀”的表現方式。比如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在看到照片中俄羅斯婦女系的絲巾時聯想到了自己過世的母親而潸然淚下,他把影像中帶來別樣感受的細節稱為“刺點”。[11]受眾在“反觀”時,同樣是個人獨特的“視域”產生“刺點”的情感表征。
2.感知
“感知”即受眾接收客體(作品)的方式,以其不同的“視域”詮釋作品意涵。從接受美學而言,“感知”是最能體現受眾能動性的方面。受眾可通過“感知”解讀文本,其地位可以凌駕于作者之上。從受眾的詮釋中,創作者可窺視到姚斯所言“感知”的不同途徑,如聯想、同情、反諷等。
以《十日談》之二“失憶的犀牛·尼斯”(圖四)為例,此影像拍攝于法國南部海濱小城尼斯,被攝者是一位無外語溝通能力的中國東北大叔,早年離異,跟隨兒女定居此地。他每日在海邊釣魚,沒有朋友,遇到漁友也只能通過身體語言溝通,生活異常苦悶。當遇到同樣來自中國的拍攝者后,他打開了話匣子,毫無顧忌地講起了他日常生活中唯一的樂子——通過金錢交易的性生活。看似溫飽無憂、生活優越的移民,對他而言卻缺少真正的愛和自由。于是本人在空間與短詩中通過大量比喻試圖表達被攝者的苦悶和處境。但受眾的詮釋卻迥然不同:被攝者終日暴曬的皮膚質感與犀牛皮的對照、襯衣上玫瑰花的異域感、熱帶飛禽,都成了受眾獨特而有趣的詮釋因子,表征受眾不同“視域”帶來的不同“感知”。
3.凈化
“凈化”最初來自亞里士多德《詩學》中對古希臘悲劇審美功能的闡述。姚斯認為,古典主義肯定審美的凈化作用,現代藝術則開始質疑它。尤其阿多諾為了避免藝術成為現代工業或意識形態所操控的工具,喪失其獨立性和對社會現實的批判性,認為藝術只有“否定”才能破除文化工業對它的控制。姚斯則認為阿多諾在處理藝術與社會的辯證關系時,簡單地將其視為“否定”與“肯定”的兩極,而忽視了兩者之間的轉化。很多最初具有“否定性”(批判作用)的作品會隨著時間的流逝(受眾“視域”的變化)而逐漸喪失它的“先鋒作用”,反之亦然。于是姚斯跳出“肯定”與“否定”的兩極,認為審美經驗有更廣闊的交流與對話空間,“凈化”即審美經驗的交流功能。
《十日談》之七“烏托邦·卡帕多西亞”(圖五)拍攝的是一位加拿大女士為了遠離城市喧囂而前往土耳其卡帕多西亞的一家馬場做義工,這里沒有喧囂與干擾,恰似一方安靜平和的烏托邦世界,給疲乏的靈魂棲息之地。毫無疑問,這位被攝者的故事與拍攝者(“我”)有著“欽慕式的認同”之互動模式,而這幅影像作品與受眾之間也有以“認同”為中介的交流與對話,即“凈化”。“認同”是姚斯接受美學里的關鍵概念,他闡述了五種審美經驗交流中的認同模式:聯想式認同、欽慕式認同、同情式認同、凈化式認同、反諷式認同,“‘凈化’包含著認同的要求和行為模式,它是一個交流框架”[12]。跨媒介攝影尤其強調這個交流框架,更需要受眾動態地介入其中,“也能讓觀察者在獨自的心靈解放中獲得純粹個人的滿足”[12]。
綜上所述,對跨媒介攝影而言,受眾的參與無可回避,且是十分重要的一環。以往對攝影美學的論述,多從攝影本體(作品)出發,即使羅蘭·巴特從現象學、生命史書寫攝影,也不乏攝影本體的討論。然受眾主體性才是跨媒介攝影獨特的美學新意。
三、余 論
羅蘭·巴特提出“作者已死”,德希達(Jacquea Derrida)提出“寫作對作者而言就是自身的滅亡”,他們已經把關注重心全部放在了讀者對作品意義的詮釋上,而忽視了文本本身。本文則通過伽達默爾的“游戲互動理論”和姚斯的“接受美學理論”闡明跨媒介攝影的美學特征。然僅透過受眾與作品的互動關系就能判斷作品的“好”“壞”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常言道:不會走怎會跑?藝術創作亦然。追求個人風格和創新固然重要,但傳統攝影美學中的基本功也不可忽略,對影像的把控與敘事能力仍是跨媒介攝影創作的基礎。對影像本體的分析也是詮釋作品之外的基礎,基于本體研究再上升到作品之外的詮釋,才可能會實現受眾與作品/作者間的“視域融合”。
另一方面,作品若曲高和寡也難與受眾互動起來。因此,談及跨媒介攝影時,日常生活美學也是不可忽略的。新寫實主義者強調,藝術創意與制作過程中,“現實”之美須再現于作品中,成為藝術作品最重要的實質內涵之一。[13]作品懸在空中難以被欣賞也非創作者意愿。簡·福西(Jane Forsey)指出,新寫實主義導引出“日常生活美學”的藝術創作觀,凸顯超凡的美感體驗是來自平凡的美感體驗。[14]因此,即使觀念主義攝影創作,也要適應現實,傳遞出創作者的意圖,這樣受眾才能介入到作品中。總之,創作一個完整的、有意義的跨媒介攝影作品絕非易事,需要創作者全面衡量,否則容易“撿了芝麻丟了西瓜”,只為迎合一方而失整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