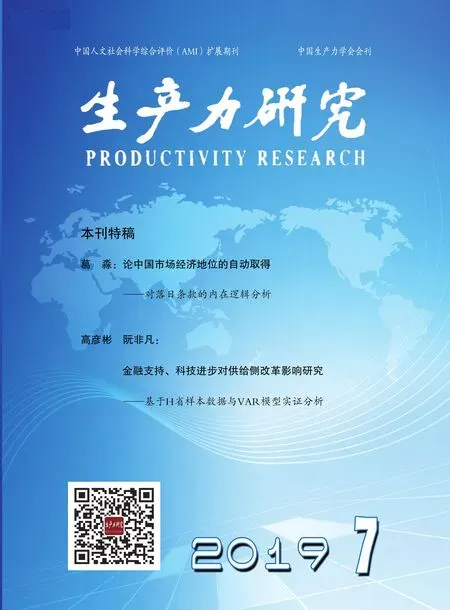加班態度對勞動者過勞程度的影響研究
張智勇,蔣玲
(1.武漢科技大學 文法與經濟學院,湖北 武漢 430065;2.武漢科技大學 勞動經濟研究所,湖北 武漢 430065)
一、引言
在當前職場,超時勞動或者加班行為正在呈現出普遍化和常態化的傾向。有調查顯示,我國九成行業每周工作時間超過40小時,過半數行業每周要加班4小時以上(賴德勝等,2014)[1];“996”現象更是引發了社會各界的熱議。這些似乎表明今天的中國正在復制一個類似日本的“過勞時代”(森岡孝二,2018)[2]。對于加班行為對勞動者本人效用和健康帶來的影響,有研究表明:加班,尤其是時間安排不規律的加班會加劇身體疲勞的蓄積(張智勇,2018)[3],引發職業倦怠、工作效率下降等后果,甚至“過勞死”(楊河清,2014)[4]。但是,也有觀點認為,能夠“996”“是一種福氣”,對于“熱愛的工作”,別說8個小時,就是“12個小時也不算長”[5]。本文認為,如果不考慮勞資立場的因素影響,兩種觀點相左的焦點似乎在于:主動還是被動、自愿還是被迫,即加班的主觀態度決定了加班的行為(時間長短)以及后果(倦怠還是幸福)。轉化為經濟學的語言,即加班的意愿(勞動供給的偏好)決定了加班的行為(勞動供給時間的增加)以及加班的結果(勞動者勞動供給的效用水平)。顯然,對于加班這種超量性質的勞動力供給行為,要作為一個完整的鏈條加以把握的話,必須考慮意愿和能力的統一。基于此,本文擬從心理學和經濟學的雙重視角,對加班的效應進行分析。
二、加班態度影響過勞程度的研究假設
(一)計劃行為理論視角下態度對行為的影響
過度勞動是指勞動者在工作過程中存在超出社會平均勞動時間和勞動強度的行為,并因此導致疲勞蓄積的工作狀態(孟續鐸,2014)[6]。心理學中的計劃行為理論認為,行動的發生是由人們的行為意向決定的。行為意向是指個人想采取行為的傾向與程度,對于行為具有較強的的預測力和解釋力。態度是影響行為意向的因素之一,是個人對特定行為所持有的正面或負面評價。個人的態度越積極,行為意向越強。根據計劃行為理論,本研究推測當勞動者對加班持不同態度時,其超時勞動供給是不同的,即相比非自愿加班的勞動者,自愿加班的勞動者加班情況可能更嚴重。由此,我們提出假設:
H1:不同加班態度的勞動者加班時長存在顯著差異。
(二)基于效用最大化的過度勞動效應
加班是勞動力市場上,基于勞動者自愿基礎上的一種勞動力供給行為,這里沒有任何超經濟的強制的力量存在,作為一種超時行為,加班不完全是被動的,還存在自愿加班現象[7]。但是因為勞動者個體體質的差異性問題,即使沒有加班,甚至在勞動時間低于合法的制度勞動時間的情況下,也有人會感到“力不從心”、疲憊不堪。同樣的,在相同的加班時間里,身體素質差的人可能很容易疲勞,而身體健康者則沒有負面的反應。如果站在適度勞動的層面看,目前的研究大多對過度勞動持否定的態度,認為過度勞動的經濟社會效應總體是負的。但是從理論上看加班則不然:作為勞動者自愿的勞動供給行為,加班的發生,一定會帶來效用的增加,否則加班行為就不可能產生。如前所述,因為個體差異,加班即長時間勞動不一定引發疲勞。從理論上看,加班本質上是一種勞動力超時供給行為,確定其勞動供給量的,是在該供應量上所確定的抽象意義上的效用,而非僅僅來自身體和心理上的疲勞蓄積。勞動者會根據自身情況,選擇對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勞動供給時間。因此,本研究推測不同加班態度的勞動者是基于效用最大化的原則決策勞動時間的供給,即相比非自愿加班的勞動者,自愿加班的勞動者更容易“樂在其中”,因而其過勞程度更低。由此,我們提出假設:
H2:不同加班態度的勞動者過勞程度存在顯著差異。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研究所用數據來源于2016年6月至2017年9月武漢科技大學勞動經濟研究所進行的職場行為與疲勞狀況調查問卷,采用結構式問卷設計,問卷分為四個部分:一是工作和職業,包括被訪者的單位城市、行業、單位性質、職業、職位層級、加班時間等,其中部分題項作為勞動者工作負擔狀況的評分依據;二是職場行為與態度,了解被訪者的職場客觀情況及工作主觀態度;三是工作疲勞蓄積度,了解被訪者的職場疲勞蓄積狀況,部分指標作為勞動者職場疲勞狀況的評分依據;四是個人基本情況,包括被訪者的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等。問卷采用抽樣調查方式,調查地區涉及東部沿海、中部內陸、西部邊遠共27個省份,調查對象為勞動力市場上60歲以下就業群體。本次調查發放問卷1 650份,收回1 617份,回收率98%,其中有效問卷1376份,有效率85.1%。
(二)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本文研究加班態度是否會影響勞動者的加班時間,進而影響勞動者的過勞程度。因此在研究加班態度對加班時間的影響時,選取周加班時間作為被解釋變量;在研究加班態度對勞動者的過勞程度的影響時,選取勞動者的過勞分值作為被解釋變量。過勞分值的測量參考王丹和楊河清(2010)[8]的過度勞動評價體系,根據問卷中的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相應指標測得勞動者的工作負擔狀況評分和疲勞自覺癥狀量表評分,并根據二者綜合得出勞動者的過勞分值。
2.解釋變量。本文選取加班態度為解釋變量,將勞動者對工作需要加班的態度分為非自愿、混合、自愿。非自愿即當工作需要加班時,勞動者愿意加班的意向為非常不愿意,自愿即其加班意向為非常愿意,混合即既存在自愿成分也存在非自愿成分。變量賦值分別為“非自愿=1,混合=2,自愿=3”。在研究加班態度對加班時間的影響時,加班態度是作為周加班時間的解釋變量;在研究加班態度對勞動者的過勞程度的影響時,考慮到加班態度與加班時間的交互作用,因而將周加班時間分段,并作為新的解釋變量,變量賦值為“0~5小時=1,5~10小時=2,10~15小時=3,15小時以上=4”。
3.變量描述統計。從表1中可以看出,大多數勞動者對加班的態度是混合的,即在實際工作中,自愿加班與非自愿加班的心態并存。從每周的加班時長來看,54.6%的勞動者每周加班在5小時以內,35.5%的勞動者每周加班在5~10小時之間。從過勞分值來看,30.3%的勞動者過勞分值為3。

表1 變量描述統計
(三)模型構建
本文討論加班態度對加班時間的影響,以及加班態度和加班時間各自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對過勞程度的影響。因此采用SPSS22.0構建以下方差分析模型:

其中,αi、βj分別表示加班態度i和周加班時長j的主效應,γij為兩者之間的交互作用。
四、研究結果
(一)加班態度對加班時間的影響

表2 誤差方差的齊性Levene's檢驗
從表2可以看出,方差齊性檢驗的顯著性p>0.05,總體方差齊同。表3為主體間效應檢驗結果,修正模型的顯著性p>0.05,說明加班態度對周加班時間影響的模型無統計學意義,加班態度的顯著性p>0.05,即不同加班態度的勞動者周加班時間無顯著差異。這一結果說明,自愿加班的勞動者其加班情況并沒有顯著高于其他勞動者,對待加班的不同態度并沒有顯著影響加班行為。

表3 主體間效應檢驗
(二)加班態度、加班時間對過勞程度的影響

表6 加班態度變量的事后比較
1.模型檢驗結果。從表4結果來看,修正模型的顯著性p<0.001,因此模型有統計學意義。加班態度與周加班時長的顯著性p<0.001,兩者均具有統計學意義,但是二者的交互作用的顯著性p>0.05,無統計學意義,因此將其從模型中剔除。表5為去除交互作用項后方差分析的結果,模型及兩個自變量仍然具有統計學意義。
2.加班態度與周加班時長的交互作用。假設加班時長受加班態度的影響,導致勞動者的過勞程度不同,因此在該模型中分析加班態度與周加班時長的交互作用。從表4結果來看,加班態度與周加班時長無交互作用,說明不同加班態度的勞動者,其過勞分值的差異不受周加班時長的影響;不同周加班時長的勞動者,其過勞分值的差異也不受加班態度的影響,即勞動者因加班而導致的過勞并沒有因為其態度是自愿或非自愿加班而存在顯著差異,因而無論是自愿加班的勞動者還是非自愿加班的勞動者都必須重視過度勞動問題。
3.不同加班態度的過勞分值差異。從表6的事后比較結果來看,自愿加班的勞動者過勞分值最大,但是自愿加班的勞動者和非自愿加班的勞動者過勞分值無顯著差異,即自愿加班的勞動者往往更容易忽視自身健康,沒有因為工作“樂在其中”而導致過勞分值顯著低于非自愿加班的勞動者。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基于加班盛行、“過勞死”事件頻發的社會現象,從理論角度分析加班態度對勞動者過勞程度的影響,提出假設并構建方差分析模型,通過分析發現,不同加班態度的勞動者加班時長無顯著差異,即加班態度并沒有顯著影響加班行為;不同加班態度的勞動者過勞分值無顯著差異,無論是自愿還是非自愿加班,勞動者的過勞分值都隨著加班時間的增加而增大,即超時的勞動供給導致的疲勞蓄積并沒有因為主觀態度的不同呈現顯著差異。因而,在社會競爭加劇,“過勞死”日益頻發的時代背景下,我們不僅僅要關注非自愿加班導致的過度勞動問題,勞動者的主動過勞問題也亟需關注。根據上文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建議:
1.勞動者應樹立健康意識,適度勞動,減少主動過勞。自愿加班的勞動者往往更容易忽視自身健康,勞動者應該意識到身體是革命的本錢,注意合理控制工作時間,養成良好的作息習慣,避免因自身對健康的忽視、對工作目標的過度追求損害身心健康。
2.企業應關注員工健康,避免員工過勞。員工過度勞動不利于生產效率的提高,企業合理安排工作量,拒絕“惡意”加班,能夠體現企業的責任意識,樹立企業良好形象;另外,更多的閑暇有利于員工恢復精力,提高工作效率。員工還可以利用閑暇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提高工作技能,促進人力資源的長遠發展。
3.政府應加強勞動法律的監管。對勞動者主動過勞的控制,主要依靠勞動者自身提高健康意識,加強自我約束;而對于勞動者非自愿過勞的控制,則需要法律的力量進行約束。企業較低的違法成本,以及勞動者為保住工作而不得不接受加班的現實,助長了加班風氣的盛行,嚴重損害了勞動者的身心健康。政府應該加強制度的執行,加大勞動法律知識的普及,提高企業的違法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