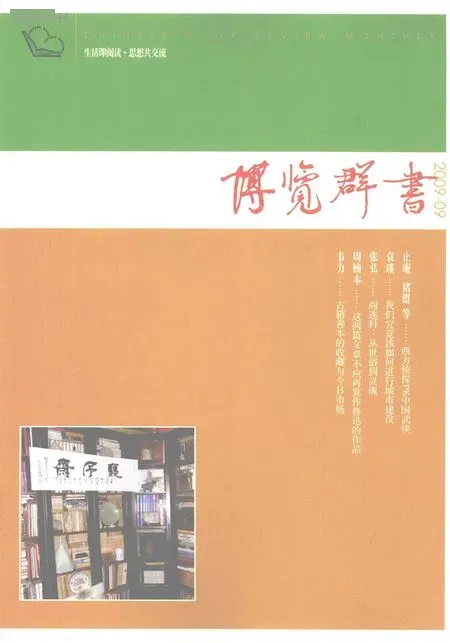序楊莉《民國時期天津文廟研究》

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在其《文明沖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書中提出了著名的“文明沖突論”;稍后,他又在《我們是誰?》中強調了美國的基督教文化認同。這些著作的獨特視角被“9·11事件”放大,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教文明的沖突預言不幸而言中,而其關于中國為“儒教文明”的判斷定性也在大洋此岸引起震動和思考。今天,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文化自信”的口號漸漸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的時候,從文化和文明的角度對儒教與中國社會、歷史乃至政治的關系進行梳理和研究就變得特別重要了。
如果說秦始皇與法家李斯攜手確立了中國歷史的政治結構,那么漢武帝則與儒生董仲舒攜手確立了其文化結構。從“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方略下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到“東漢功臣多近儒”,再到昔日的秦人、周人和楚人被統一稱呼為漢人的時候,儒教文明應該說就初步成型了。后來雖有佛教道教對儒教形成沖擊,但宋孝宗“以佛修心,以道養身,以儒治世”的《三教論》,基本框定了各教在中國社會中的功能和地位,“治世”的儒教文化權重顯然遠非“養身”的道教與“修心”的佛教可堪比擬。宗祠、書院和孔廟正是儒教與社會互動,實現或承擔其功能的平臺或組織系統。
關于孔廟的研究已有很多的積累,但以文獻學、歷史學為主,甚至建筑學等方面的成果也超過宗教學。十年前從臺灣黃進興教授處獲贈《優入圣域》及《圣賢與圣徒》。因為二書暗含儒家思想乃宗教之系統的預設,當時聊的時間雖短,卻十分投機愉快,有他鄉遇故知的感覺。黃教授從國家宗教和公共宗教角度,談論了儒教的一些特質,將孔廟研究推進到宗教學的論域或層次。我自從提出“儒教之公民宗教說”后,一直希望能帶學生做些個案研究,將這一直覺判斷加以驗證、深化或證偽。楊莉曾說她想做孔廟的神圣空間問題,后來各種因緣際會走到了宗教社會學的進路。現在,畢業多年之后她把這樣一部書稿發給我,要我寫序,應該也算是一種補償吧?
匆匆瀏覽一過,對關于民初天津文廟三次修繕的章節印象深刻,不妨就此發些議論。這是她的觀察和分析:
天津文廟在民國早期大修背后的意義實際上是士紳階層借助文廟這一文化象征,在其逐漸喪失文化權威的社會中重新構筑一個文化空間,并依此獲得新的文化權利。然而,這種情況到民國后期在政府主導修繕時發生了變化。在政府將文廟的象征意義納入自身的意識形態體系之中后,逐漸消解了其原本道統的象征意義。因此,即便士紳再參與到文廟的修繕過程中,也難以達到民國初期時的效果。所以,民國時期天津文廟的修繕不僅是士紳文化權利的體現,同時還可以看出在文廟修繕過程中社會和政府在承續傳統文化符號過程中的博弈。
十分有趣!
我們知道,全國兩千余座孔廟除開曲阜、衢州一北一南兩座家廟之外,主要都是廟學合一的“學廟”或“廟學”。學廟或廟學就是以辦學為宗旨,學習儒家經典的學校與祭祀孔子的廟宇結合在一起的官辦機構。從圣賢崇拜的角度看,“廟”無疑意味著宗教;但從“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封號頒自朝廷而言,“廟”同時又意味著國家權力的出場,意味著國對教的掌控。公元前195年漢高祖親臨曲阜孔廟祭孔后,這一家廟就此開始過渡成為了國廟。而“學”,就其以儒家經典為內容來說其實就是作為“布衣”的孔子及其思想,但又因其設于“廟堂”而有著官學的地位或身份。
民間性質的書院,也是祠學合一。“學”幾乎一樣;“祠”與“廟”的區別在于,祠作為一種祭祀方式,“品物少,多文辭”,其祭祀對象一般為儒門圣人或地方鄉賢。簡單說,二者結構上高度重合,只是規模層次存在官方民間之區別,民間的“祠”不能跟官方“凡神不為廟”“室有東西廂曰廟”的“廟”相提并論。
這種民間書院在宋尤其明時期高度發展,代表著社會組織的活力與活躍。到明張居正嚴禁私學,再到清雍正十一年下旨各州府官辦書院,書院又開始在政府的組織序列里重新生長,廟學合一也漸漸成為書院的標準配置。成功失敗?是喜是悲?至少長沙的岳麓書院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為近代中國培養出曾國藩、左宗棠、魏源等一大批創造歷史的風云人物。
我認為,孔廟和書院的廟學合一仿佛一個隱喻,象征著國家和社會的結合、政統與道統的聯系。所以,雖然從具體的過程看,政與教、廟與學存在摩擦,政府官員與地方士紳“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圍繞文化象征或文化權力的博弈爭奪無有盡時令人生厭,但各種怨憎會的后面,最終仍是斗爭后的妥協、矛盾中的平衡。而廟學合一的維持,與“霸王道雜之”的“漢家制度”遙遙相契。儒教文明云乎者,其此之謂也歟?
指出這一點,首先是希望提醒讀者從這樣一個大的背景和關系結構中去理解作者向我們揭示的那段歷史事實。其次,則是希望給作者鼓鼓勁,楊莉觀察深刻,但調子有點偏暗。文化權力爭奪或博弈是事實的一個方面,但并非全部。即使均衡點有所偏移,也應歷史地去看,其意義價值仍然值得肯定。論者注意到,天津衛學建立之前,民間“少淳樸,官不讀書,皆武流”。但到明正統年間,已是“循循雅飭,進止有序”了。這種教化之功微小卻不可小覷,積石成山積水成淵,遲早會有興風雨而生蛟龍的一天。民國時期政府疲弱,社會急劇動蕩,且存續時間不長。那些官員,那些士紳,卻是那么的認真投入,某種程度上都可說是叫人尊敬的文化情懷黨!
身為儒生,雖然我個人發心在建私人書院,但卻也不得不承認,儒學真正的復興,首先還是要寄望于孔廟的激活,寄望于廟學合一的制度及其所隱喻的道統與政統的結合、國家與社會的互動。目前孔廟文物化、博物館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民間士紳這一源頭活水沒有被引入,之所以沒有被引入的原因則在于國家和社會間互動不夠良好。這種情況下,有心人士不妨學學書中嚴修及其崇化學會的“新廟學”經驗,以“與祭灑掃社”這樣的義工組織身份低調進入,或許可以就此拉開互信的帷幕。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何況有關方面早有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平臺建設的指示精神打開了相關政策空間。
《闕里志》有云:“孔子之教,非帝王之政不能及遠;帝王之政,非孔子之教不能善俗。”政以施化,教以善俗,政教相維,天下以治,文明以興。儒、釋、道的整合已成過往,基督教、伊斯蘭教的對話正在路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需要文化的支撐,文化的支撐需要孔廟的激活——有志者,事竟成。
是為序。
(作者簡介:陳明,原道書院山長,現任湘潭大學教授,曾任職于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員,首都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研究領域為中國思想史、中國儒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