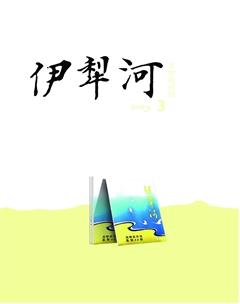與節氣有關或無關
汪劍釗
節氣里貫穿著每個人的氣節,
氣節是節氣堅韌的經脈。
——自題
立 春
立春與春節猝然相撞,
如同白毛的喜兒遇見久別的大春哥,
一腔相思的愁苦化成了雪水
流淌,灌溉郊外麥地的拔節聲。
季節的重疊并不常見,
倒也并不是象征的骰子偶然一擲,
青春的高冷與中年的和暖撬動生活的雙 輪車。
越過了小寒與大寒,
二月的身體裝滿大小不一的冰凌,
等待黃昏的熙風,等待破曉的霞光,
等待奇跡在水洼中迸發。
林蔭道邊,兩塊石巖的縫隙,
稀疏的柳枝躲開了影子的脅迫,
正在咿呀低語……
花壇上,一只貍斑貓
敏捷地追逐驚惶的灰喜鵲。
連翹的籬墻正在醞釀樸素的芬芳,
為花苞敷設燦爛的前程。
世界原本是一幅留白的風景:
數叢偶然的綠意正從大地深處滲出,
哦,一種輪回的必然!
冬 至
是的,已經是冬至,
我獨自把每一個字與詞挨個掂量,
趕在群體性雪花飄落之前。
感情降到零度,
去掉負數,也去掉正數,
一切重新開始,
在鏤空的樹洞觸摸成長的意義。
我,站在我的身外,
瞇眼端詳無謂忙碌的一尊軀殼。
從今天開始,嘗試重新做一個嬰兒,
與環形的符號成為親密的鄰居。
手握一枝烏鴉遺棄的枯枝,
享受自由涂鴉的快感,接受聲音與象形的 愛撫……
哦!感謝母語,這皺紋密布的漢字,
美是藝術的初戀——驀然回首:
詩,再一次逼近生活的內核。
冬至日的夜晚,在入九的寒風里哆嗦,
有點沮喪,但我不絕望。
除 夕
所謂除夕,就是鉆進時間的序列,
不露聲色地刪掉一個夜晚,
一個實際平常、但被世人特殊命名的夜晚。
記憶是一張孔眼密布的羅網,
撈住的總是大于網格的飛禽和游魚,
至于大朵浮夸的云彩,
以及細節的螻蟻,總被有意無意地漏過。
留不下的,又奈之如何?昨天的影子跨不進
明天的門檻,遺下的豈只是悔憾?
除去的,不只烏黑如礦巖的長夜,
還有耀眼的日光。
敲響錚亮的銅鑼,擂起緊繃的大鼓,
點燃二踢腳的炮仗,以驅逐疫癘之鬼為名,
抹除一年的瑣碎與364天的煩惱,
當然,也必須把辛苦與榮譽視若草芥,
一股腦兒扔棄,猶如7÷3的余數,
多么糾結,多么輕松,就此兩訖。
點燈,讓蝙蝠飛進屋子……
美麗的隱喻雖然外表矜持,
卻是一個善良、樸實、勤勞的女人,
熱衷于在詩歌與現實之間搭橋或者造船,
于是,入夜遂成為一個節日,
召喚人們集聚在一起,如同一排饕餮的動詞
享用豐盛的年夜飯,
那一盤又一盤美味的名詞,
最后,僅剩一堆殘缺不全的標點……
零點的鐘聲響起,虛無再一次孕生了偉大 的存在。
大 寒
戊戌年的冬天是一個早產兒,
一路翻滾著向前,終于來到臨界點;
而關于諾亞方舟的圖紙正在作初步的勾勒,
遇春學長美好的囑托尚未完成。
黃土店是北京郊區,曾有知青在此偷雞 摸狗。
寒氣逼人。道旁的楊樹早已脫去了枯葉,
便于挺拔的身軀集聚暖意于核心,
并且作為風景,呈現非黑即白的荒涼。
售賣“驢打滾”的大叔在高聲吆喝,
與其說在招徠顧客,不如說是為了借此 驅寒,
喪家的野狗發出低低的嗚咽,
仿佛要與朔風爭奪埋伏在耳朵里的聽覺。
地鐵口,人群被倒出,猶如廢棄的煤渣,
驀然,一襲紅色的圍巾飄起,
仿佛黑色爐子上一股竄向天空的火焰,
燦爛而詭異,但旋即熄滅……
雪片不曾落下,冰層平躺在小清河的水面,
隱約閃爍一長串星星的憂傷。
所謂大寒,所謂立春,它們看似遙遠的距離
不過是中間橫隔著詞語的毛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