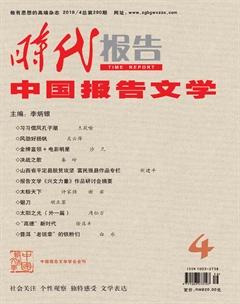太陽之光(外一篇)
周松萬
義務和良心——這些道德情操是人區別于動物的最重要之點。
—— 蘇霍姆林斯基
引 子
2月1日,離2019年春節近在眼前了,位于湖南省南部的邊陲小縣——臨武縣,低溫雨雪冰凍天氣持續,但絲毫不影響人們對新年和春天的向往,從鄉村到城市,村里村外,大街小巷,迎接春節的氣氛漸濃,人們開始買年貨,抖糍粑,殺豬,做臘肉,掛紅燈籠。
“沒有風雨躲得過/沒有坎坷不必走/所以安心的牽你的手/不去想該不該回頭……”瓷青的天空露出淡粉,臨武縣福溪廉住房小區的一戶人家,樂曲響起,唱歌的人伴著音樂節拍,唱起了經典老歌《牽手》,嗓音粗糙,跑調,但聽歌的人,卻側耳傾聽,嘴角上揚,淺笑嫣然。
唱歌的人,不是歌手,是一位平凡的中年男人,他叫劉圣平,今年47歲,膚色黧黑,頭發稀疏,濃眉小眼,中等個頭,乍一看,他黃銅色的臉上皮吊吊的,額上幾道抬頭紋有棱有角,黑眼圈很重。
聽歌的人,不是歌迷,是一名普通的中年婦女,她叫林國月,今年51歲,蓄著板寸頭,臉色蠟黃,眼窩微陷,顴骨凸出。看上去,很瘦,瘦得臉上似乎只有一層黃皮,遮住輪廓畢現的骨頭。
劉圣平與林國月是一對恩愛夫妻。
此時,劉圣平如往常一樣早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照料妻子,他扶起躺臥在床的妻子,把枕頭墊高,讓她就著枕頭靠住床頭,為她洗漱,為她按摩,為她唱歌……
整個房間彌漫著溫馨的氣息。歌聲飛出窗外,飛入小區住戶每個人的心里,觸動著他們最柔軟的神經。
此刻,他就是她最帥的新郎、不老的歌神,她就是他最美的新娘、忠實的歌迷。
一家人的春節:歲月靜好,“你在,家就在”
大年初一,天空放晴,太陽泛起笑臉,驅趕著冰凍雨雪,之前呼嘯刺骨的北風,天寒地凍的天氣,被和煦的春風和燦爛的陽光取代。
“九九那個艷陽天來喲/十八歲的哥哥想把軍來參/風車呀跟著那個東風轉/風車呀跟著那個東風轉……”劉圣平哼著歡快的小曲,拉開窗簾,把窗戶打開,把房門打開,陽光照進來,金光點點,光影斑駁,撒下一屋碎金。春風吹進來,伸出溫暖的大手,摩挲得人毛孔翕張,渾身舒坦。
“南風吹其心,搖搖為誰吐?”劉圣平站在窗前凝神遠眺,遠山環繞,疊翠如畫,樓房下面一條小路,隔著小路不遠就是一壟壟農田,田間有零星早開的油菜花,這春的信使,穿著黃裙子的小精靈,嫩黃嫩黃的,有的起舞,有的點頭,有的哈腰。
妻子林國月背靠在床頭,瘦削的手臂軟軟垂在床沿,表情嫻靜,眼神明亮。一向少有開口的她,竟也張嘴念起了2017年冬丈夫為她寫的一首小詩《小精靈》:
遠方的小精靈/藍藍的翼/晃暈了亮//沉下去的黑/一點一點浮上來/又打著旋慢慢轉過去/青春啊/我的愛人/我要彎一彎腰/將你細細拾起
短短幾行,字里行間透著愛和力量。她念起詩來,結結巴巴,很吃力,臉憋得通紅。當念完最后一個字時,她眼角溢出了淚水,淚水仿佛兩只肥白的蟲子,在臉頰蠕動。劉圣平輕輕走過來,把頭挨向她的頭,輕輕捧起她的臉,又用手作喇叭狀湊過她耳邊,低低的說:“老婆,今天是新年第一天,從今往后,你都不許哭,要開開心心。”他手指向窗外的艷陽天和從窗外瀉進來的陽光,“你看外面的天氣多好,太陽公公都跑進來看你,正沖著你笑呢。月,你也笑一個好不好?”他憐愛的為妻子擦拭眼淚。
窗外金燦燦的太陽掛在天上,好似一個紅金盤,灑下道道金光。
“好,我聽……聽——你的。”妻子細聲應道,笑了笑。她在丈夫的懷里溫軟如泥,雙腮紅潤,像個被寵慣了的孩子,“只是……這些年來,我拖……拖累了你!讓你受……苦了。”她又忍不住嚶嚶抽泣起來。
“月,我是你丈夫啊,不要這么說——你在,家就在。”“噓!”他將食指豎在唇邊,“你怎么又哭了?咱不是說好了不哭了嗎?”
“嗯,嗯。”妻子搖搖頭又點點頭。
春節一到,家家戶戶熱鬧起來。劉圣平一家也不例外,他為妻子擦洗好身子,換上新買的衣服,然后給她吃藥喝水,聽輕音樂,陪她嘮叨家常……兒子劉飛鴻則在廚房里淘米、洗菜、包餃子準備中餐。劉圣平不斷地提醒兒子這個不要洗錯了,那個別摻雜在一起搞混了,并特別交代:“你媽媽的中餐我來做。”
兒子聽了嘟著嘴不高興,從廚房門口探出頭來沖劉圣平扮了個鬼臉,說:“爸,您看我從今天開始又長大一歲啦,我都這么大的人了,難道我給媽媽洗個菜也會弄錯?您也太低估我的能力了——吧?”兒子為表明自己的不爽,故意將“吧”字拖了個長音。“沒有媽媽就沒有我,我也想更疼愛、更關心她。”,兒子心里想,“我今年都22歲了,已經是個成年人了,不是小孩子了,爸爸應該把我當大人看待才對呀!”。
對于兒子剛才的反應,劉圣平作為父親,心里“咯噔”一下,愣了愣:從小到大,在他眼里兒子是個“講什么聽什么的乖乖仔”,在他心里兒子還是個“沒長大的孩子”。也就愣了那么幾秒,心思細膩的劉圣平很快就緩過神來,他朝妻子看看,連拍幾下自己的額頭說:“嗯嗯,是我多嘴了,鴻兒做事我們放心啦,你自己計劃著就好。”這時,父子倆似有默契,相視一笑。妻子也露出了兩個淺淺的小酒窩。
日當正午,一大桌子飯菜已經做好,香噴噴饞得人流口水。可再好吃的飯菜也得先她吃了再說,這這是父子倆多年來形成的習慣。劉圣平左手端著飯碗,右手拿著調羹,一小勺子,一小勺子,往妻子嘴里一小口一小口喂。還適時給她喝一兩口溫開水。
妻子嘴刁,挑食,吃飯喝水比較快,腸胃卻不好。但往往吃快了卡喉,嗆咳;吃硬了咀嚼不了,吞咽不下,消化不良;吃稀了沒胃口,還容易拉肚子。好在劉圣平對妻子的飲食習慣、口味要求很了解。他每天很早都要去菜市場為妻子精挑細選妻子喜歡吃的菜。
久別重逢的欣喜在他們心湖里先是淡淡的,像層漣漪,漸漸就蕩漾開來,形成一波波浪花。
(四)
他身著雪花狀白底襯衫,腳步輕盈,領著她行走在田野阡陌上。泥土芬芳,蛙鳴聲聲,綠浪翻滾。他們談愛情,聊未來,說人生,愜意歡愉。走著走著,她驀地靠近了他,挽著他的手臂,一副小鳥依人的摸樣。他一陣眩暈,立刻被幸福的子彈擊中。
風揚起她的裙擺,像一朵純白的雪蓮花開放。“平,我只有高中文化,你不會嫌棄我吧?”
“不會啊!我就是個窮教書匠,沒有錢,也沒有其他本事,只有一顆愛你的心,你不嫌棄我就好了。”
“呵呵,可是我的年齡要比你大3歲多喲。”
“女大三抱金磚嘛,你未嫁,我未娶,我覺得這樣很合適呀。”
“嘻嘻,你說愛情是什么呀?”
“我覺得無論是陽光還是風雨,無論貧窮還是富有,喜喜憂憂,都要一起面對,永遠不分開,這才叫愛情。”
“你會永遠愛我,永遠和我一起嗎?”
“會的,會的。我眼里是你,心里也是你。我說過,你就是我生命中的太陽。”
“嗯嗯,嗯嗯……”
“江畔何人初見月?江畔何年初照人?”夜色如水,明月如霜;蛩聲細細,楊柳依依。那個夏天,那個夏天的夜晚,他們在爛漫的月光下,坐在學校背后的小河邊,軟語噥噥,不說再見。
一個人的20年:堅毅成一棵樹,“我要你好好活著”
(一)
1996年夏,劉圣平與林國月的愛情修成正果,辦理了結婚登記,成為了夫妻。
1997年2月3日,隨著醫院產房內傳出一陣響亮的嬰兒啼哭,林國月腹中的小生命呱呱墜地了。她給劉圣平生了個大胖小子!
由于妻子懷孕期間身體弱,嬰兒又屬于早產,不得不進行剖腹產分娩,好在母子平安。
“我終于做爸爸了!老婆你辛苦了……”,劉圣平坐在妻子床邊,看著睡在妻子身邊胖嘟嘟、嫩生生、葵花一樣鮮亮的兒子,喜不自禁,同時也為妻子心疼不已。
他給兒子取名叫“飛鴻”,寓意展翅高飛、宏圖大展。他暗暗發誓要對妻子好一輩子!
(二)
歲月留香,時光清淺。劉圣平當教師,林國月當工人,兒子乖巧可愛,一天天健康成長,夫妻兩人都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固定的工資,工資雖然不高,家里也沒有多少余錢,但一家人不愁吃穿,和和睦睦,其樂融融。
天有不測風云。可是,這樣安樂幸福的日子還沒兩年,老天就給他們一家開了個天大的玩笑。
從1998年下半年開始,林國月身體出現不適癥狀,主要表現在說話結巴、走路不穩、手發抖。起初林國月以為是工作、家庭兩頭跑,太忙太過辛勞所致,認為沒有什么大問題,只要休息好就不礙事。
“我覺得你最近不正常,去醫院看一下醫生吧?”,“我真不放心你,還是到醫院做做檢查為好。”,作為丈夫的劉圣平卻多留了個心眼,為她擔心起來,多次勸她去醫院看醫生,林國月卻堅持不去,理由是“不礙事,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再說,家里兒子沒人看管,哪有時間!”。劉圣平說得多了,她還不高興,撅著小嘴,咧成月牙狀,拿著粉拳就去敲他。
隨著時間的推移,她行動更遲緩,說話存在障礙,語音變低,咬音不準。她在休息狀態時手腳也會間歇性抖動,原本寫得一手好字的她,寫起字來歪歪扭扭,彎曲不正,像蚯蚓一樣細小;吃飯的時候,手還發抖,連筷子都拿不穩;走路時步態異常,或邁著碎步,或往前沖。
病像個魔鬼,說來就來,1998年底,經省、市兩級大醫院檢查,林國月的病癥被確診為帕金森綜合征。
帕金森綜合征是一種慢性的中樞神經系統退化性失調,屬于慢性進展性疾病,這種病的主要臨床特點是:靜止性震顫、動作遲緩及減少、肌張力增高、姿勢不穩等為主要特征。醫生說這種病一般都不能治愈,也無有效藥物控制震顫。
一紙診斷書和醫生的一番話,猶如兩道閃電忽然劃過天際,“轟、轟”雷聲炸響,頃刻間,黑壓壓的云團像大鳥的翅膀張牙舞爪壓過來。緊接著,飄飄灑灑下起大雪,不僅有雪花,有大豆般的冰雹,還結成了厚厚的冰凍。
“天啊!……怎么會是這樣啊?!”劉圣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仿佛一頭怪獸長了無數尖刀般的利齒,撲過來,撲過來,追趕著他,撕咬著他。
林國月則釘在醫院檢查室里,臉色慘白,頭搖得像貨郎鼓,身體篩糠似地顫抖著,站都站不穩。劉圣平見狀,趕緊扶住她坐下來,握緊她的手,哽咽的說不出話來。她雙肩耷拉,脖子向兩邊歪著,眼神呆滯,像一泡軟泥巴。
男兒有淚不輕彈,劉圣平半蹲著,拍拍她的肩,安慰說:“月,別怕,有我在呢。”妻子一頭扎向他寬闊的肩膀,心一酸,眼淚嘩地奪眶而出。妻子的淚,像一枚枚重磅炸彈,又像是催化劑,在他的心湖里洶涌地發酵著悲傷。
夜像幕布一樣扯了下來。他緊抿的的嘴,繃成一條線,往左歪歪,往右扭扭,終于還是忍不住咧開嘴,哇哇哭出聲來。
(三)
有一句話說得挺好:“生命之舟面對險灘,面對激流,弱者會選擇逃避和放棄,而強者則會選擇面對和挑戰”。面對這突如其來的不幸,作為家庭的頂梁柱,劉圣平無疑選擇了“面對和挑戰”。
“哪怕有一線生機都絕不放棄!我相信老婆的病總會有出現奇跡的一天,一定會好起來的!”2003年的一天,劉圣平聽說有一種叫“細胞刀”的外科手術,對妻子的帕金森綜合癥可能有效用。因其精確度從傳統手術的肉眼可見的厘米數量級提高到細胞水平的百微米數量級,病人在實施手術過程中需作局部麻醉、頭顱鉆孔,所以被稱為“細胞刀”手術。不過做這種手術費用昂貴,一般家庭承受不了。他咬咬牙,還是簽字交錢給妻子做了這個手術。結果是事與愿違,手術做了后,病癥還是沒有明顯改善。這次白白花去的幾萬元錢,就如把一塊石頭丟在棉花上一樣,一點聲音也沒有。
屋漏偏逢連夜雨。2004年,妻子林國月所在的五交化公司改制,她成為了一名下崗工人,原先的固定工資沒有了,僅靠劉圣平一點微薄的教師工資,難以維持這個家的日常開支和妻子每個月必需的2000多元藥用費。
世界以痛吻我,要我報之以歌。劉圣平肩上的擔子更重了,壓力更大了,他既要關心照顧好妻子的飲食起居,又要照顧教育好兒子,為了緩解經濟壓力,補貼家用,他不得不利用雙休和寒暑假時間幫人去打零工,什么臟活累活都去干,每天忙得像個陀螺轉,恨不得自己有分身術。妻子實在看不過去,說“我都是廢人一個了,活著還有什么意義,死了算了”,她幾次要自殺,幸好發現及時。“這個家不能散啊!你死了,我怎么辦?兒子怎么辦?你一定要給我挺住,我要你好好活著!!”劉圣平抱住妻子,態度強硬,話說得斬釘截鐵,神情堅毅,堅毅成一棵風雪中的樹。
2009年,民政部門為林國月辦理了二級肢體殘疾證。正如醫生所推斷這個病“不能治愈”一樣,妻子的病一天比一天嚴重,生活質量嚴重下降,生活基本無法自理,像解系鞋帶、扣紐扣等動作都變得異常困難了。她走路時起步也相當吃力,一旦開步就身體前傾,不能及時停步。偶爾外出走路鍛煉,劉圣平都要小心攙扶著她,生怕她摔跟頭。同時,她還肢體麻木,語言不清,流涎等,就像個嬰兒。劉圣平心中痛苦、難過、傷心,難以排遣,他寫下一首《情殤》:
那片窒息的黑/揪住春天的胸/放過我吧?/雷聲轟隆隆滾過來/坐在門墩上/任閃電一道道撕咬著緊裹的黑/他跑過來/風聲裹住他單薄的身體/她仍無動于衷
1999年至2014年,這15年時間里,由于家庭變故妻子患病,劉圣平一有時間就背著妻子到處尋醫問藥,足跡遍及郴州、長沙、上海、南京、北京、天津、吉林長春、重慶等十余個大中小城市的各大醫院,花掉手術費、住院費、醫藥費加上路費、食宿費等各種費用前后達40多萬元,不僅花光了家里積蓄,還欠下了一筆很大的外債。
(四)
命運弄人,蒼天無情。妻子林國月的病終究沒有出現奇跡這一天。從2015年起,林國月的病情急轉直下,變本加厲,她日常生活起居竟然變得完全不能自理,僅靠藥物維持生命。她癱瘓在床,再也起不來,不能走路,下不了床,說不起話,吃飯靠流食,睡覺靠哄,小便靠插管子。了解劉圣平妻子病情的人都說“要不是劉圣平不離不棄把妻子照顧得這么好,很可能她早就死于肺炎、骨折等并發癥了,哪能一拖就是20多年啊!”
“這個病我來得,老婆就不會這么痛苦難受了!”劉圣平照顧妻子就好比照顧一兩歲小孩一樣,非常細心、耐心,體貼入微。面對妻子這個病,他從2017年起就無奈地向學校申請辦理了請假手續,開始寸步不離在家照顧妻子。
有那么一年半載,他愁得自己也患上了抑郁癥,整天悶悶不樂,茶飯不思,不肯出門,不肯見人。然而妻子和家庭始終是一塊巨大的磁鐵,看著長大成人的兒子知冷知熱、忙里忙外,還有一句對妻子“你在,家就在”的話,時刻在耳邊響起,像有一口洪鐘一樣敲醒自己,像有一根鞭條在抽打自己,使得他很快又自我調節好了心態,重新開始樂觀生活,去做一個好父親、好丈夫。
道德當身,不以惑。林國月曾有一次對劉圣平說“平,你就聽我一句勸,你再……再找一個吧!你還……還年輕,我不能——再這么耽誤你……!”劉圣平心一陣痙攣,頭搖成撥浪鼓,他蹙緊眉頭,恨聲恨氣:“我既然選擇和你在一起,就會永遠不會離開你,不會拋棄你!”2016年上半年,有一個了解劉圣平家庭底細和知道他為人的單身離異中年女老師看上了他,成天有事沒事找各種理由接近他。女老師人長得漂亮耐看,熱情開朗,她有房有車,家庭條件好。一天,女老師瞅準個機會請他吃飯,席間,女老師故意喝許多酒,“我知道你老婆那方面不行了,你是個男人,讓我來陪你照顧你吧?”借著酒勁說喜歡他、愛他之類的話,說只要他同意和她一起生活,她就愿意把房子和車子過戶給他。說著說著,就往他懷里鉆,一雙手蛇一樣纏住他不放。劉圣平剜了她一眼,鐵青著臉,一把推開她,丟下一句“你醉了,我要走了!”,悻悻而去。
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劉圣平沒有這樣做。2017年底至2018年初,妻子林國月由于肺部感染和突發腦梗塞住進了縣人民醫院ICU(重癥監護室),她兩眼翻白,全身冰冷,毫無意識。整整40天的時間,劉圣平臉上的胡子硬邦邦的,像瘋長的野草,頭發蓬亂,還白了一大半,清瘦的臉龐塌陷更深,直熬得兩只眼睛布滿血絲,渾濁的眼淚不斷從眼窩里滾出。他守在醫院,跪在醫院的走廊里,口中喃喃念著“我要你好好活著、你要好好活著”,默默為妻子祈禱。
興許是大地被他誠意感動了,興許是老天看他的眼淚快流干了而發慈悲,興許是妻子聽到了丈夫內心的呼喊,總之,她終于醒過來了!
尾 聲
歲序更新,春風初度。2019年的春天來得特別快,幾場稀疏的春雨過后,就是驚蟄,劉圣平家門口對面的那一大片田間油菜花,爛漫盛開,黃燦燦像鋪上了金色的地毯,春風吹過,涌起一股股金色波浪,空氣新鮮而濕潤。
趁春光燦爛,春暖花開,父子倆一起將他們骨血熨帖的親的人——林國月,慢慢挪向陽臺。她坐在搖椅上,面向春天,陽光暖暖落下來,慵懶的灑在她身上,仿佛鍍上了薄薄的一層光暈。
“兒子,四月份就要去考公務員了,老婆,你的身體一定要好好的、棒棒噠,你要為他加油喝彩,好不好?”
陽光灑滿一地,她輕輕點點頭,臉如葵花一樣向著陽光綻放。
那是良心之光,道德之光,希望之光,太陽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