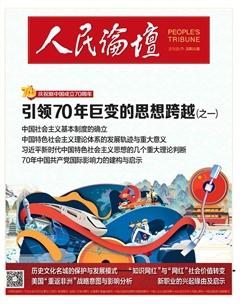后閱讀時代“躍讀”的實現與意義
師曾志
【摘要】近年來經典作品重回人們視野,傳統閱讀所需要的專注度、理解力和體驗感已難符合當下人們快餐式的碎片化閱讀習慣。互聯網超鏈接、超文本技術引導出一種新的“躍讀”,成為人們不斷提高自身認知能力、保持對知識智慧的追求以及安置自我身心的源泉活水。在后閱讀時代應觀止經典,在傳承中回歸自我,在閱讀傳播中注重自我思想和行動的同時卷入,讓經典閱讀真正為我所用。
【關鍵詞】后閱讀時代 “躍讀” 經典閱讀 【中圖分類號】G252.1 【文獻標識碼】A
后現代閱讀時代:“躍讀”作為一種閱讀傳播方式
閱讀原指人類從編碼系統中獲取信息并理解其含義的能力,后又特指人類對書寫在物體表面上的連續文本符號的理解。隨著媒介技術的發展,閱讀還包括了人類從電子屏幕上獲取編碼信息的能力。閱讀演變與傳播過程也是考量人類進步的依據。
在某種意義上,閱讀的歷史也是媒介發展的一種折射。在文字尚未出現以前,閱讀意味著朗誦和說話,口頭文字在傳遞知識和記錄交易等方面承擔著“見證者”的角色。口頭事實也伴隨著歪曲、爭執和遺忘,作為表達形式用以記錄事實的文字便由此誕生。直到紙本早期,閱讀仍是少數人的事情,識字、書籍、教育都是特權階層的專屬品,人們對文本尤其是經典作品往往懷著虔誠和敬畏之心,閱讀傳播是一種權力與權威的象征,這是傳統閱讀時代的顯著特征。隨著印刷術、數字技術的發展,書寫文字的力量被釋放,復制書籍快速取代手抄書稿,也催生了現代閱讀。原屬于少數人的閱讀走近了大眾,經典作品也從神圣邁向日常。
傳播技術與手段的發展并未減損人們對書籍的敬畏,作為獲取知識的重要媒介,書籍仍保持著原有的權威性和神圣性,閱讀經典一直被視為一種有深度的審美活動。然而,隨著后現代思潮對權威的解構和對經典的消解,再加上技術發展帶來閱讀形態的轉變,人們進入后閱讀時代。
美國學者伊哈布·哈桑通過對文學領域的后現代特征進行考察與分析后,發現不確定性與內在性是后現代主義的兩大核心構成原則。不確定性是后現代思想及后現代文學的根本特征,文學作品中的模糊性、間斷性、反叛與曲解都是后現代主義的精神品格。內在性是指文學不再具有超越性,不再對精神、價值、終極關懷、真理之類超越性價值感興趣,相反,后現代文學是主體的內縮,是對后現代環境的內在適應。后現代文學的碎片化、平面化、互文性和反體裁的特點不僅體現在版式、印刷、字體等形式上,甚至也表現在閱讀傳播層面,由此,我們說人類進入后閱讀時代。
不同于現代閱讀,后現代閱讀指的是在互聯網技術的支持下,讀者打破以往線性閱讀模式,根據自身需要選擇作品、解讀文本,生成意義并在此基礎上獲得自我認知、激發自我體驗的閱讀方式,碎片化與差異性是后現代閱讀中最重要的特征。
后閱讀時代人們常常不按作者和文本本身的順序閱讀,在隨意瀏覽的過程中不斷跳轉、反復、騰挪,打破了印刷文本線性閱讀的秩序,一種新的閱讀方式——“躍讀”由此產生。“躍讀”是指讀者根據自身的知識、興趣和過往經驗、體驗不斷越界,閱讀逐漸由時間的連續中斷裂出來,轉向時空并置,實現閱讀歷時性與共時性的共在。“躍讀”突破作者權威和文本中心,互聯網帶來的超鏈接文本更是賦予了人們根據自身需要、興趣、知識和過往經驗進行閱讀的選擇空間。讀者個體的經驗、體驗和認知方式決定了“躍讀”的程度與水平,為自我實踐提供態度及行為的基礎,正因如此,閱讀傳播本質上影響到社會的變革。
經典閱讀傳播的途徑:格物致知,知行合一
西方社會有關后現代的研究更重視外部世界的變化,在他們看來,社會是碎片的和斷裂的,而東方智慧則強調感性與理性的統一。由此,外部世界的斷裂實則強調的是個體間差異的分野,個體自主性和能動性惟有在格物致知、誠心正意、止于至善的前提下,人格與行動才能形成有機整體。

傳統社會中閱讀與日常生活常常處于分離狀態,對經典作品的認知和理解往往屬于“知”,而日常生活和行為則歸于“行”。古有紙上談兵的趙括、坐而論道的王公和“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書生,今也有徒陳空文、不見之于行事的空想家,閱讀若只是一種精神、思想活動,則很難在傳播實踐中生成智慧,化為行動的力量。
互聯網傳播速度加快,萬物皆媒的連接成為可能,從而徹底改變了人們的時空觀,也大大激發和延伸了人的各種感官,人們的認知與信息快速流動、交換、生成和行動的實現聯系在一起,對經典作品的認知和理解不再是空洞的說教,而是不斷在現實行動中轉化為解決問題的智慧和能力。
互聯網喚醒了人們思想與行動的統一,它與傳統文化中所倡導的知行合一不謀而合。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老子言,“上士聞道,勤而行之”;王陽明則繼承了先人的思想并通過體悟和實踐直接提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主張。“良知”是人人自足、一種不假外力的內在力量,而“致”則是兼備知行的過程,強調行動和實踐的重要性,致良知就是將良知具體入微到日常生活的點滴之中。
近代以降,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的隔離在不知不覺中斬斷了閱讀、智慧和日常生活的緊密聯系。經典閱讀傳播強調的是將閱讀與自我實踐結合在一起,靈活運用各種知識,服務社會,解決問題。經典作品的價值不只是記錄先人的經歷和空洞的、抽離了感覺和情感卷入的知識,其真正的魅力在于穿越時空的限度找到與個體生活密切相關問題的解決方案。因此,經典閱讀不僅要重視“躍讀”,更重要的是身體力行的閱讀傳播,不應只是書齋里的悶頭苦讀和和苦思冥想,更應該在閱讀經典的同時體悟生活,將對經典文化和智慧的理解與個體對現實的關懷與創造結合起來,寄知于行,行中致知,使傳統經典依然能夠在傳播中煥發出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