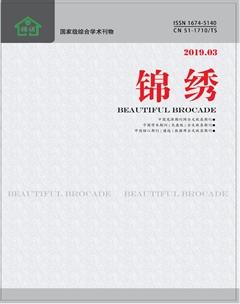戈壁情
姜初陽
火車上,窗外一片荒漠戈壁景象綿延不窮,厚重的玻璃也擋不住風沙在耳邊的呼嘯,伴隨著細沙黃土肆意地鉆到窗沿。我坐在窗戶旁,看著這白天黑夜都毫無變化的景象甚至懷疑火車在一個地方打轉。
可惜不是。在前往神秘古老的和田之路上,或許正從綿亙1000余公里如艾德萊斯綢緞般鋪開的塔克拉瑪干大沙漠邊緣飛馳;或許在塔里木盆地旁的戈壁上潛行。一省之內,跨越了一個時區,穿越了黑夜與白晝,一路上看盡了大漠戈壁,亦有綿延的山、不朽的胡楊、堅毅的紅柳——不能稱得上是欣欣向榮,但它們都用力地活著。極目遠眺,一個個的沙包與夕陽輝映,在火車的轟鳴聲中,我仿佛聽見了陣陣的西域駝鈴。
同在新疆長大,千里之外的南疆在我記憶里卻是陌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亦或是流言構成了我對這片土地的記憶,貧窮、濃厚的宗教氛圍等等刻板印象充斥著我的腦海。
兩天的舟車勞頓,終于到了和田市,又是兩三個小時的車程前往父親的住所。途中休息,捧起一柸黃沙緊緊攥住,卻也逃不出狂風的漩渦,不少砂礫順著風勢硬生生拍在我的臉上,生生的疼——不知父親狀況如何,我迫不及待了。
父親參加“訪惠聚”工作己有近兩年了,為了精準扶貧、更為了一方穩定。此次入駐到新疆極為貧困、且形勢復雜的地區展開工作,頗有些“奉命于危難之間”的悲壯意味一一告訴父親,他只笑道這是一種使命,他愿意。
我不懂什么是使命,我只知道一家人能在一起最好。
去父親所駐村莊的路上,過了不知道多少道安檢的關卡,這在新疆并不稀奇。窗外風沙呼嘯,卻一路平穩一一這倒出乎我的意料,沙漠邊上的地方能有修的這么好的路還真是稀奇!
車開著,我的刻板印象一點點分崩離析著,“稀奇”的事不止一件。大漠邊緣,一路上卻都是平整的柏油路,維漢雙語的路標、宣傳語,有大片鱗次櫛比的新樓亮著電燈,也有樸實寧靜的村莊偶爾跳動著幾簇人間煙火。
下車進村,幾個光著腳丫的維吾爾族小巴郎子如一群好奇的小獸打量著我,靦腆的用新疆味兒十足的國語試探著說了聲“姐姐你好!”,隨之嬉笑著一哄而散,旁邊坐在梧桐樹下、帶著小花帽的維吾爾族老大爺慈祥地看著孫兒們微笑的向我點了點頭,揮手示意。不知為何,一種莫名的感動直沖上了我的鼻腔一一早有耳聞為了能讓村民們更好地接觸外界信息、得到更多外出務工機會等,大批干部、志愿者投身南疆國語教學事業,天知道在這幾乎百分之百都是維吾爾族的土地上開展這樣一項工作是多么浩大的工程!維吾爾族同胞的熱情同時讓我倍感親切,完全感受不到語言不通與信仰不同帶來的排斥與隔閡,你能感受到那種安全且舒適的氛圍。
感嘆著走著,父親剛從會議室走出了正好看見了我,眼睛里好像閃過一絲光彩。我看了看父親,他看起來老了十歲,肆虐的風沙刻在了他溝壑般的皺紋里。我強忍住心酸,跑了過去,父親的精神看起來卻比我還好,拉著我在大門口照了兩張相,隨即給我介紹這個村子。
這個村從前是什么樣我無法想象,我只看見平直的柏油路縱橫在村落間,路燈矗立在每一個昏暗的路口間,黑暗無處躲藏一一這些都是父親與其他的駐村同事們為這個村帶來的,為這些硬件設施,他們不知道奔波了多少個日夜。講這些的時候他充滿自豪。很奇怪,我也自豪。
隨后幾天的見聞甚至讓我舍不得離開這片土地。新蓋的樓房里已經入住了不少村民,他們也總算能暖和過個冬了。飯后總能維吾爾族老大媽坐在樓下談天說地;文化宮里四五歲的維吾爾族小朋友搖頭晃腦的將唐詩背的字正腔圓;雖然氣候惡劣,但昆侖山的雪水滋養的和田同胞們卻透著骨子里的樂觀,不改其樂:其他地方的“新疆美食”在此處都會黯然失色,物美價廉讓人不知所措,這里的歌舞在新疆都是最正宗的,跳出的是大漠的奔放與快活。為了讓特色走出去發展經濟,加工、包裝、技能培訓一一這里工作的人們盡一切能勢招商引資著,旅游業萌芽著,通訊設備大規模得普及著——一股星星之火在這片土地上悄無聲息的有了苗頭。
我突然明白了父親所念叨的“家國情懷”與使命。自新疆“訪惠聚”工作展開以來,有多少個“父親”犧牲自己,離開家人奔赴南疆,在一片荒蕪上屯墾戍邊,才有了今天這種局面呢?
我不得而知。但一想起在祖國的邊陲,那個從未真正進入過大眾視線、被現代化“落下”的遼闊土地上有這樣一群人默默付出著,為發展、為穩定奮斗著、戰斗著,我就感到溫暖,有希望。
走了,但我會回來的。一路上看著戈壁荒漠中的鐵路與沙漠公路,我看見了升起的太陽照在了每一處渺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