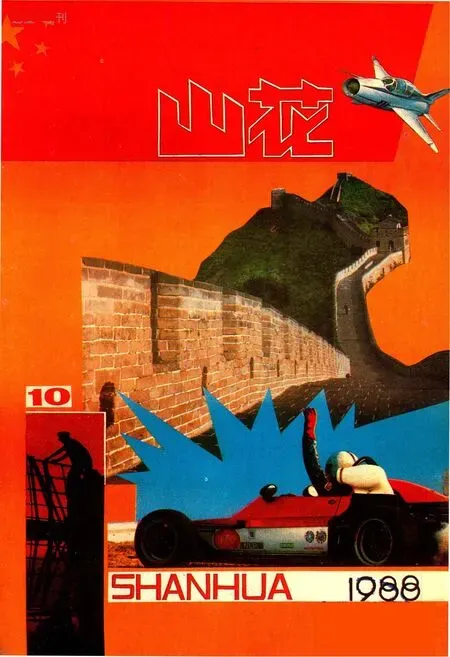驚蟄:大雨滂沱,人世慌張(外一篇)
海飛

2018年3月3號(hào)凌晨2時(shí)06分,我開始坐在杭州城西一幢寫字樓的辦公室里等待驚蟄的來臨。窗外的雨聲有著一種鋪天蓋地的響亮,這樣的響亮讓我心生安靜。空曠狹長(zhǎng)的馬路上顯然已經(jīng)沒有行人,路燈光潮濕中透著蒼涼和清瘦。我把身子探出窗外,長(zhǎng)時(shí)間感受著初春最深的夜涼,并且十分愿意暗夜之雨將我打濕。
我是如此地?zé)釔壑贾莸拇笥赇桡N以敢庠谶@樣涼薄的時(shí)分,用探出窗口的半個(gè)身子,等待驚蟄的來臨。
在這之前的午夜時(shí)光里,我像一只無聲無息的貓一樣在辦公室里來回踱步,和散落各處的同行用網(wǎng)絡(luò)語音開會(huì),熱烈地討論一個(gè)叫馮寶的人,是怎樣在上海街頭的雨地里屈辱地跪下,并撿起一塊大洋。一塊大洋有時(shí)候不是錢,是一條命。那時(shí)候的馮寶從鄉(xiāng)下來到大上海,十里洋場(chǎng)中他不過謀到了一份給大光明電影院畫電影海報(bào)的工作。但我還是覺得,他應(yīng)該算是一名畫家。這位后來成為特工的畫家,最終由慌張轉(zhuǎn)為篤定。槍林彈雨中,他覺得自己命不會(huì)久,那么每一天都是他多出來的日子。
他想把多出來的日子過得精彩。而大部分人都認(rèn)為自己的日子不夠多。
這是一個(gè)叫《棋手》的電視劇本,那個(gè)叫賀羽豐的小伙子,我想象他干挑挺拔,熱烈而平靜,隱秘而光榮,慌張而美好。上海某棵法國(guó)梧桐下,他倚在腳踏車邊,穿著白襯衣并卷起袖子,頭發(fā)干凈清爽,他明亮地笑了一下,我就覺得這個(gè)叫做驚蟄的節(jié)氣就快要來了。
無數(shù)個(gè)午夜時(shí)分,或者是紛繁雜亂荒蕪的夢(mèng)境中,我都能聽到隱隱的雷聲滾動(dòng),這樣的聲音里充滿著無數(shù)的未知。你說吧,像不像人生?
事實(shí)上,這單調(diào)、冗長(zhǎng)的兩年,我一直像是河里的水草,從未露頭但能接受陽光,氧氣和養(yǎng)分,并且在水平面以下?lián)u搖擺擺地飄蕩。比起在空中隨風(fēng)飄蕩的風(fēng)箏,少了俊逸多了笨拙。但我曉得的,至少沉默的水草有根,根扎在河床,河床寬大而溫暖。這兩年,我沉浸在小說《驚蟄》中不能自拔,我把這個(gè)小說改成了劇本。這個(gè)小說在《人民文學(xué)》首發(fā),被《長(zhǎng)篇小說選刊》和《小說月報(bào)》分別選載,入選廣電總局“大眾喜愛的50種圖書”書目……
我相信關(guān)于《驚蟄》,還將會(huì)有許多熱烈的故事。我希望她能劍拔弩張,風(fēng)起云涌,真正像一聲驚雷一樣,撕開云層并讓大地顫抖。我還有一本叫做《驚蟄無比美好》的散文集,即將出版。所以,這兩年我大約是同驚蟄較上了勁。哪怕是在此刻,雨聲未停,人聲未至,一切美好都是在夜的安靜里悄然生長(zhǎng)。哪怕茁壯成長(zhǎng)的只是一朵苔蘚,那也有著她微不足道的青春,美麗,慌張,甜蜜,以及確實(shí)存在的愛情。
如果我仍然將身子探出窗外,往右看是競(jìng)舟北路,我可以看到《驚蟄》中的陳山分明在大雨里奔跑,火藥的氣息在雨水中流淌。往左看,是古墩路,我可以看到《風(fēng)塵里》中萬歷年間的鬼腳遁師田小七,他穿過雨陣的姿勢(shì)迅捷得讓人眼花繚亂。在這樣的奔跑里,鐵器鳴響,他騰空躍起時(shí)手中握著的繡春刀已然出鞘。我悄然想起,田小七的隊(duì)友中,有個(gè)非常堂皇的名字,叫唐胭脂。他是一個(gè)男人,但是他熱愛著化妝,他把化妝當(dāng)成他在明朝年間的畢生事業(yè)。他們都有著慌里慌張的人生,他們都像歌中唱的那樣,沒有歲月可回頭。
我們的歲月也不能回頭。而慌張并不是一個(gè)丑陋的字眼,在多年以前,我開始寫一個(gè)叫《大西南剿匪記》的劇本,匪首劉大卯很久沒見著他中意的少奶奶鄭幺妹,他終于把她堵在民國(guó)年間的墻壁前,那時(shí)候還沒有壁咚這個(gè)詞,但他確實(shí)是十分壁咚地告訴鄭幺妹,見不著你,我心里慌。
我還突然明白,人生有時(shí)候其實(shí)都來不及慌張,一生就已經(jīng)匆匆而過。
我十分尊敬的一位叫紅柯的作家,突然離開了這個(gè)世界。他曾經(jīng)寫出那么多美好的文字,比如《西去的騎手》,現(xiàn)在他如騎手般的離去令許多作家和讀者痛惜。事實(shí)上,在大雨籠罩著的鄉(xiāng)村,比方講我的故鄉(xiāng)丹桂房,也會(huì)有一些人的離世。他們走得悄無聲息,比螞蟻?zhàn)哌^的聲音還輕,像是從來沒有來過這世間一樣。他們的消息被二十四個(gè)節(jié)氣封鎖,并不能傳得很遠(yuǎn)。而這個(gè)世界本身,天空、大地、歲月,向來都是一如既往的從容篤定,從不慌張地輪回。一位更年輕的經(jīng)營(yíng)中文內(nèi)容管理的女子,在離世前寫下:游歷人間四十二載,我任性過也努力過,歡樂比痛苦多,收獲比遺憾多……她最后說,不必懷念我,盡興去生活,再見。
有時(shí)候,說再見就是再也不見。比如生命,比如愛情……
杭州地鐵二號(hào)線上穿行的地下列車,是我經(jīng)常使用的交通工具。地鐵站臺(tái)白亮的廣告牌上,有二十四節(jié)氣的呈現(xiàn)。無數(shù)次我會(huì)在那幅“驚蟄”的圖前,久久地站立,十分像是緬懷。我想,我緬懷的可能是時(shí)間,也可能是過往。我會(huì)隨著人流候車,上車,下車,我沉默寡言,和地鐵上所有的男人女人一樣,喜歡用手機(jī)來消磨這地下的時(shí)間。車上的人們,表情木訥,他們和地鐵一樣,像機(jī)器般地生活著,慌張而匆忙,機(jī)械而單調(diào)。
一般我會(huì)選擇在武林門站下車,從地下回到地上,有一段去往單位的短暫的路。那一次我重逢了雨,而且我沒有帶傘,當(dāng)我沖進(jìn)雨陣被雨淋濕時(shí),我的眼睛透過這密密麻麻的雨,看到了馬路四周閃動(dòng)的都是匆忙的人生啊。一切都靜止了,紅綠燈在更替她的顏色,我突然想,世界會(huì)不會(huì)定格與靜止。如果是,我愿意是在雨與雨的縫隙之間靜止。最好頭頂一道閃電,春雷滾滾……
雜亂無章的這個(gè)夜晚,斷斷續(xù)續(xù)地改劇本,寫文字,看窗外的雨陣。事實(shí)上我并沒有聽到隱隱的雷聲,但是我相信,驚蟄這個(gè)節(jié)氣正在趕來的路上。在網(wǎng)上,最終還看了馮小剛唱的《那些花兒》,然后《芳華》里的那些鏡頭在電腦屏幕上再次一一呈現(xiàn),穿著雨衣的劉峰在雨中捋了一把臉上的雨水說,我是劉峰。
人生中有多少場(chǎng)大雨滂沱,也就會(huì)有無數(shù)次的人世慌張 。寫下以上文字,紀(jì)念和期待驚蟄。那么,大雨請(qǐng)繼續(xù)。那么,凌晨4時(shí)08分的杭州,晚安。
鄉(xiāng)愁是被大風(fēng)吹散的月光
壹杯酒
倒上這第一杯酒的時(shí)候,我開始相信,鄉(xiāng)愁就是被大風(fēng)吹散的月光。如此零碎,細(xì)微,溫暖,涼薄,卻又無處不在。月光打濕黑夜中的故鄉(xiāng),看到那些被風(fēng)吹散的月光,我就想站在丹桂房村的土埂上痛哭。
村莊沉睡。我久未謀面的小伙伴們都已人到中年,他們用單薄而且日漸老去的身體,護(hù)衛(wèi)著妻兒老少。我突然之間覺得,人生匆忙,所有經(jīng)過的碼頭都不能回頭。多少的月光下,我們依稀還只是衣衫單薄的少年。多少的月光下,我們又突然發(fā)現(xiàn)雙鬢有了零星的白發(fā)。在風(fēng)塵里打滾,我們變得參差不齊的城府和世故,精明,以及些許的狡黠。只有月色是潔白的,像童年時(shí)課桌上未曾寫下一筆一劃的紙張。而面對(duì)著沉睡的黑黝黝的村莊,以及那些在月色之中休眠著的各式人生,我大抵是能想見明晨村莊或被大霧封鎖,或被陽光披灑,如果天氣寒冷,可能還會(huì)見到一層玉樹臨風(fēng)的白霜。
有人說溫一壺月光下酒。那么故鄉(xiāng),白霜也是一種酒 。
貳杯酒
其實(shí),我的半個(gè)故鄉(xiāng)在浙江諸暨一座叫丹桂房的村莊,我的另半個(gè)故鄉(xiāng)在上海市楊浦區(qū)龍江路。我是被風(fēng)吹來蕩去的蒲公英。作為一株普通的植物,曾經(jīng)有那么一片短暫的光陰里,我的故鄉(xiāng)甚至是江蘇南通縣一個(gè)叫環(huán)本的地方。我在那兒用我最青澀而美好的年紀(jì)服兵役三年,在時(shí)隔二十五年之后,我曾踏進(jìn)陳舊的人去樓空的營(yíng)房。遼闊與空曠,會(huì)增加你的孤獨(dú)感,我就是站在營(yíng)房操場(chǎng)上那個(gè)有著強(qiáng)烈孤獨(dú)感的人。只有軍號(hào)不滅,軍令不滅,腳步聲不滅,口號(hào)聲不滅……所有的記憶,都是不滅的。
我在杭州已經(jīng)生活了十二個(gè)年頭,我覺得我就是杭州的一粒塵土,或者移植成功的蒲公英。在微信和各種通訊技術(shù)如此發(fā)達(dá)的今天,我躲在露臺(tái)上搭建的玻璃房里,數(shù)一寸又一寸的月光。我總是會(huì)在一些熱鬧過后的安靜里,突然惦記沉睡在夜色中的丹桂房。在玻璃房里看見風(fēng)吹月光,也看見雨打屋瓦,那么激烈與溫情,俗世與雅致。我也在玻璃房里寫下了大量的文字,在這狹小的空間里徘徊、喝茶、打電話,吃瓜子。凡人總是會(huì)做一些凡人才做的事,我也不例外。我家露臺(tái)上搭建的玻璃房當(dāng)然屬于違建,在拆違的呼聲中,玻璃房結(jié)束了她七年半的使命。
我覺得玻璃房的消亡,其實(shí)就是一種生命的解體,痛徹我的心肺。現(xiàn)在,當(dāng)每一個(gè)夜晚來臨,我可以直接走向一貧如洗的露臺(tái),月光可以自由拍打在我身上,但我覺得我長(zhǎng)久地站在午夜的露臺(tái)之上,是對(duì)玻璃房的一種懷念與默哀。
有人寫下床前明月光的詩篇。那么故鄉(xiāng),請(qǐng)?jiān)试S我的露臺(tái)也成為一首長(zhǎng)詩。
叁杯酒
露臺(tái)之上,握著一杯醇厚綿長(zhǎng)的海半仙同山燒,那是故鄉(xiāng)的味道。寒意陣陣的午夜,我想到了親愛的山海。山海兄,這是我的第三杯酒,別來無恙,先干為敬。
唐山海是在1940年沉悶得要發(fā)瘋的夏天走下火車的踏板的,他聽到知了的聲音在上海火車南站此起彼伏地響起來,那響亮的聲音在1940年明晃晃的陽光下,恍然是我們的前世所看到的場(chǎng)景和聽到的聲音。此后并不漫長(zhǎng)的歲月里,他無數(shù)次站在黃浦江邊,孤獨(dú)得像一根木頭電線桿一樣,站在那個(gè)年代的月光下。風(fēng)吹起黃浦江上潮濕的月光,連那時(shí)候的槍聲也仿佛是受潮了。
2017年整個(gè)漫長(zhǎng)的夏天里,我都在寫一個(gè)叫《唐山海》的小說。唐山海的故鄉(xiāng)在湖南,這個(gè)叫做“湘”的地方對(duì)我來說神秘而且遙遠(yuǎn)。風(fēng)在城市的上空激蕩與盤旋,我是風(fēng)中拉著一只拉桿箱的匆忙的旅人。風(fēng)吹起了我日漸稀疏的頭發(fā),也吹起一片稀薄的月光。在十分匆忙的人生中,有一個(gè)聲音說,到故鄉(xiāng)去。
然后我就出現(xiàn)在丹桂房村的土埂上。于《麻雀》而言,《唐山海》是番外。而于我而言,杭州城是我的番外。
都在唱月亮走我也走,那么故鄉(xiāng),走來走去就是各種模式的人生。
肆杯酒
我曾經(jīng)在杭州城一個(gè)叫葉青苑的小區(qū)里虛度過四年的光陰。適當(dāng)?shù)臅r(shí)候,我會(huì)選擇沿著運(yùn)河河水的方向走走。拱宸橋上是有月色的,賣魚橋上也有,信義坊也有……可見我是如此地?zé)釔壑\(yùn)河。
江楓是拱宸橋邊一個(gè)穿著長(zhǎng)衫的書生,無數(shù)個(gè)夏天,他喜歡泡在運(yùn)河的河水里摸青殼螺螄。《內(nèi)線》的故事開始的時(shí)候,他站在拱宸橋上的一堆月色中,和一個(gè)叫汪五月的姑娘望著一條條船從橋下經(jīng)過,前往江蘇。然后他帶著一個(gè)叫小歡的小女孩,來到上海灘尋找小歡的媽媽安娜。而失蹤的安娜此刻正在汪偽76號(hào)特工總部的監(jiān)獄里,站在小窗口一小縷瘦骨嶙峋的月光中思念小歡。之前的靈隱寺,曾經(jīng)被一場(chǎng)白雪覆蓋,清秀的鐘聲里,零星的槍聲在某年的冬天響起。江楓作為穿著長(zhǎng)衫的行刺者,當(dāng)過一回比荊軻更失敗的刺客。而更早以前的吳山,日本人的炸彈讓小歡失去了一只手。失去手就等于失去童年,她同江楓一樣猶豫的眼神,在杭州城的民國(guó)年間粗糙而簡(jiǎn)略地掠過了。
這是我的小說《內(nèi)線》中的情節(jié)。我一直在想,有些人文可當(dāng)?shù)昧藭湟部梢猿蔀樘貏?wù)。
李白兄說,舉杯邀明月,對(duì)影成三人。那么故鄉(xiāng),江楓站在拱宸橋上的月色里,也是對(duì)影成三人的。
伍杯酒
我喜歡一部叫做《明月幾時(shí)有》的電影,也喜歡著這部電影的海報(bào)。海報(bào)做成了通緝令的樣子,我們被酒通緝,被欲望通緝,被情感通緝,被家長(zhǎng)里短,被凡塵俗世,被所有的灰塵通緝。我們整個(gè)的人生,是一場(chǎng)被通緝的人生。
而月光,是這一場(chǎng)場(chǎng)通緝的見證者。她十分平靜地看著這一切事件的發(fā)生。
我喜歡張國(guó)榮的一首歌,叫做《風(fēng)繼續(xù)吹》。悠悠海風(fēng)輕輕吹冷卻了野火堆,讓我突然覺得,野火堆是如此的在冷中有暖,在暗夜中有光。海風(fēng),春風(fēng),暖風(fēng),寒風(fēng),狂風(fēng),臺(tái)風(fēng),以及世界上所有的風(fēng)。我一直都在等待著他們的降臨。而被大風(fēng)吹散的月光,是不是我們?nèi)松囊粋€(gè)個(gè)停靠站站臺(tái)上能看到的最憂傷和美麗的風(fēng)景。
杜甫兄說,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xiāng)明。那么故鄉(xiāng),你到底是照亮了我?guī)追智迨莸泥l(xiāng)愁。
陸杯酒
如果你站在丹桂房村的土埂上,向南而立,左手是溪水以及溪水發(fā)出的聲音,當(dāng)然也有月夜升騰的水氣;右手是一座安靜得像一張黑白照片一樣的故鄉(xiāng),偶爾有某戶人家一盞黃燈昏暗虛弱的亮起,像故鄉(xiāng)睜開的一只老花眼。我曉得的,我能聽到月色的聲音,這聲音就像是潮水,一記一記拍打,一記一記讓你的頭發(fā)在這樣的聲音里被打濕,變白,甚至眼神都在此時(shí)老去了。人終歸要老去的。
在這樣的靜夜,可以想一想的是慘淡或美好的人生。那些過往像一場(chǎng)無聲的膠片電影,在劇終以前,呈現(xiàn)各不相同的片斷。這其中有美好,鮮花,酒,音樂,愛情和月亮,這其中也有陰謀,殘酷,暗夜,叛變和病痛。我曉得有一位朋友,在加官進(jìn)爵的路上一路狂奔,他最害怕的是被擠軋與退休。我也記得一位早年故去的朋友,安靜地長(zhǎng)臥在楓江邊的山腳,墳前長(zhǎng)草,墳后是猩狂的野花,并且月光普照。那么神秘、詭異,又透著一種陰森的美麗。這時(shí)候我們才曉得,我們只是大地上奔忙的螞蟻,大地提供了一個(gè)場(chǎng)地,讓各式人等在這個(gè)世界上經(jīng)過并稍作停留,最后不留痕跡。甚至都沒有閃爍過流星的光芒……
有人這樣唱:天上海上沒有路,月亮在偷著哭。那么故鄉(xiāng),讓我在丹桂房這條彎彎曲曲如漫長(zhǎng)人生的土埂上,為我和我親愛的兄弟姐妹號(hào)啕大哭。就像小說《人生》中被城市拋棄的高加林,在家鄉(xiāng)的土地上跪地痛哭:這人生哪……
柒杯酒
明月出天山,蒼茫云海間。長(zhǎng)風(fēng)幾萬里,吹度玉門關(guān)。
我不是詩中的戍邊將士,我只是鎮(zhèn)守著人生的邊關(guān),我只是面對(duì)明月舉起我手中的第七杯酒,我只是想說,那么故鄉(xiāng),你若平安靜好,就是我寄念于你的思緒與牽絆;我若月光加身,就是你加蓋在我身上的不朽商標(biāo)。
那么故鄉(xiāng),我最后還是要同你講的。我始終相信,鄉(xiāng)愁就是被大風(fēng)吹散的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