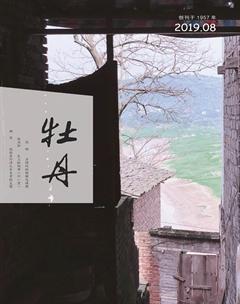《楚辭》中的祭祀形式的研究
楚人“信鬼好祠”,祭祀活動不論對于“廟堂之高”還是“江湖之遠”都有著重要意義。《楚辭》作為楚地文化特產,“書楚語,作楚聲,記楚地,名楚物”自然有不少對祭祀活動的描述,本文將根據《楚辭》分析楚地的祭祀風俗,主要方面有祭祀內容、祭祀形式、現代傳承。
楚人以巫覡扮神的形式祭神祀神,在他們的思維里,神人同欲同好,有普遍的生活要求,因而從人的需要來揣測神靈的需要,與希臘神話將神人化,賦予神人的情感欲望,有異曲同工之妙。翟兌之在《釋巫》中指出:“人嗜飲食,故巫以犧牲奉神;人樂男女,故巫以容色媚神;人好聲色,故巫以歌舞娛神;人富語言,故巫以辭令歆神。”他們以“巫”為媒介,通過供奉犧牲祭品、裝扮鮮艷華麗、歌舞大膽奔放、頌詞恭敬歆娛等方式,使神得到口腹心神各方面的滿足,以求借此取悅、“娛神”從而得到神靈保護庇佑,實現所求心愿。因此,楚國宗教祭祀活動以“樂神”“娛己”為主要目的和特征。
一、犧牲奉神
古代生產力低下,人的生存首要條件便是獲取食物,推己及神,神亦有口腹之欲。許慎《說文解字》曰“祭,祭祀也。從示,以手持肉”,可見祭祀首要條件便是供奉飲食。楚人祭祀“飲”多指酒,“食”多指谷物與肉類。在《楚辭》中,對于祭品的描述不可勝數,人們可以從此窺見楚人的飲食文化與祭祀熱忱。
(一)酒
上古時期便有“祭必飲”的說法,楚人好酒,祭祀用酒更是講究多變。《招魂》中有“華酌既陳,有瓊漿些”中的白酒、“瑤漿蜜勺,實羽觴些”為紅酒、“挫糟凍飲,酌清涼些”提及的是楚人已發明冰鎮酒,《大招》中有“吳醴白蘗,和楚瀝只”為米酒。而《九歌·東皇太一》和《九歌·東君》中有“莫桂酒兮椒漿”“援北斗兮酌桂漿”兩句,說明楚人也有飲甜酒的習慣。由此可見,楚人飲酒的種類之多。
(二)谷物
民以食為天,谷物作為人類主要的果腹食物,在祭祀中具有重要意義。楚地自古土地肥沃,水源廣布,有“魚米之鄉”之稱,物種豐富、產量充足。除南方特有作物外,楚人歷來與中原多有來往,故種有北方作物稷、粟、黍、豆、菽等。《招魂》曰:“稻粢穱麥,挐黃粱些。”這里就提到了稻谷、粟米、麥子、黃粱多種糧食,《大招》又云“五谷六初”,可見楚人祭祀五谷具備,糧食種類豐富且精致。
(三)肉食
楚國地處云夢澤,森林廣布,水網密集,漁獵便利。在《楚辭·招魂》和《楚辭·大招》中,提到的肉食共有二十二種,不僅有人類馴養的牛、羊、豬、雞、狗等,還有十二種野味菜肴,包括鴻、鵲、鵑、鱉、豺等。品類豐富,描寫詳細,如“內鸧鴿鵠,味豺羹只”“鮮蠵甘雞,和楚酪只”“醢豚苦狗,膾苴蒪只”“炙鴰烝鳧,煔鶉敶只”“煎鰿膗雀,遽爽存只”。楚人祭祀的肉食以野味為主,是因為野味來之不易,往往是人們以性命相拼所得,極其珍貴,被視為珍寶。而將這些珍貴野味作為犧牲祭品來祭奠神靈,最能表現楚人祭祀的虔誠,以及對獲得神靈歡心的熱切期盼。除野味之外,人們還能看出,魚類等水產品也是楚人主要的祭祀食物。因為楚國地處長江流域,河網湖泊交織,淡水魚鮮資源豐富。在祭祀神靈時,講究選用本地的物產,因此楚國祭祀獻魚也就成了理所當然的事情。
祭品除了種類豐富,還精美非常。例如,“蕙肴蒸兮蘭藉”講的是在佳肴上加入蘭花同蒸,使菜品不僅味美還香氣馥郁。楚人相信精心的準備能換來神明味覺上的歡愉,達到“娛神”的目的。
二、容色媚神
除了供奉精美祭品,楚人還通過裝扮自己、裝扮祭壇使神“悅目”。“靈偃蹇兮姣服”,女巫是溝通世俗世界與神明世界的渠道,也是降神的載體。在祭祀前,女巫都要沐浴更衣,齋戒幾日,佩戴香花香草“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洗去身上污穢,使香草的神圣感轉到自己身上。楚人還相信神明通過香味識別祭品,香氣襲人的香草能夠招徠神明,更方便人與神明溝通,為神明附身做準備。
楚人認為香草的香氣使人愉悅興奮,故認為香氣也能使神興奮,便以香草作為娛神的手段。《九歌》中的祭祀場面總是隨處可見香草的蹤跡,彌漫著香草的氣息。為迎接神靈的到來,屈原精心營造了一個個香氣四溢的環境。例如,《湘夫人》“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建芳馨兮廡門”,從庭外到門廊、屋頂、室內都用香草裝飾,去除邪祟凈化環境,從而“九嶷繽兮并迎,靈之來兮如云”。屈原更是將香草視作優良品行、高潔人格的象征,故常將“香草美人”作為抒寫對象。《離騷》中有“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湘君》中有“薜荔柏兮蕙綢,蓀橈兮蘭旌”,《九歌·禮魂》中有“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禮魂》是《九歌》的最后一篇,被視為送神曲,這里提到香草表達了對神明的歌頌和祝愿。
三、歌舞娛神
俗話說,巫舞不分。王國維在《宋元戲曲考》中提出,“古代之巫,實以歌舞為職,以樂神人者也”。楚人重巫好歌舞,《楚辭》中《九歌》對祭祀樂舞有詳細描述。部分學者將其定義為祭祀詩,相傳它源于楚地流傳的民間祭歌,經屈原“更定其詞,去其太甚”加工而成,共有十一篇,除《國殤》為祭人魂外,每篇祭一神,如《云中君》云神、《少司命》生產子嗣之神、《山鬼》山神等。《禮魂》一篇例外,是禮成時的送神曲。這11篇為一個完整的祭祀體系,神由巫覡帶著面具角色扮演,他們穿著華服、佩戴香氣馥郁的蘭草,手持瓊枝在鼓樂聲中踩著節拍起舞禱告:“緪瑟兮交鼓,蕭鐘兮瑤簴;鳴篪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翾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敝日。”整個祭祀場面一片歌舞歡騰。楚人相信神靈與人一樣,對精神文化精神愉悅有追求,所以巫覡們用悅耳動聽的音樂與奔放熱情的舞姿給予神靈極大的視聽享受。
在祭祀中,還有一個重要環節便是降神。楚人相信通過巫舞與巫術能夠使神靈附體,女巫往往在降神階段會失去自主意識,進入狂亂狀態,不受控制地抽搐舞動,念念有詞,甚至釋放巫法。此時,女巫已被神靈附體,她的指示便是神示,神靈通過她觀覽人間,得知百姓愿望。降神活動是百姓最期待的,他們期望借此達到與神交流、祈福散福的目的。
四、情愛歆神
人樂男女,重聲色,楚人也在祭祀活動中加入情愛成分娛樂誘惑神靈。梅瓊林認為,“巫歌原型結構中潛存著的濃厚的性戀關系的內容,儲存著生動的巫風性人神戀的原始模式”。在《九歌》這場祭祀樂舞中,其以歌舞音樂為外在表現形式,而以人神戀愛、神神戀愛為主要內容。
聞一多更是將《九歌》中《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山鬼》等八篇兩兩配對,視為戀歌。其中,“二湘”兩篇情感最為突出,《湘君》是女巫以湘夫人的口吻唱出等待湘君而不至“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為此感到悲傷的故事。《湘夫人》則是男覡以湘君的立場對湘夫人暢訴幽情。除“二湘”外,《河伯》全詩也是難逃一個“情”字,“與女游兮九河,沖風起兮水揚波”“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與之相配的《山鬼》亦是“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閑”,洋溢著濃濃的情愛氛圍。
古代的祭祀有多種規格形式,與此對應的有不同目的、用途,如祭祖、敬山水風雨等自然神、祈福、婚喪嫁娶等。而現代,除了古時楚地遺存的少數民族依然保留祭祀的多數內涵。學者吳玉春指出,“近代苗族的‘構相仙巫師每祭鬼送神時,頭戴草竹帽,肩挎黑白紗線,一手持茅草,一手持長刀。擊鼓敲竹,邊念邊唱。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酷似王逸所說的楚國南鄖之風”。
目前,漢族對《楚辭》中的祭祀風俗傳承有限,多保存于喪葬風俗中。在湖南等地,人去世后喪家會請民間藝人唱喪歌,俗稱“唱夜歌子”,歌詞大多歌頌死者美德、描述當地山川風物等,常常通宵達旦,以示熱鬧,與楚人歌舞娛神有異曲同工之妙。另外,還會請人做道場,供奉諸位天神以及目連尊者等地神的排位,或殺豬宰牛祭祀,為逝者洗脫冤孽,超度亡靈,與楚人犧牲祭神別無二致。
今人對古時楚人祭祀風俗的傳承還體現在“招魂”一事上,古時人初死,生人要上屋頂面向各方為死者招魂,稱為“復”。期待死者魂歸而醒,復而不醒,再辦理喪事。《楚辭》錄有《招魂》篇,其中有“工祝招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等語,可知當時人們普遍相信魂是可以“歸”的。現代人雖不相信招魂能使人復活,但在祭祀活動中,往往會請做法先生召回亡魂,希望讓其接受后人對其的供奉,并觀看整個祭祀過程了解后人對其的尊敬和不舍。
《楚辭》作為南方文化的瑰寶,它不僅思想深邃、想象奇特、情感豐富、文采斐然,獨創浪漫“楚辭體”,成為后世創作的楷模,同時也蘊含著豐厚的歷史傳說、風俗習尚,是后人研究楚文化的鮮活教材。文學源于生活,是現實生活的客觀反映,《楚辭》從衣食住行、婚喪嫁娶各個方面記錄著當時人們的生活,讓人們看到了一個從社會文化到音樂舞蹈各方面都暈染著楚地特有的祭祀文化特色的楚國,這種浪漫神秘的文化特色讓楚文化得以與樸實中庸的中原文化在歷史的長河中交相輝映,對后世影響深遠。
(長江大學文學院)
作者簡介:張健芳(1998-),女,湖南長沙人,本科,研究方向:古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