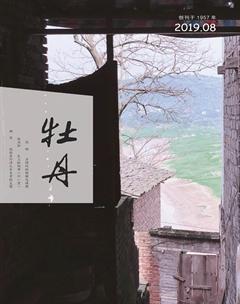語文教育資料改編的尺度問題
作家出版社2019年版《讀故事 學作文》之《標點和空格》堪稱“魯迅與標點”軼聞的“最佳”改編,而軼聞之最早出處是孔另境的《我的記憶》,方圓等的改編存在不合史實、違背常識、偏離邏輯和模糊真相等問題。
關鍵詞“魯迅”與關鍵詞“標點符號版”在某些語文教育資料中發生疊加。一則關于“魯迅與標點”的軼聞就廣泛分布在眾多中小學語文教育資料之中。對此,已有論者指出其在中學生刊物如《今日中學生》,專業刊物如《咬文嚼字》以及主打“故事”“趣談”“趣話”的著作中的全方位傳播。這則佚文正好可以“拿來”探討語文教育資料改編的尺度問題。
一、“魯迅與標點”軼聞之“最佳”改編
就筆者目力所及,方圓、曹燦、張嵐主編的四冊《讀故事 學作文》之《標點和空格》一文,堪稱“魯迅與標點”軼聞的“最佳”改編,刊發在“修改修辭卷”第10-11頁,由作家出版社2019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全文節錄如下:
“1926年秋天,魯迅先生為了躲避國民黨反動派的政治迫害,由上海虹口區輾轉流落到廈門大學……在教學之余,他做起了翻譯小說的工作……十五萬字的書稿加上標點符號,按當時的翻譯價格,得三百多塊大洋的稿酬呢……之后的幾天,魯迅先生又把稿子重新抄了一遍,寄給了書局……先生對書局的人笑了笑:“我說嘛,標點和空格還是有用的!”魯迅先生的這一舉動,令書局老板頗為尷尬,很快,他重新給先生核算了稿費寄了過來。新稿酬是三百五十塊大洋……”
稱“最佳”改編的原因在于其篇幅達到728字(含標點),目前所見在長度上無出其右者;而且背景清楚明白,情節巧妙曲折,細節生動“準確”,情感豐富飽滿。此“最佳”改編還有另外兩個版本,一是方圓編《小學生開啟作文思路必讀的故事》(石油工業出版社2007年版)第199-200頁之《標點與空格》,一是張載軍等編《讀故事 學作文》(濟南明天出版社2005年版)第220-221頁之《標點與空格》。
2005年版與2007年版之間僅有13處不同:4處替換(“先生”替換為“魯迅”),4處刪除和5處修改;2019年版與2007年版之間則有7處替換(漢字替換阿拉伯數字),8處刪除,7處文字修改,2處文字增加與2處標點調整。這些改動見證了編者十余年不斷優化的努力,也造就了2019年版之“最佳”地位。編者之《敬啟》有云,編寫過程中“查閱了大量的相關資料”,這則軼聞資料情況如何?出處何在?
二、“魯迅與標點”軼聞溯源小考
要追溯“魯迅與標點”軼聞的源頭,首先想到的自然是魯迅著述,想到《魯迅全集》。但檢索新舊諸版《魯迅全集》,都沒有相關信息。《魯迅全集》之外,最早記錄“魯迅與標點”軼聞的文獻見于何處?檢索資料筆記,一則民國時期的史料浮出水面——
周先生聽我們談后微微一笑,他說:“那也有方法的,我自己就碰到過,但我也向他們搗亂過一下。有次一家書坊來要我譯書,他們開來的條件其中一條是要照實字計算的,后來我給他們翻譯了,我從頭至尾把它們連接起來,每張稿紙寫得滿滿的,不漏空一個字,因此章和節自然看不出了,而且我還不加一個標點符號。送去之后他們來信告訴我不能印,希望我分一分段落,加一加標點,我回信說要分段加標點是得另算錢的,可見空格自亦有用處,標點也有用處的,中國人卻連這點常識都沒有。”
此材料出自茅盾小舅子孔另境的散文《我的記憶》,初刊上海民國期刊《光明》1936年第11期。這應該是已知“魯迅與標點”軼聞之最早源頭,其中直接引用魯迅發言的202字(含標點)就是軼聞的本來面目。前引凌孟華論文也持此說,并就孔另境回憶的可靠性問題有過簡要分析,感興趣者可自行參閱。
三、幾點商榷意見與關于語文教育資料改編尺度的思考
對讀“魯迅與標點”軼聞之孔另境“原始”版與方圓之“最佳”改編版,人們就會發現二者差異巨大,這引發了筆者關于語文教育資料改編尺度的思考。改編的尺度雖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遵從基本的歷史真實與文化邏輯應該是最基本的原則和共識。以此衡量“最佳”改編,人們就會發現其存在不少問題,筆者在此提出幾點意見與方圓老師商榷。
(一)廈門大學時期魯迅“生活很窘迫”嗎?
翻檢《魯迅日記》,1926年9至12月都記錄有收到“薪水泉四百”,次年1月亦然,既勝過之前北京教育部任職并多校兼課的收入,又超出之后中山大學任教的280元薪金,既遠遠超過普通雇工的工錢,又高于當時名流如吳宓的340元月薪。因此,擁有穩定且不菲的收入,魯迅生活很難說“窘迫”。
(二)廈門大學時期魯迅寓所“狹小潮濕”嗎?
魯迅書信《致許廣平》(1926年9月4日)及時匯報“所以我暫時住在一間很大的三層樓上”,二十余天后,魯迅搬家,又在26日鴻雁傳書“至于我今天所搬的房,卻比先前靜多了,房子頗大,是在樓上”。魯迅《致韋素園》(1926年9月16日)更明確告知友生“此地秋冬并不潮濕”。這些書信都可以作證魯迅其時的寓所雖然不及八道灣十一號寬敞,但并不狹小,也不潮濕。
(三)大先生翻譯過十五萬字的“英國小說”嗎?
核查《魯迅全集》《魯迅譯文全集》等資料,可知魯迅作為翻譯家的翻譯范圍雖然涵蓋15個國家,涉及“一百一十人的二百四十四種作品”,但真正的英國作品唯有與周作人合譯的《紅星佚史》之十余節譯歌。
同時,已發現的魯迅譯小說接近或超過十五萬字的,僅《十月》《毀滅》《死魂靈》等幾種,都是蘇俄作品,均完成于1930年以后。因此,說魯迅翻譯十五萬字的“英國小說”,改編者可能缺乏魯迅研究常識。“由上海虹口區輾轉流落到廈門大學”也是如此。
(四)大先生有可能“把稿子重新抄了一遍”嗎?
十五萬字的稿子,按照正常抄寫速度,以每分鐘約25字核算,需要花費約6000分鐘,約100小時;就算把速度提高一倍,達到每分鐘50字,也需要3000分鐘,50小時!魯迅是“把別人喝咖啡的時間都用在工作上”的,會有這樣的閑工夫嗎?也就是說,“重新抄了一遍”只有在稿子不長的情況下才可能出現,當篇幅放大到十五萬字,就幾乎沒有可能。
(五)稿費金額“三百五十塊大洋”經得起推敲嗎?
廈門大學時期,《魯迅日記》中的稿費記錄不多,沒有收到稿酬“三百五十塊大洋”的記錄。同時,按照“最佳”改編之邏輯,十五萬字稿子,按實字計算,稿費二百四十元,可推算出千字稿酬為一元六角;書局老板重新核算后的稿費總額三百五十元,可折算出加上標點和空格后,字數已超過二十一萬字;二者作差,可知標點和空格有六萬余字,大約每隔三字就有一個標點或空格,這顯然是不可能的。毫無疑問,在稿費金額計算方面,改編者存在邏輯矛盾,難以自圓其說。
當然,語文教育資料在編寫、處理“魯迅與標點”軼聞時反映出來的諸多問題可能不僅是編寫者的個別問題,而是中小學語文教育資料編寫界的共性問題,包括不合史實、違背常識、偏離邏輯、模糊真相、經不起考證以及耐不住推敲等。如何努力避免部分語文教育資料編寫精彩有余而嚴謹不足的弊端,給學生讀者以言傳身教,對培養他們的科學精神、謹嚴意識與規范觀念具有重要意義,是值得人們進一步思考和研究的學術課題。筆者的分析還比較粗淺,如有冒犯或不當之處,懇請方圓老師海涵并批評指正。
(重慶日報報業集團)
作者簡介:田娟(1978-),女,重慶人,本科,記者,研究方向:編輯出版學、中國現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