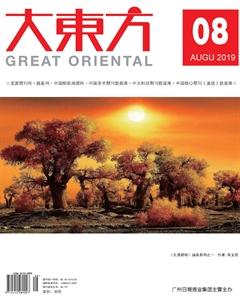穿越千年的竊竊“絲”語
宋佳
摘 要:我們沉迷于兩千多年前的藝術,驚嘆于古人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從“T”形帛畫的身上我們了解到了那個時代的思想、文化以及生活,它是“過去”和“現在”的一次世紀對話。本篇從“T”形帛畫著手,分析了漢朝的文化思想,以及帛畫在現代的影響和發展。它銘記的是中華民族的文明和精神信仰,它身上的故事和意義值得我們不斷地去研究探索。
關鍵詞:帛畫;神仙思想;現代帛畫;穆益林;古帛今傳
人死之后會去哪里?
從古至今,這是每個人、每個時期都在不斷探索的問題。“生死”不僅是與人相伴始終的現實問題,也是一個吸引古往今來無數哲人智者無盡探索的哲學問題,不同的生死觀形成了對生與死的不同理解。2000多年前,當西漢王朝的轪侯家為死去的親人送葬的時候,無論如何也無法想到,他們這個巨大的墳冢會對后世的人們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在眾多文物中,馬王堆墓出土的“T”形帛畫,和那位穿越2000年的貴婦人一樣,令所有考古學家為之震驚。覆蓋在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內棺蓋板上的這幅帛畫,傳承著2000多年前喪葬理念和繪畫藝術的傳奇,于1972年4月25日晚上將它的神奇呈現于世人面前。
兩千年,一瞬間,永生之夢光華再現。
一、“T”型帛畫的前世記憶
墓主人生前處于漢初,統治者改變了先秦“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的繁重徭役,而實行“輕徭薄賦,休生養息”的政策,減輕人民負擔,勸課農桑,恢復經濟。休養生息政策的實施,使西漢的社會經濟得到恢復發展,穩定和鞏固了漢朝的封建統治秩序。在文化思想上,一方面先秦思想也在各個方面影響著漢代人,比如對神仙方術的追求從未停止過;另一方面,源自楚文化的影響,“T”形帛畫中所描繪的不少神畫圖像都與《楚辭》相符。這種逐漸富足的社會經濟和成熟的社會思想為這個“豪華棺槨”的呈現奠定了基礎。
在漢代,升仙思想促使了當時厚葬之風的盛行,人們都以為人死后的靈魂是不滅的。他們在覆蓋棺槨的帛畫上,描繪出靈魂升天的情景和靈魂所生活的天界仙境,以寄托渴望成仙的遐想。馬王堆出土的“T”形帛畫從繪畫內容上來看,主要表達的還是墓主人升仙的一個主題,無論是畫面中“人”與“神”的地位,還是神龍引頸飛天的姿態,都表現了當時人們對死后升仙的追求和對重生的渴望。
二、“T”型帛畫之中的思想
從古至今人們對神仙的追求和對重生的渴望從未停止過。從遠古時期人們對待死亡的模糊認識到恐懼和害怕死亡,再到創造出一系列復雜的喪葬儀式以求升天,這都取決于當時人們對天神以及靈魂存在的信仰之上。至秦漢時期,人們的墓葬儀式已發展的相當成熟,成為早期中國思想與信仰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他們看來,生與死之間是有關聯的,而這個關聯需要通過一種形式-墓葬儀式來完成。
這幅“T”形帛畫所描繪的正是人們所向往的能通天地神靈的永生之路。帛畫分為三個部分,帛畫的上方描述的是人們理想中天界的模樣:金烏低聲訴,立在扶桑樹;蟾蜍伴玉兔,廣寒宮里住;神靈燭龍,在祥云間飛舞;那里日月同輝,那里比人間更加豐富。中部為人間世界:在華蓋下面,畫的是一位老年貴夫人拄杖而立,她就是一號墓的主人辛追,對于辛追夫人的形象描繪采用的是寫實的手法,辛追夫人手持拄杖,面向西方,前有小吏迎接,后有侍從護送,相當形象的刻畫出了一位貴婦人的體態樣貌,這是畫面的中心,也是作者著力描繪的重點。中部的下端是辛追老夫人的家人,個個面色青藍,神色悲哀,仿佛在哀悼老夫人的逝去。最下部為地下部分:描繪了一個赤身裸體的地神―鯀,[1]他正托舉著大地,腳下踩踏著兩條巨大的鰲魚,傳說中鯀是大禹之父,只有鯀才能穩住興風作浪的鰲魚,制止地震山崩的發生,從而鎮壓地府中的妖魔不去侵擾主人安靜的亡靈。
三、帛畫的今生價值
斯人已逝,但其留給后人的文化、藝術等寶藏都將隨著歷史的向前而源遠流長。在漢代帛畫中,馬王堆帛畫不僅數量多,水平高,形制完備,而且年代最早。同時,馬王堆漢墓,在現已發掘的所有帛畫墓(包括楚帛畫墓)和所有西漢初墓中,又是唯一具體下葬年代清楚,死者見于史書記載的墓葬。[2]馬王堆T形帛畫有著很高的藝術價值和歷史文化價值,是當之無愧的國寶。
馬克思說:“一切神話,都是在想象中和通過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3]。這些想象不僅是古人的精神寄托,同樣也影響著現代人的思想文化,既是過去的,也是現代的,更將是未來的。俄國的美學家車爾尼雪夫斯基說過“每一代的美都是而且是為那一代而存在,它毫不破壞和諧,毫不違反那一代美的要求;當美與那一代一同消逝的時候,在下一代就將會又有它自己的美,誰也不會有所抱怨的。”[4]雖然帛畫在現代的喪葬儀式中已經很少出現,但是從帛畫的出現至今,卻一直影響著不同領域、不同時期的文化、思想和藝術創作。
“帛畫是我們民族的瑰寶,曾豎起古代中國畫藝術的巔峰。這祖先留給我們的優秀文化遺產,是你的,是我的,是我們大家的,我只不過為帛畫在今天重新崛起出了一些微薄之力,振興帛畫,讓帛畫重展輝煌是我們共同的責任。從世界的角度看,帛畫也是世界文明的財富,是人類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帛畫應該成為國際的繪畫語種讓大家一起來畫,但必須讓世界知道帛畫是中國創造的,這是帛畫申遺的目的之一。”—穆益林。作為中國當代帛畫的領航者,穆藝林先生曾經說過:“如果把中國畫的歷史比作一條奔流的長河,3000多年的中國畫從源頭到中游,一半以上都屬于帛畫的歷史;一半以下出現的一個支流便是以宣紙為材料的中國畫。”穆教授經過三十多年的研究和探索,利用帛的透疊、折光性能創造出神奇的會產生圖形和色彩變化的現代帛畫藝術,舉起了傳承、發展和弘揚中國帛畫的旗幟。這種在絹、紡、紗、縐、綾等真絲平面織物上作的畫,不僅是中國畫的起源,更是代表著中國民族之繪畫的極高成就。在當代,這個在古代名聲顯赫的繪畫技藝,雖然已被大多數人遺忘,但是它所傳遞給世人的民族精神、神奇的藝術魅力仍然在感染著我們,去追尋和傾聽帛畫從三千年前走來的腳步聲。
參考文獻
[1]《山海經·海內經》[M]:“禹鯀是始布土,均定九州”.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
[2]劉曉路《馬王堆帛畫再認識:論其楚藝術性格并釋存疑》[J].《文藝研究》1992年03期.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第二卷.第11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4]〔俄〕車爾尼雪夫斯基《生活與美學》[M]第125頁.
(作者單位:天津工業大學藝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