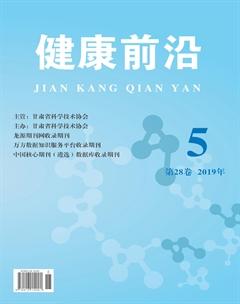負性生活事件與心理健康:心理韌性的作用機制
包廣華
摘要:目的:選取150名農村留守兒童為研究被試,探討心理韌性、負性生活事件及心理健康的關系。結果表明:(1)心理韌性和負性生活事件顯著負相關(r=-0.31,p<0.01),心理韌性和心理健康顯著正相關(r=0.46,p<0.01),負性生活事件和心理健康也呈現顯著負相關(r=-0.42,p<0.01);(2)心理韌性在負性生活事件和心理健康中有部分中介作用,效應為27.2%。結論:負性生活事件對農村留守兒童的心理健康具有消極作用,并且心理韌性在負性生活事件與心理健康之間起到中介作用。
關鍵詞:留守兒童;心理韌性;負性生活事件;心理健康;
一、引言
近20年來,我國青少年心理健康研究由于受到積極心理學思潮的影響,由消極心理的研究轉變到積極心理的研究,著名心理學家Seligman認為不應該用消極的態度去對待個體的發展潛能,而是應該用欣賞、積極、開放的態度去對待,進而激起個體積極的力量和品質,通過各種反思,認識到提高人的心理素質是心理健康研究的基本目標,促進人的心理和諧是心理健康研究的基本價值追求,也是當前心理健康研究的基本方向[1]。心理韌性(Resilience)是積極心理學領域全新的研究熱點之一,是個人面對生活逆境、創傷、悲劇、威脅或其他生活重大壓力時的良好適應,也是意味著面對生活壓力和挫折的“反彈能力”[2],也有譯者翻譯為復原力,心理彈性等[3]。在積極心理學思潮的影響下,從心理潛能的視角對心理韌性的內涵予以新的詮釋,提出促進韌性潛能實現的策略,注重生物學影響因素,擴大研究領域、實施干預研究面[4],當前對心理韌性的研究也大部分放在能夠提高個體心理韌性的個體特征和環境因素。
負性生活事件是指個體在社會生活過程中所經歷的各種變動,它會使個體產生不安、消沉、焦慮等情緒情感體驗,影響個體的情緒向消極方面發展。負性生活事件是導致個體心理問題的一個重要因素。王秀希等人(2010)的研究表明:提高大學生復原力水平可以減少負性生活事件對大學生的不良影響,進而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5]。也有研究表明大學畢業生的心理彈性對心理健康的預測效應是通過積極情緒這一中介變量實現的[6]。在面臨高負性生活事件的被試中并非所有都表現出較低的心理健康水平,甚至還有些非常優秀,他們表現出了很強的心理韌性。對于心理韌性的在負性生活事件應對中起什么作用,如何起作用還沒有統一的定論[7]。
我國正處于快速的社會轉型發展階段,經濟發展,城鎮化的迅猛推進,農村留守兒童作為一個特殊群體不斷的受到了公眾的關注和社會的關心,對農村留守兒童的關愛也引起了全社會的共鳴,其心理健康問題更是備受社會關注的話題。留守兒童指的是父母雙方或一方將孩子留在戶籍所在地而自己外出打工時間超過半年,破事孩子和自己分開居住,生活的,年齡在18歲及其以下的兒童。隨著社會的發展,農村留守兒童面臨的負性生活事件也相對以往要多,如情感喪失、感情陪伴、生活適應、同伴關系等一系列的問題,很可能產生自卑懦弱、行為孤僻、情感冷漠等方面的問題。有研究表明留守兒童在人際焦慮,學習焦慮,自責傾向,以及心理問題的檢出率均高出非留守兒童。本研究以農村留守兒童為研究對象,探究心理韌性在負性生活事件與心理健康之間的中介效應,以期考察是否能通過提高農村留守兒童的心理韌性水平來減少其心理健康水平受生活中的負性事件的影響,從而提高農村留守兒童的發展歷程中的心理健康水平。
二、方法
1.被試
選取廣西壯族自治區6個鄉鎮農村的留守兒童為被試,出事發放材料300份,刪除廢卷并剔除其中的極端數據,最后有效分析數據285人。其中男生163人,女生122人,平均年齡為9.8歲。
2.測量工具
(1)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8]。由27項可能給青少年帶來心理反應的負性生活事件構成。受測者根據自己最近3個月的實際情況進行自評,每個條目進行6級評分,包括6個因子:人際關系、學習壓力、受懲罰、親友與財產喪失、健康與適應問題及其他方面。
(2)一般健康問卷(GHQ-20)[9]。包括自我肯定、憂郁、焦慮3個維度,采用0~1記分法。具有三個維度自我肯定維度、憂郁維度、焦慮維度。根據Diener的觀點和本研究的目的,把自我肯定維度的總分作為積極心理的指標,分數越高,說明被試的心理越健康;將憂郁和焦慮2個維度的總分之和作為消極心理的指標,分數越高,說明心理問題越嚴重。
(3)青少年心理韌性量表[10]。共有5個維度,目標專注、情緒控制、積極認知分、人際協助、家庭支持,共27個項目,采用5點計分,分數越高說明心理韌性水平越好。
3.統計分析 采用 SPSS 18.0 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
三、結果
1.心理韌性、負性生活事件、心理健康的相關分析
對各量表的總分做相關分析,顯示留守兒童的心理韌性和負性生活事件顯著負相關(r=-0.31,p<0.01),心理韌性和心理健康顯著正相關(r=0.46,p<0.01),負性生活事件和心理健康呈現顯著負相關(r=-0.42,p<0.01)。
2.心理韌性、負性生活事件、心理健康的關系
進一步考察留守兒童的心理韌性、負性生活事件和心理健康之間的關系,根據溫忠麟等人提出的對中介效應的檢驗方法[11]以及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將負性生活事件作為自變量,心理韌性作為中介變量,心理健康作為因變量進行分析。負性生活事件對心理健康的回歸效應為-0.41(t=-8.39<-1.96,p<0.05)。進一步進行中介效應分析,由圖3可知,負性生活事件對心理健康的直接效應為-0.30(t=-6.31<-1.96,p<0.05),表明負性生活事件對心理健康的主效應顯著,即受負性生活事件影響越大,心理健康水平越低。負性生活事件對心理韌性的標準化路徑系數為-0.31(t=-5.97<-1.96,p<0.05),心理韌性對心理健康的標準化路徑系數為0.36(t=7.45>1.96,p<0.05),最后對心理韌性的中介效應檢驗發現,心理韌性的中介效應顯著,即心理韌性在負性生活事件和心理健康中有部分中介效應,其在總效應中的比例為27.2%。
上述結果表明:一方面,負性生活事件對心理健康有直接負效應,即個體受到負性生活事件的影響越大,其心理健康水平受其影響而具有一定程度降低。另一方面,負性生活事件通過心理韌性對心理健康有間接負效應,即個體受負性生活事件的影響能夠反向預測心理韌性的水平,而心理韌性水平能夠正向預測個體心理健康水平。而心理韌性的在負性生活事件與心理健康之間的中介效應在總效應中的所占的比例為27.2%。這說明,心理韌性并不是負性生活事件影響心理健康的主要途徑,但也占一定的比例,因而,提高學生的心理韌性水平仍能從一定程度上降低負性生活事件對心理健康造成的負面影響。
四、討論
國內研究表明,在農村留守兒童中,隨著年齡的增加,其心理健康問題就越凸顯[12],農村留守兒童作為特殊群體,并且青少年時期是思維的自我中心以及自我熱衷是這個時期的重要特點,“心理延緩償付期”的獨處愿望以及平衡友誼的各種矛盾[13]。同樣這樣的特點將會為他們帶來相關的負性生活事件,如家庭的、朋友的、自我的等一系列事件,這些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的影響都起著重要影響。研究表明在過去30年中,青少年的自殺率已經翻了三倍,25%-40%的女孩和20%-35%的男孩在青春期有過短暫的抑郁體驗[13],因此需要更多對農村留守兒童的心理健康的研究來指導實踐工作。
Rutter(1990)在對許多經驗性文獻歸納總結后提出了心理韌性發展作用機制之一是減少負性事件的消極連鎖反應 [14]。在本研究中,發現心理韌性越高則負性生活事件的影響則越低,這一結果支持了Rutter的觀點。此外,本研究對與心理韌性、負性生活事件與心理健康的相關分析顯示出心理韌性的水平越高則心理健康水平越高,而受到負性生活事件的影響就越小,這一點與王秀希等人的以大學生為被試的結果相一致。而在中介分析結果也與王秀希等人的結果一致,均為個體遭遇負性生活事件的數量及影響程度負向預測個體的心理健康水平,心理韌性水平正向預測心理健康水平。這表明,農村留守兒童群體與大學生群體的心理健康水平在受負性生活事件和心理韌性這兩者的影響上具有類似的機制。而我們的研究還表明,負性生活事件的影響程度負向預測心理韌性水平。個體受到負性生活事件的影響的程度高則可能預示著個體的心理韌性水平越低,也許可以換句話說,當個體處于高的心理韌性水平時,其受到負性生活事件的影響程度會更低一些,從而降低了負性生活事件對心理健康的影響。
心理韌性所測量的是個體目標專注、情緒控制、積極認知、家庭支持、人際協助這幾個方面的情況。心理韌性水平高的個體可能在生活中得到更多的家庭支持和人際協助,他們可能具有更多的社會支持的力量,而社會支持可以提高人們面對壓力時在心理及生理上的調試能力,因而,高心理韌性著擁有的社會支持力量可能是他們成功應對負性生活事件的重要能量源泉。此外,相同的刺激經過不同的認知加工會激發不同的情緒,高心理韌性者的積極認知可能使他們對負性刺激的解釋更多地朝向積極的方面,從而減少了負性情緒的產生或強度,減輕負性情緒對他們的心理健康的影響。因此對心理韌性的訓練有助于促進積極的心理健康。
參考文獻:
[1] 陳良,張大均. 近 20 年我國青少年心理健康研究的進展與走向[J]. 高等教育研究,2009(11):74-79.
[2] American Psychology Association. The road to resilience:what is resilience[J]. 2010-12-20]. Http://www. Spa. Org/Helpcenter/Mad-Resilience. Aspx.
[3] 胡月琴,甘怡群. 青少年心理韌性量表的編制和效度驗證[J]. 心理學報,2008,40(8):902-912.
[4] 劉丹,石國興,鄭新紅. 論積極心理學視野下的心理韌性[J]. 心理學探新,2010,30(4):12-17.
[5] 王秀希,許峰,任云,等. 復原力在大學生負性生活事件與心理健康間作用機制的探討[J]. 教育與教學研究,2010,24(9):59-60.
[6] 趙晶,羅崢,王雪. 大學畢業生的心理彈性,積極情緒與心理健康的關系[J]. 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2010(9):1078-1080.
[7] 丁繼紅,徐寧吟. 父母外出務工對留守兒童健康與教育的影響[J]. 人口研究,2018(1):76-89.
[8] 劉賢臣,劉連啟,楊杰,等.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的信度效度檢驗[J]. 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1997,5(1):34-36.
[9] 李虹,梅錦榮. 測量大學生的心理健康:GHQ-20 的心理測量學指標[J]. 心理發展與教育,2002,1:75-79.
[10] 胡月琴,甘怡群. 青少年心理韌性量表的編制和效度驗證[J]. 心理學報,2008,40(8):902-912.
[11] 溫忠麟,張雷,侯杰泰,等. 中介效應檢驗程序及其應用[J]. 心理學報,2004,36(5):614-620.
[12] 張更立. 農村留守兒童孤獨感與社會適應的關系:感恩的中介作用[J]. 教育研究與實驗,2017(3):25-30.
[13] Feldman R S,蘇彥捷譯. 發展心理學:人的畢生發展[M]. 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3.
[14] 趙曉航. 父母外出務工對農村留守兒童健康的影響-基于CFPS 2012數據的實證分析[J]. 社會發展研究,2017(1):1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