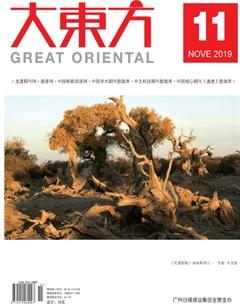從《費郵存底》看沈從文的文學觀
梁林艷
摘 要:目前,學界對沈從文的研究很多,不論是小說、散文還是評論文章,其研究成果都頗為豐盛。但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沈從文的作品部分,而忽視了那些文學性較弱的信件的研究,而正是在這些信件中,蘊含了沈從文諸多文學觀點。本文以《廢郵存底》甲輯中沈從文的信件為研究對象去探尋沈從文30年代的一些文學觀念,并結合資料分析這些文學觀念產生的原因及對當時文壇造成的影響。
關鍵詞:廢郵存底;沈從文;文學觀
沈從文在任《大公報·文藝副刊》編輯時期,極其認真負責,為改正青年作家不良寫作態度并勉勵他們堅持創作,到底寫了多少信件現在已很難完全統計。他和蕭乾后來將一部分書信整理出版,取名為《費郵存底》。《費郵存底》中收錄的書信表面上看似只是普通的回復信件,但是細細分析,便可從中看出沈從文30年代的一些文學觀念。而沈從文在回信中有意或無意提及到的一些文學觀念,不僅對其本人文學作品的創作有著重要指引,還影響了30年代北京文壇的一批作家。
一、注重文學創作中的“文體技巧”
文學作品有內容和形式兩個方面,其中形式指的是文章的語言和技巧。在中國傳統的文學之中,是非常注重技巧的,如晚唐“苦吟詩派”的代表賈島為“僧推月下門”和“僧敲月下門”中的一字之差而大費腦力。然而,文章的技巧發展到明清又走得太過極端,作品只注重形式的華美,內容和思想則顯得太過空洞。五四時期,新文學陣營的文人們對此頗多批評,如胡適就在《文學改良謅議》一文中提出“需言之有物”,另外還有“不模仿古人”、“不作無病之呻吟”,以此來強調文學內容的重要性。但是文學發展到30年代,似乎又走上了另一個極端,即只重視內容與思想,忽略文學的技巧與語言。
沈從文對這種只重內容,不重技巧的寫法大為不滿。在收錄于《廢郵存底》的第二封信《給一個寫詩的》中,他寫道:“寫詩,單是文字和思想,不加雕琢同配置,正如其材料一樣,不能稱其為藝術。要選擇材料、組織文字、處置它到恰當處,古人說的‘推‘敲那種耐煩究討,永遠可以師法。”如果說關于詩歌創作的建議,他是得益“新月派”的影響,還不能完全確定他個人對于的文章寫作中技巧的要求。那不妨再讀他《廢郵存底》中的第十三封信《給一個讀者》和第十封信《風雅與俗氣》,在這兩封信中,他不止一次得強調技巧對于文學作品的重要性。
在《給一個讀者》的一信中,關于文字的運用他寫道:“文字是作家的武器,一個人理會文字的用處比旁人淵博,善于運用文字,正是他成為作家的條件之一。沒有文字,什么是文學,詩經與山歌不同,不在思想,還在文字。”短短幾句話將文字運用對于一部作品的重要性表達得淋漓盡致。在另一封《風雅與俗氣》的信中,他通過一個朋友的例子來說明自己這一觀點:他的這個朋友在生活各處都在追求藝術、追求美,為了讓最好的理發師給自己理發寧愿花費很長的時間去等待,一個煙灰碟子的選用都要色澤形體精美等等。然而就是這個在生活中處處“講究”的朋友在談到文學時,對文學作品在辭藻與組織上的價值是大加輕視,認為好的文學作品重在有思想、有目的、有意義,而不是擺弄技巧。這種自相矛盾的觀點使沈從文非常無奈,然而擁有此種觀點的作家在當時文壇卻并不占少數,于是,為了糾正這種錯誤的文學觀,沈從文自覺的成為了了二三十年代為數不多的為“技巧伸冤”的文人中的一員。
二、不許“白相”的文學態度
沈從文曾于《大公報·文藝副刊》第九期上刊登過自己所作的《文學者的態度》一文,他在文中尖銳的諷刺了當下文壇中將寫作或當作游戲消遣或作為牟利手段的不正之風。并指出這種“白相文學”的寫作態度是非常不端正的,是對作者及讀者均極不負責的一種行為。
從《廢郵存底》收錄的沈從文的幾封信件中可以看出,他對于自己的這一文學創作態度一直反復重申。如在收錄的第十封信《風雅與俗氣》中,他對當下的幽默刊物的排斥,認為:“幽默刊物的效果,便是使作家與讀者不拘老幼兼學成貌若十分世故,仿佛個人皆很聰明、很從容,對一切惡勢力惡習氣抱著袖手旁觀的神氣。在黑暗中,他們或許也會向所謂敵人抓一把、捏一把,且知道很敏捷的躲開……但人人皆無個性、無熱情、無糊涂希望與冒險企圖、無氣魄與傻勁。照這樣下去,這個民族還能混幾年。”在此,他以舉例的手法道出了創辦和閱讀幽默刊物的國人這種游戲文學的態度對個人及民族的危害。我們都知道,以沈從文為代表的京派文人向來保持著與政治之間的距離,不為某一黨派所服務,追求藝術的無功利性,然而這并不代表京派文人就沒有社會與民族責任感。沈從文在1928年就寫了他的長篇片童話《阿麗思中國游記》來諷來中國當時黑暗的社會現實和頹敗的文化現實。之后又發表的一系列充滿湘西意蘊的小說,如《柏子》、《邊城》《虎雛》等,這些小說表面上看充滿著牧歌情調,有逃避現實之嫌,但實則是作家對當下中華民族出路的一種探尋。
三、反對“天才”與“靈感”
沈從文在成名之前曾有過一段非常艱難的生活,只有小學學歷的他十九歲獨自一人闖北京。他想進入大學讀書,但參加幾次大學入學考試,皆無疾而終;他寫了很多散文、詩歌和小說,到處投稿,結果連音信都沒有。最困難的時候,他住在又窄又霉的公寓里,甚至都吃不上一頓飽飯,但即使這樣,他都沒有放棄創作。30年代,已經名滿文壇的沈從文仍然辛勤如初,當時的他幾乎每月都有新作品問世,一年出版好幾本書,但是他的寫作速度非常之慢,每一部作品都要細細斟酌、反復修改,不使自己滿意絕不輕易出手。《邊城》不到七萬字,寫了整整半年。他作品的原稿,經常是密密麻麻改滿了所有邊頁,作品發表了,整理成單行本時,再改;單行本匯集成集時,仍要改。所以在沈從文的觀念里,他認為一部好作品的出現是來自于作家的辛勤努力,而不是流行于當時文壇的一些所謂的“天才論”和“靈感論”。
因此,在《廢郵存底》甲輯中的第七封信《致‘文藝者》中,沈從文對這種迷信“天才”與“靈感”而不加努力的創作風氣給予了十分嚴厲的批評。他認為迷信“天才”與“靈感”對文藝工作者是有害而無益的。對于那些已經成名的作家,若一昧迷信“靈感”,就會變得懶惰,總以“靈感”不來而掩飾自己的不辛勤,最終會導致作品匱乏。而對于那些未成名的作家,這兩個詞匯則有更大的壞處:“一是這作者看到其他作家的好作品,只認為這是天才所致,故而早早沒了信心,便不去寫作;二是他自己的作品不好,但因自己迷信天才,認為‘天才歷來很少為人所認識,故而不去改正;三是他將天才的作品看作‘紀念碑,認為永無其他作品可企及,便不去努力創作。”總而言之,這種迷信“天才”和“靈感”的做法只會讓作家越來越懶惰,越來越放縱自我,最終會使中國文壇走向墮落。
《費郵存底》中的信件看似普通,其中卻蘊含著沈從文獨特的文學觀念:如注重作品的文學特性,使文學與政治商業保持適當距離,成為獨立的“那一個”;反對“天才”與“靈感”,追求勤奮創作的嚴肅文學態度;探索文體技巧及其正確的使用方法等。這些文學觀點,不僅可以幫助我們更深層的解讀沈從文與以其為代表的京派文學的作品,對當代中國文壇及中國作家的創作仍具有非常好的指導意義,值得我們認真研究。
(作者單位:內蒙古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