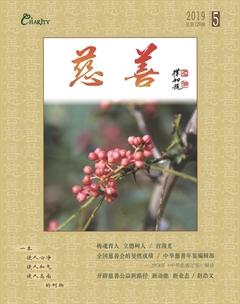二婆
趙浩義
二婆是普通的農(nóng)家婦女,無(wú)兒無(wú)女,但卻有傳統(tǒng)女性的美德。
1921年,18歲的二婆從鄰村嫁給爺爺做妾,那時(shí)候我的大家族有幾十畝地,還在縣城里開(kāi)有幾間商鋪,高祖父兄弟二人子孫滿(mǎn)堂,五十多口人一口鍋里吃飯,院落里有一棵上百年的大槐樹(shù),樹(shù)蓬碩大,遮天蔽日。故,家族字號(hào)取名“槐蔭堂”。
二婆到家第三年,大婆分娩叔父時(shí)大出血撒手人寰。當(dāng)時(shí),二婆也產(chǎn)一女?huà)耄乓暿甯笧榧撼觯涯趟辔菇o了叔父,自己的女兒卻因奶水不足、護(hù)理不周而中途夭折。
大家族中有五十多口人,每日飯菜由族里的六婆領(lǐng)著幾個(gè)婆媳操勞。聽(tīng)母親講,那時(shí)家有兩口大鍋,一口煮飯,一口炒菜,她們天不亮就下廚,天亮后要把五十多口人的飯菜端到桌上,甚是艱辛。在“炊事班”中,二婆負(fù)責(zé)劈柴、燒火,因此每日她是起床最早的,把一鍋水燒開(kāi)后,其他人才下廚切菜、下米。常年在火灶旁拉風(fēng)箱,因此她總是“滿(mǎn)面灰塵煙火色,面色蒼蒼十指黑”。
1946年,因縣城的生意衰敗家道中落,爺爺兄弟三人分了家產(chǎn)分灶吃飯。爺爺是長(zhǎng)兄,分得五畝土地和三間瓦房。分家時(shí)大家族里有一個(gè)老人叫老李,老李60多歲討飯時(shí)被大家族收留,那時(shí)還能下地干活,到分家時(shí)已80多歲,完全喪失了勞動(dòng)能力,各家都覺(jué)得是負(fù)擔(dān)不肯要,二婆可憐老李,就把老李領(lǐng)回了家,當(dāng)作自己的老人精心伺候,養(yǎng)老送終。
分家后爺爺雙目失明,父親和叔父都在上學(xué)讀書(shū),家中沒(méi)有男勞力,五畝地的農(nóng)活就全由二婆和母親操持。每年收、種莊稼時(shí),臨時(shí)雇幾個(gè)短工幫忙,地里鋤草、施肥的活計(jì)就全靠?jī)蓚€(gè)邁著“三寸金蓮”的小腳女人“汗滴禾下土”了。
新中國(guó)成立后,1951年大哥出生那年?duì)敔斎ナ馈.?dāng)時(shí)家貧如洗,買(mǎi)不起棺材安葬爺爺,父親穿著孝服四處告借,最終砍了一棵大桐樹(shù)做了口棺材才將爺爺入土安葬。爺爺走了后,父親因患肺癆從于右任創(chuàng)辦的三原中學(xué)輟學(xué)回家養(yǎng)病,叔父也上學(xué),家中仍無(wú)勞力,還是二婆和母親下地干活,終年的勞累,沉重的生計(jì)背負(fù)壓彎了她們的腰。
1953年,父親自學(xué)中醫(yī)治好了自己的病,到公社衛(wèi)生院當(dāng)醫(yī)生去了。隨后,我們兄弟姐妹5個(gè)相繼出生,好在那時(shí)農(nóng)村已先后實(shí)行了合作化、人民公社,土地劃歸集體所有。母親作為婦女勞動(dòng)力到生產(chǎn)隊(duì)出勤掙工分,二婆在家管孩子做飯。我們兄妹6人都相差一至兩歲,家里就成了幼兒園,這個(gè)哭那個(gè)鬧,把二婆忙得像陀螺一樣團(tuán)團(tuán)轉(zhuǎn)。
1958年人民公社辦食堂吃大鍋飯。那時(shí)食堂按人口打飯,每頓飯都是能照得見(jiàn)人影的稀糊湯,每人分得一大馬勺,我家8口人,全靠母親用兩個(gè)大瓦罐擔(dān)回,我們兄妹6個(gè)都是正長(zhǎng)身體的時(shí)候,飯打回來(lái),孩子們先吃,到了二婆和母親的碗里就剩了半碗稀飯了。二婆又把自己碗里的倒給了母親說(shuō):“你還要出工干活,我在家里管孩子少吃一點(diǎn)。”記得有幾次母親擔(dān)飯回家時(shí),由于饑餓暈倒,瓦罐破碎稀飯全流在了地上,一家人沒(méi)飯吃了,二婆和母親看著嗷嗷待哺的孩子,號(hào)啕大哭。哭聲驚動(dòng)了好心的生產(chǎn)隊(duì)干部,忙安排食堂做飯送來(lái),一家人才少了一頓挨餓。
上世紀(jì)六十年代初,中國(guó)農(nóng)村遇到了大饑饉,村里餓死了幾個(gè)人。二婆和母親整天到坡上去挖野菜、剝樹(shù)皮為家人充饑,挖回的野菜放在鍋里下幾粒米,飯做好后讓孩子們先吃,到了二婆和母親的碗里就所剩無(wú)幾了。如此的空腹饑餓,二婆和母親都患了浮腫病,躺在土炕上已奄奄一息了,幸好父親帶回了幾十斤出診時(shí)從山里買(mǎi)回喂牛的黑豆,二婆和母親才起死回生。
二婆終生慈悲為懷,樂(lè)善好施。她常給我們兄妹念叨:虧是福,人都不;利是害,人都愛(ài),做人要厚道,行善才能積福。村上誰(shuí)家沒(méi)糧食、斷頓了,她就從家中舀一升米、挖一碗面送過(guò)去,誰(shuí)家有人生病了,她就到衛(wèi)生院找父親要回點(diǎn)藥片送去。因此,她在村上博得了“賢惠人”的美名。記得上世紀(jì)七十年代初的一天,家門(mén)口走來(lái)一位七十多歲討飯的老太婆,突然跌倒在地,昏迷不醒,二婆忙喊來(lái)了母親將老人扶回家中炕上,喂完了一碗米粥,老人醒了,說(shuō)她已餓了三天沒(méi)吃飯,二婆和母親就照料老人在家中養(yǎng)了十幾天,直到她的兒子找來(lái)才把老人接走。
我上中學(xué)時(shí)已到了上世紀(jì)七十年代初,當(dāng)時(shí)農(nóng)村還是吃不飽飯,那時(shí)二婆才六十多歲,卻已過(guò)早地衰老,腰駝了多度,頭發(fā)白了,步履蹣跚,已干不了家務(wù)活了,母親把飯做好后,我們兄妹爭(zhēng)著打飯,母親把臉一板:“先給你婆打。”“把二婆的碗拿過(guò)來(lái)給撈上幾筷頭面條。”二婆將碗奪過(guò)來(lái)把面條倒進(jìn)鍋里:“就那點(diǎn)面條都撈給我娃吃啥,”舀了幾勺稀湯端走了。
兄妹6人中我和二婆感情最深,在我童年的記憶里,二婆的臉最慈祥,二婆的懷抱最溫暖。我忘不了二婆為這個(gè)8口之家辛苦勞作的一幕幕。1977年,我在商縣中學(xué)讀高中時(shí),學(xué)生轉(zhuǎn)了戶(hù)口吃商品糧,每周吃?xún)纱斡蜅l和油炸饃,當(dāng)我把油條、油炸饃遞到嘴邊時(shí),突然想起了二婆那菜色的臉,就把食物用報(bào)紙包起來(lái),等到周末時(shí)帶回家中,偷偷溜進(jìn)了二婆的房間拿給二婆吃。二婆吃著饃說(shuō):“一輩子沒(méi)吃過(guò)油條和油炸饃,用油炸饃,得用多少油?太好吃了。”望著二婆樂(lè)滋滋的吃相,我甚感欣慰。時(shí)間長(zhǎng)了母親問(wèn):“你咋每次回來(lái)都拿一包東西先進(jìn)你二婆的門(mén),你給你婆拿啥了?”我如實(shí)坦白。母親說(shuō):“我娃孝順,你婆為咱這個(gè)家勞累了一生。”回想起來(lái),這可能是我這一生對(duì)二婆唯一的孝順。
二婆最心疼的是叔父。上世紀(jì)五十年代,叔父念完中學(xué)后參加工作在縣水利局當(dāng)水利員,1963年在商縣三賢水庫(kù)搶險(xiǎn)救災(zāi)時(shí)落入水庫(kù),在水中泡了一夜患了風(fēng)濕性關(guān)節(jié)炎,長(zhǎng)期臥床不能行走,住了兩年醫(yī)院回到家中,由二婆和母親照料,1972年病情好轉(zhuǎn)才結(jié)婚成家,搬到縣城居住。我在縣城中學(xué)讀書(shū)周日回學(xué)校時(shí),二婆總是遞給我一個(gè)包袱讓我送到叔父家去,里面裝的無(wú)非是糧食、衣物之類(lèi)。時(shí)間長(zhǎng)了,母親就很不高興,說(shuō)我是“家賊”,把家里東西偷出去給外人。我說(shuō)那不是外人,是親叔父,母親苦笑一下:“咱家也不富裕,拿吧拿吧,幫幫也應(yīng)該。”
1975年年初,二婆突然臥床不起,我跑到了公社衛(wèi)生院叫回了父親診治,父親開(kāi)了幾副中藥讓慢慢調(diào)養(yǎng)。幾個(gè)月后還不見(jiàn)好轉(zhuǎn),我就用架子車(chē)?yán)诺娇h醫(yī)院檢查,拍了片子,做了B超,沒(méi)查出大病。我問(wèn)大夫:“沒(méi)有大病為啥病成這樣?”大夫說(shuō):“這就像一盞燈,油耗盡了,燈自然就熄了,老人的器官都衰竭了,準(zhǔn)備后事吧。”我含著淚把二婆從城里拉回家中,一家人在床前悉心照料。在二婆彌留之際,嘴里還含糊不清地喊著:“天槽、天槽(叔父的乳名),你咋不回來(lái)看我。”
1975年7月15日,二婆走完了辛苦一生最后的一程。
二婆是一根蠟燭,燃燒了自己,照亮子孫!
二婆是一只春蠶,春蠶到死絲方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