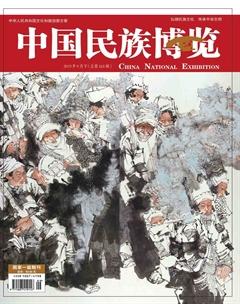新時期云南民族文化傳承保護的價值意蘊闡釋
【摘要】在新的歷史時期,云南民族文化傳承與保護的價值意蘊生成的明顯的變化主要表現為:有利于傳續少數民族特色,為云南民族文化強省建設提供基礎性條件支撐;有利于傳揚民族文化精華,為民族團結進步示范建設提供必要的文化保障;有利于民族文化資源整合,為國家西南邊疆繁榮穩定提供相應的引領示范;有利于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為精準扶貧系統推進提供科學有效的文教支撐。
【關鍵詞】云南省;民族文化傳承;民族文化保護;價值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云南具有歷久傳承的民族文化保護傳統,早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省委、省政府就明確提出了建設民族文化大省的戰略性目標。當前,隨著現代社會信息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尤其是互聯網+的變革,云南的傳統民族文化傳承保護亦迎來了新的機遇與挑戰。如何更好地傳承保護云南民族文化,既是全面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于把云南建設成為民族團結進步、邊疆繁榮穩定示范區的要求,也是我省“十三五”期間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工作。為此,特就新時期云南民族文化傳承保護的價值意蘊做系統闡釋,以期為我省相關工作的系統推進提供參考。
一、有利于傳續少數民族特色,為云南民族文化強省建設提供基礎性條件支撐
云南是一個多民族共居并存的省份,有25個少數民族世居云南,其中,15個民族為云南特有,且更有超過15個的少數民族跨境而居,既有從原始社會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基諾、布朗、傈僳”等“直過民族”,也有至今仍保留母系氏族傳統的“摩梭人”……[1]這些多元的民族構成和復雜的民族歷史,演化為云南民族文化“時序性、地域性、合容性、差異性”四位一體的特征,并逐步在地域分異上形成了以昆明為中心的“古滇文化”,以大理為中心的“南詔文化”,以西雙版納為中心的“貝葉文化”,以曲靖為中心的“爨文化”,以文山為中心的“坡芽文化”,以麗江為中心的“土司文化”。若不考慮行政區劃約束,云南的文化區又可進一步劃分為“滇中彝族主體文化區、滇南哈-彝主體文化區、滇東南壯-苗主體文化區、滇西白族主體文化區、滇西南傣-景主體文化區和滇西北藏-傈主體文化區”[2]。可見,云南不同的民族文化間既相互獨立又彼此交融,既互融共生又具有鮮明地域特色。也正是這些鮮明的文化特征,賦予了云南民族文化傳承與保護的不可替代性。對這些民族文化的傳承與保護,不僅具有直接傳承民族物質和精神財富的作用,更具有發掘民族文化精髓、延續民族文化特性、傳揚不同民族文明的價值。而作為云南民族文化構成的基本單元,對其區域內每一個少數民族優秀文化傳承與保護皆是云南文化強省建設工程的文化主體支撐。
二、有利于傳揚民族文化精華,為民族團結進步示范建設提供必要的文化保障
從云南民族關系史看,除抵御外族入侵之外(中緬邊界北段的片馬事件、中緬邊界南段的班洪事件、抗日戰爭時期的滇西保衛戰),云南基本上未爆發過大規模的民族沖突和民族矛盾。區域內總體上長期保持了各民族的團結統一和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如主體文化區內各類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的多民族文化和諧共生共榮和非單一民族自治區域(諸如“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雙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縣”等)的經濟社會平穩發展就是最好證明。簡言之,云南經濟社會的長期穩定和民族團結和睦,既是黨和政府堅強領導的結果,也是云南各民族文化特質和民族文明和諧交互、良性互動的結果。區域內無論是苗族、藏族、壯族等外遷民族,還是基諾、布朗等“直過民族”,通過大雜居、小聚居的長期發展演進,總體上與區域本土民族(含漢族)形成了包容和合的民族關系。與此同時,區域獨有的白族、傣族、景頗族、傈僳族、佤族、德昂族、阿昌族等,大多具有開放、包容、溫和、向上的民族文化特征,對待外來文化(文明)沖突時一般選擇包容的心態。從這個意義上看,對云南各少數民族文化精髓和民族文化特質的傳承與保護,一方面可以更好地保存民族血脈、凝聚民族情感、增進民族認同、創新民族發展;另一方面,也可以通過這些民族團結進步的示范,為國內其他同類民族地區的內部管理和社會治理提供文化層面的參照借鑒。
三、有利于民族文化資源整合,為國家西南邊疆繁榮穩定提供相應的引領示范
截至目前,云南區域內6000人以上的世居少數民族達到25個之多。但在這為數眾多的少數民族群體中,其民族節慶、民族服飾、民族語言、民族建筑、民族宗教、民族工藝的差異性與同一性同在,地域性與時代性共存。如在民族節慶方面,彝族、白族均有火把節,且兩者除了時間上有前后一天的差異之外,其節慶形式、節慶寓意、節慶內容大致相似;從民族建筑來看,傈僳族的“千腳落地房”、景頗族的“矮腳長屋”、拉祜族的“木掌樓”、傣族的“傣家竹樓”都具有“桿欄建筑”的特征,總體上屬于同一類型的民居建筑樣式,無外乎在不同區域內,這些建筑樣式依據地形特征、原生建材、雨量氣候、宗教信仰、民俗禮儀等進行了屋頂、建筑材料等的差異調整。顯然,對諸如此類民族文化的保護和傳承,可極大地促進各民族傳統文化資源的高效整合,一方面,為保存中華民族的完整性、多樣性提供堅實的文化主體支撐;另一方面,通過各少數民族文化資源的保護和傳承,也有利于挖掘族際融合發展、包容共生的文化內核,為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潛能的釋放提供文化資源支撐。與此同時,作為國家西南重要門戶的云南,還肩負著守衛精神領土、吸收外來文明、輻射區域發展的重要使命,而云南區域內多民族聚居的特性和傣族、佤族等民族的跨境分布、交互,相當程度上亦賦予了區域內少數民族文化傳承在拱衛邊疆文化安全上的特殊使命。因此,對云南民族文化的傳承與保護,從根本上看,還具有為國家西南邊疆繁榮穩定提供相應支撐和示范的積極功用。
四、有利于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為精準扶貧系統推進提供科學有效的文教支撐
與全國其他區域貧困人口的致貧原因不同,少數民族聚居區的貧困具有典型的代際傳遞特征。有關數據表明,大部分少數民族地區的原始經濟總量、經濟發展增量長期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貧困在區域各相關少數民族群體中形成了較強的代際復制;另一面,長期以來存在的教育、經濟、衛生等基礎設施滯后,加之自然條件、文化習俗等因素的影響,區域內對扶貧的社會排斥總體上較為明顯,在極大程度上影響了扶貧的總體效果。盡管早在本世紀初,國務院便投入各項資金37.51億元,專門對全國總人口在10萬以下的22個民族聚居的640個行政村給予重點扶持,但截至目前,云南的民族貧困問題仍舊較為嚴重。以“直過民族”為例,涉及建檔立卡的貧困人口達66.75萬之多,貧困發生率高達28.6%,高出云南省貧困發生率15.4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傈僳、拉祜、德昂等民族人均受教育年限不足6年,由于長期閉塞,“直過民族”還有近50萬人不能熟練使用“普通話”,多數“直過民族”群眾仍沿襲傳統農業的生產生活方式,[3]生產力極其低下。這些都為云南少數民族地區的貧困留下了代際因素。據扶貧的歷史經驗,教育是阻斷貧困代際傳遞,實現少數民族貧困人口精準脫貧和長效脫貧的根本舉措。而教育的精準扶貧,必須以民族文化的傳承為基礎,以民族教育水平的提升為目的。因此,對云南少數民族文化的傳承與保護,特別應在民族文化“否定之否定”的基礎上探尋少數民族持續發展進步的優秀文化基因,與民族教育形成有機對接,進而通過教育發展不斷提升少數民族人力資本質量,增強就業能力,最終實現民族貧困群體的精準脫貧和長效脫貧。
參考文獻:
[1]段從宇,甘健侯.適應、引領與超越:云南民族教育信息化建設研究[J].學術探索,2015(1):83-87.
[2]謝紅雨.云南民族文化傳承之區域教育路徑研究[D].昆明:云南師范大學,2016:4-47.
[3]云南2019年實現“直過民族”脫貧http://www.sohu.com/ a/70956735_162758.
作者簡介:段從宇(1987-),男,云南楚雄人,博士,云南師范大學 高等教育與區域發展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教育資源配置、民族文化傳承保護。
基金項目:云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基地項目“云南‘直過民族教育精準扶貧實施路徑研究”(項目編號:GD2017YB02)前期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