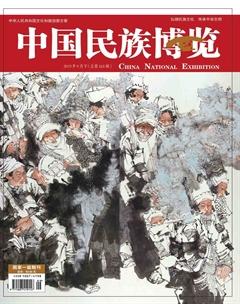傳統武術習演中書法精神的探析與思考
【摘要】在中國傳統文化體系中,武術和書法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兩者歷經漫長歲月,皆演繹出了別具一格的獨特審美特性與藝術形式,同時,兩者之間并非完全獨立,而是存在一定的聯系。本文筆者以武術演練為研究對象,通過比較兩者共同的文化起源、審美的互通性等,探索武術習演中的書法精神,讓武術習練者能更好地理解武術動作內涵,熟練編排武術套路,提升習演美感,激發創造力,并進一步完善學習者性情、人格、道德,提升其精神境界。
【關鍵詞】武術;書法精神;探索;創新
【中圖分類號】J613.3 【文獻標識碼】A
現今,我國不斷創新和發展中國文化,使得我國文化軟實力加速提升。而武術與書法作為中國文化寶庫中最具代表性與影響力的文化,開始在世界各地流行起來并深受各國人們青睞,但是兩者之間的聯系尚未明確。因此,筆者擬基于傳統文化書法理論,對書法藝術的結構特征、藝術美學以及精神內涵進行深入剖析,并將其融入武術演練中,以緩解兩者矛盾,進一步推動武術習演的發展和創新。
一、武術與書法的思想同源關系
(一)“天人合一”的共同哲學思想基礎
最早,“天人合一”的思想概念是道家思想哲學體系中被提到的,并由此構建了中華傳統文化的思想主體。人相比宇宙自然而言僅僅是一小天地,但是從本質上看,兩者并未剝離,而是相互融合的,所有人事只要不違背自然規律,就能實現和諧相處目的。天人合一不僅是一種思想,而且是一種狀態。
無論是商周時期的甲骨文中的象形文字,還是青銅器上的鐘鼎文,書法藝術都十分強調自然,都是人們通過對自然物象的直觀理解然后轉換變化出來的字體。大自然中蘊含大量文字精華,書法家筆下以粗獷、流暢、狂放、雄壯、優雅、剛勁、飄逸等線條構成的每一個字都體現了大自然的姿態美、形式美、韻律美。這些外化使筆下的字構成更為生機盎然的生命個體,抒發情志,體現了書法中“天人合一”的內涵。
人類的搏斗行為以及對自然萬象體察的與活動實踐是武術蘊含的技擊意識的動作重要來源。模仿自然界中各種事物的姿態、動作、神情,結合人體運動的規律和實際的搏擊行為,創造和編改而成,如鶴拳、虎拳、猴拳、螳螂拳等都是取法自然。中國武術“天人合一”主要表現在其把觀察到的事物與現象通過主觀的解讀分析,演變成組構武術的各種動作和技術。武術技術歷經百年的演變是在總結和提煉直覺的感性思維的基礎上形成的。中國武術正是受這種文化精神的影響而得以表現出內涵深刻、百花齊放、逸趣橫生特性。
(二)“辯證思維”對武術與書法的思維認識的構建
中國哲學最核心的內容即為辯證思維,這種實現也體現在陰陽統一對立上。中國文化的各個領域都有“陰陽”思想的滲透,武術與書法也不例外。
在中國書法藝術的發展過程中,對立統一思想起到關鍵作用,其演變或生化形成的藝術辯證法生動而豐富,是整個書法藝術的精髓和靈魂所在,并衍生出了包括呼應、方圓、繁簡、濃淡、虛實、干濕、開合、松緊、賓主、疏密、奇正、巧拙等中國書法的藝術審美辯證法。只有正確處理統一與對立并存的矛盾關系,讓陰陽互動,才能實現和諧至善。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在武術中的陰陽對立統一思想的具體表現,比如太極拳體現陰陽思想,八卦掌、形意拳也都以五行思想為指導,像剛柔、動靜、虛實、開合、俯仰、吞吐、進退、收放、攻防等都體現了陰陽對立統一的運動規律。盡管不同門派存在不同的攻防套路,但是都體現了攻防矛盾相互轉變的規律,所謂“以柔制剛”“以快制慢”“以靜制動”等皆是遵循陰陽矛盾運動的基本原理派生出來的技擊原理。
書法與武術正是基于這種復雜的辯證關系,才創作出了意蘊深厚、生動美妙、千姿百態的藝術形象,縱觀中國武術與書法,始終貫穿著陰陽對立統一觀念,以達到陰陽平衡的要求。
二、書法精神在武術習演中的體現和比較
(一)形式審美的講究
美的創造依賴于藝術這一特殊手段或技巧,其最重要的表現形式主要體現在形式美上。盡管在美的具體表現方式上書法與武術不盡相同,但在形式美方面,兩者存在著不少相似之處,例如呼應、開合、松緊、平衡等。另外,在結構上,書法用筆變化與武術動作分解都遵守著平衡的法則。平衡也曾出現在歷代書論中,即“四平八穩”。具體到武術中,平衡法則要求要五體勻稱,每個動作勢式都要顧及空間的上下高低、前后左右,正如字體的骨架結構,輕重有致、分布均衡、重心平穩。在武術演練與書法作品中存在奇與正的關系,各因素間相互依存。舉例來講,醉拳中的步伐以及平衡動作等都是通過對比奇與正來打破平衡,使得動作被賦予韻律節奏,表現得更加生動、活力、有趣。在書法與武術中,呼應對比集中體現了多樣統一規律。多樣性通過對比產生,變化中的統一則由呼應求得。對比讓韻律變化得以產生, 回避了精神審美和感官上的疲倦,如武術演練中的松和緊、動和靜、進和退、剛和柔、虛和實、收和放、高和低、起和落、輕和重的動作對比;書法作品中節奏的變化主要通過運用墨色上的干濕、枯潤、濃淡,章法上的藏露、剛柔、疏密的對比來表現。書法與武術,就是通過對比產生“多樣化”,整中有變,變中求整體,變化中求統一,使得作品豐富多彩、變化無窮、起伏跌宕。書法中的對比使每個字充滿活力,并借助呼應讓其連接成一個有機整體,以讓其氣脈相連、精神挽結,讓觀者感受到一種氣息貫注、筆勢流暢、精神氣足的藝術魅力。武術也不例外,其可以通過密切聯系各動作使得構成統一的有機整體,并且整個套路并非是簡單的疊加運動而形成,而是融入了攻防技擊的邏輯與精神。綜上所述,武術與書法兩者均講究形式上的審美原則。
(二)章法布局的審美
整體美是章法布局的審美的關鍵。受傳統美學的影響,書法與武術的審美觀也更加注重整體。結構即武術套路的章法。動作組合有長有短,架勢有高有低,習演中層次變化各不相同;需要強調的是,盡管起筆對于書法創作較為重要,要求能引人入勝,但是落款卻更為關鍵,精妙的落款才能更好地彰顯章法之妙。同理,對武術習演也不例外,良好的起勢更能幫助選手更好地進入戰斗狀態,同書法之落款一樣,收勢動作也能讓人感受到回味無窮和余音繞梁之感。套路習演講究水平和質量,不管是起勢還是收勢,都要求全程保持精神振奮、斗志昂揚、永不懈怠、勇往直前。此外,管領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主體的審美活動。因此,套路起勢要具備吸引力,并要求演練者保持飽滿精神、優美姿勢和規范動作,全套習演始終保持英勇的氣勢、精神和斗志高昂,讓觀賞者為之動容,感同身受,使得武術習演能更好地帶動觀眾進入戰斗氛圍中。書法章法布局最明顯的表現是富有情趣的呼應,后者表現為前后筆畫的收筆與起筆間的連帶關系。譬如“筆斷意連”,盡管筆畫斷了,但恰當運轉筆勢也可以在筆畫的呼應中感受到貫通的筆意。而在武術中要求動作的“形斷意連”,如對于“側行步轉身大龍擺尾”動作,就要求武者頭和眼睛分別要回顧和向后看,想象敵人已處于可攻擊范圍,然后通過大龍擺尾來打擊敵人。所以,在武術習演時,各動作要由技擊意識進行引導,而技擊意識則主要體現在頭部、眼神、軀干及四肢動作上,讓各動作形成統一整體,讓搏擊精神貫穿整個動作套路。整體較局部更大,但是整體并非簡單疊加局部而來。書法同武術一樣,其作品只有經過作者的謀篇布局、精心構思,才能表現出神形相稱和意氣相聚的效果。作品如果缺少章法,整體將缺乏活力,難以體現精妙特征。總之,在審美意識和具體章法實踐上,書法與武術非常類似。
(三)氣韻的呈現
“氣韻生動”通常也被叫作六法之首。在藝術表現當中,必須具備飽滿的生命力,因為藝術所要表達的都是實實在在,有活性、有張力的生命體。“氣韻”最關鍵的當屬表達生命的意義,所以,在中國美學中,主要通過生動來展現氣韻。因此,對于藝術作品而言,生動、靈活成為評判其好壞的重要因素。所謂“氣韻”,一方面講究裝作者的精神氣質,同時內涵了生理之氣,在我國傳統哲學思想的影響作用下,中國美學對于“氣”的運用已經非常成熟,能夠實現筆與行氣呼吸的有效統一。書法家主要借助內在氣息的調節,以及運筆節奏的把控等,呈現出富有表現力的節奏感。無論是書法創作還是武術表演,都必須全神貫注,氣沉丹田,確保氣與動作的有效統一;提筆、按筆、收筆等都行使用氣來配合,在武術表演當中,動作呼氣需要注重提、托、聚、沉,借助呼吸節奏的把控,實現內外節奏的統一,進而構建渾然一體的完美旋律。“韻”所表達的是音樂感,所傳揚的是和諧的節奏。在書法當中,對用筆的力度非常有講究輕重緩急、提按頓挫、張弛有度,字形也有大小長短,在武術表演當中,講究輕重緩急、抑揚頓挫,以及剛柔并濟。武術表演主要通過相應的力度、速度,以及多邊的組合來構建武術旋律交響曲,將節奏感展現得淋漓盡致。為達和諧,書法創作還講究意在筆先,意到而筆隨,如此便能夠展現出更加靈動的韻味。對于武術而言,在實際進行演練的時候要對動作幅度、路線變化、架勢高低等因素進行提前熟悉,做到“意在筆前”,進而將藝術情感內化于心,并且在腦海中不斷想象自身創造的藝術形象,進而將塑造的形象靈活地展現出來,做到“氣韻生動”。武術氣勢中含有書法里的藝術生命力,并且我們還能夠從書法的筆歌墨舞中獲得武術的靈活生動。兩種藝術都是情感帶動下,強調表現出一氣呵成的效果。
(四)意境的營造
武術與書法藝術都尤其注重“意境”。何為意境,即藝術家在審美過程當中產生的感悟、體驗等,其屬于藝術形象和 主觀處理相融合以后的產物,是情物結合,主觀心境對客觀物象的感性反映和投射。意境是作品的靈魂所在,在書法審美中,藝術審美標準不單只是出色的技巧表現,更側重于作品的精神靈魂的營造和呈現。亦然,這也同樣適用于武術演練美學中。武術套路將具有攻防意義的技擊動作進行藝術加工,和習演者、編創者的情感、意志融合一致,在似象非象中達到“情境”相融,“意”“技”結合,形神互通。整體的意境美使武術的本質融于行云流水的套路當中,使人們在刀光劍影中感受美,品味醇厚的武術文化。在武術表演當中,借助動作來展現激情,同時借助激情來呈現斗志。這也是武術審美的主要形式。就武術套路演練過程而論,要切實展現戰斗的情態,飽滿的激情,激昂的斗志,以及貫通全身經脈的氣勢,是不可或缺的,把戰斗狀態中之“情意”“心境”和“物境”結合并交融,隨而產生并營造出氣韻生動的戰斗境界,進一步上升和提煉出戰斗的藝術意境。武術演練的意境美所展現的就是自己獨有的個性風格和充滿創造性的內容。書法的意境之美所包含的是書法的筆意、書情、風采和神韻等深層次的精神境況,書法的境界事實上也是作者思想表達和情意流露的境界。當書法家身處于一定的創作環境中,波瀾起伏的情感及情緒沖動涌上心頭,激射出強烈的靈感火花時,從而筆隨心運轉,物我兩皆忘,驚為天人的舉世作品隨即油然誕生。因此,書法家的個性與風格、立意與審美情趣、思想感情是造就書法意境美的重要內容。
三、結論及思考
綜述以上對傳統武術習演中書法精神的追尋,我們由此可得知,從美學角度來看,武術和書法之間存在著非常緊密的關系,武術演練中的各個動作環節也都體現了書法精神中的形式美、布局美、氣韻美及意境美。無論是在武術當中,還是在書法當中,都有著對藝術和意境追求的理想。因此,我們可以從書法精神中探尋一些適用于武術表現的藝術技巧,進而實現二者的有效交融,中國武術表現也能夠將書法的精神氣質完美地詮釋出來。二者相互影響和滲透,共同綻放出藝術的美感,給人們呈現出富有張力、變化無窮的體驗。不難看到,在書法精神和武術演練當中都包含了“氣”與“韻”的特點,這兩種藝術方式都可以通過創作上的活力、運動上的規律等來找尋更多的靈感,達到“精”“氣”“神”“韻”的藝術融合。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在如此深厚的文化背景下,書法精神作為我國優良文化精神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越來越表現出獨有的韻味,其能夠實現藝術創作與現實生活的完美融合,使得武術習演所產生的美學追求更具意義。
參考文獻:
[1]王軍濤.淺析武術套路演練中的美學特征[J].中華武術(研究),2018,7(3):62-65.
[2]熊恬.論武術套路演練中的動靜節奏[J].西部皮革,2016,38(20):202.
[3]傅三石.文武相合——書法與武術[J].美術與市場,2015(1):73-76.
[4]李海亭.書法精神性價值的內涵[J].國畫家,2014(4):71-72.
[5]雷霆,李紅.論武術套路與書法藝術的異曲同工之妙[J].才智,2012(26):163-164.
[6]舒獻忠.文化同源:中國武術與中國書法比較研究[D].蘇州大學,2009.
[7]劉同為,王昊寧.論書法藝術與武術演練的相通性[J].上海體育學院學報,2008,32(5):61-63.
[8]王冬齡.現代書法精神論[J].新美術,2007(1):10-14.
作者簡介:陸煒邦(1995-),男,漢族,廣東佛山人,華南師范大學碩士,華南師范大學美術學院美術學專業,研究方向:中國畫創作與理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