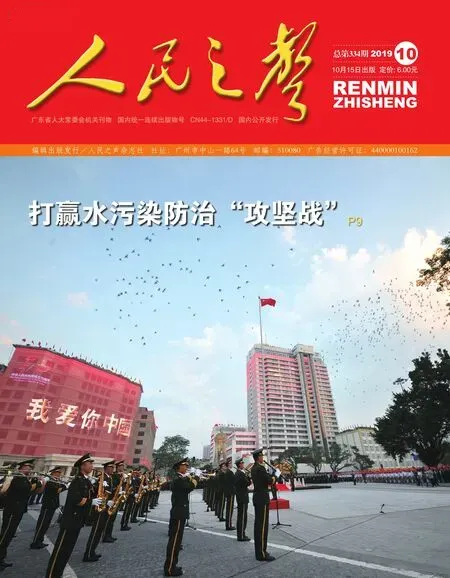地方人大工作蓬勃發展的動力機制

今年是地方人大常委會設立40周年。地方人大常委會的設立,使人大的運轉更加制度化規范化,使人大各項職權常態化地行使。地方人大常委會設立以來,在立法、監督、代表工作等各個領域取得了非凡成就,為法治中國的建設貢獻良多。回顧地方人大常委會40年來的發展,筆者認為,地方人大蓬勃發展的動力至少來自三個方面。首先是中央的頂層設計,其次是地方人大常委會自身的開拓探索,再次是社會公眾的參與支持。
首先,地方人大常委會的設立,是中央的領導層為了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的價值追求,通過國家立法從上而下地啟動的。所以說中央的立法,是地方人大制度發展的第一個推動力。1979年的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通過了新的選舉法和地方組織法。這兩部法律賦予了地方人大更大的權力和活力。1979年地方組織法規定,縣級以上的地方人大設立常委會。1979年之后,中央繼續用國家立法規范地方人大的產生和運行。至今選舉法和地方組織法已經分別經歷了六次和五次修改。1992年七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代表法也經歷了修改完善。2006年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監督法,該法于2007年施行。這些法律的制定和修改,為人大代表和選民等地方人大制度的參與者提供了制度空間與機會之窗。這些法律的制定是出于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的價值追求,是以憲法對人大的推崇為依據,重新設計地方人大的組織架構和權力界限。
其次,作為政策制定者和制度設計者的國家,很多時候并不直接參與制度的運作和政策的執行,制度的執行者是另一群行動者。他們自身也會形成對制度的理解和認同,而且會按照自己在制度體系中的地位來設計自己的行為方式,推進制度的運轉。地方人大的常委會,自成立之日起,就在組織機構和人員配備上逐漸地完善,人大內部的常委會組成人員和辦事機構的工作人員自發地探索人大權力的具體行使方式,力圖落實人大在理論上的立法、監督和民主的功能。地方人大常委會自發自覺的探索,這是人大制度發展的第二個動力。監督法出臺以前,1979年的地方組織法和1982年憲法雖然賦予了地方人大國家權力機關的地位和職權,但是并沒有提出具體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行使各項職權的方式形式和步驟程序。各地的地方人大常委會積極探索人大職權行使的具體方式,有許多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例如,地方組織法規定了地方人大審查和批準本行政區域預算的權力。預算法也規定了地方各級政府預算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審查和批準。但這些法律沒有規定人大預算審查的具體步驟。這方面法律的實施細則由地方人大自己摸索制定。早在上世紀80年代,安徽、四川、河北等地的人大及其常委會就制定了人大預算監督的規范性文件。1995年深圳市人大率先成立了深圳市人大常委會計劃預算審查工作委員會,2000年將該工委會升格為專門委員會。繼深圳之后,北京、上海、重慶、天津、四川、安徽、云南等20多個省級人大常委會都設立了預算工委會或專委會。2004年廣東省人大與省財政廳國庫實現聯網,對政府財政支付實時監督。再如,代表評議是指人大及其常委會組織代表對本級國家機關的工作進行評議。有據可查的最早的代表評議是1982年黑龍江省某縣人大對“一府兩院”進行的代表評議。直至今日,這種監督方式還在一些地方人大推行。
第三,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法治理念的普及,使社會中的群體和個人有了新的訴求和目標,這種變遷也激發促使這些群體和個人利用現存制度去實現其新生訴求和目標。市場經濟的發展使社會利益日益分化和多元化,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利益還會發生沖突。人們迫切需要制度化的利益表達機制和博弈平臺,需要通過法治的渠道來尋求自身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利的實現。人大就是這樣一個渠道和平臺。所以我們看到歷次的人大選舉中,有不同社會階層的人站出來參選人大代表。在選舉結束后,選民也會積極地去找人大代表反映問題,希望代表把自己的訴求帶到政府決策中去。在人大舉行的立法聽證會,法律草案向社會公布征求意見等場合,許多公民積極地參與,表達心聲。所以,市場經濟和社會分層所帶來的權利意識的蘇醒和公民的政治參與,是人大制度發展的第三個動力。
地方人大常委會四十年來的發展,首先體現為中央的立法設定了地方人大常委會的組織和權力;其次,是地方人大常委會在中央立法提供的制度框架內,通過地方法規和實踐對中央立法細化,落實了中央立法所規定的人大權力;最后,是社會各階層成員積極參與人大的選舉與運作。在《發展民主:走向鞏固》一書中,戴蒙德指出,民主制度的鞏固有三個指標,依次是精英層、組織層和大眾層面對本國民主制度的信念和擁護。我國地方人大常委會的發展史印證了這個說法。地方人大常委會未來的蓬勃發展,依然需要這三個動力的共同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