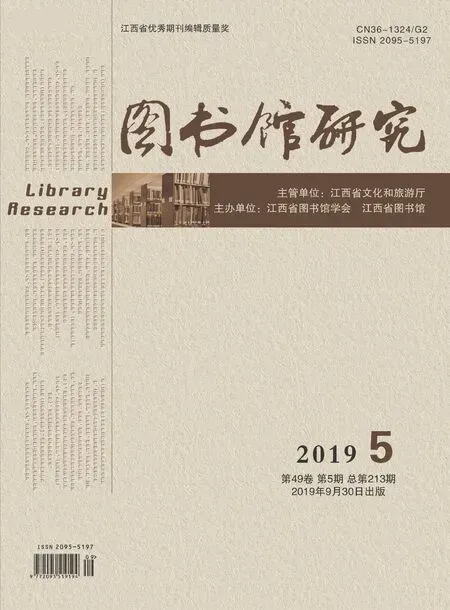近代山東教會(huì)圖書館史略
(山東省圖書館,山東 濟(jì)南 250199)
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中國戰(zhàn)敗,1858年,英法聯(lián)軍強(qiáng)迫清政府簽訂《天津條約》,約定各國傳教士可到中國內(nèi)地自由傳教,這些教會(huì)建教堂、創(chuàng)學(xué)校、興機(jī)構(gòu)開展宣教活動(dòng),從而鞏固并擴(kuò)大教會(huì)組織勢力。山東的煙臺(tái)、青島、威海等城市先后被迫開埠,傳教士亦紛紛大批進(jìn)入山東傳教,先后以登州、煙臺(tái)為據(jù)點(diǎn),繼而深入內(nèi)地,劃分教區(qū)。山東天主教和基督教等教會(huì)勢力在全國來說都占有靠前的位置。“基督教在山東布道區(qū)之多,居全國第一;信徒人數(shù),居全國第二;西教人士,居全國第五;教會(huì)中小學(xué)數(shù),居全國第一;教會(huì)醫(yī)院數(shù),居全國第四等”[1]。山東天主教徒在全國之地位,光緒三十三年(1907)占全國教徒總數(shù)的7%,次于直隸、江蘇、四川(包括西藏)、廣東,居第5位,民國九年(1920)次于直隸和江蘇列第3位。[2]
1 山東教會(huì)圖書館概況
開展教育事業(yè)是教會(huì)傳教活動(dòng)的重點(diǎn)之一,至1918年,全國教會(huì)學(xué)校已達(dá)13 000所,絕大多數(shù)為中小學(xué),教會(huì)大學(xué)相對(duì)建立較晚,基本上是在20世紀(jì)初教會(huì)所屬“學(xué)堂”“書院”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起來的。天主教會(huì)在山東創(chuàng)辦的中學(xué)與全國的天主教中等教育相比,是最發(fā)達(dá)的省份之一。據(jù)1930年統(tǒng)計(jì),全國共有天主教中學(xué)51所[3],其中山東十多所,超過全國的四分之一。山東的基督大學(xué)僅有齊魯大學(xué)一所。
教會(huì)圖書館則是隨著學(xué)校或文化機(jī)構(gòu)的興辦而發(fā)展起來的,是其重要組成部分。教會(huì)圖書館,多附設(shè)于學(xué)校,一般規(guī)模都很小,較大的圖書館一般附設(shè)于各大教堂中,濟(jì)南、青島、煙臺(tái)等的教堂附設(shè)教會(huì)圖書館,藏書都較豐富。如圣言會(huì)兗州教堂,該教堂是光緒二十三年(1897)的巨野教案賠款修建的,藏書就比較多,據(jù)說教堂建起后,余款均購買了圖書。不過,教會(huì)圖書館的藏書多是神學(xué)方面的,一般不對(duì)外開放。

表1 基督教學(xué)校圖書館民國二十五年藏書情況[4]
從表1各學(xué)校教會(huì)圖書館藏書數(shù)量上可以看出,除齊魯大學(xué)圖書館館藏豐富,在10萬冊(cè)以上,其余皆相對(duì)較少,最多才1.5萬冊(cè),訂購雜志種數(shù)更是少之又少,有的甚至沒有,進(jìn)一步印證了學(xué)校圖書館規(guī)模之小。
除了教會(huì)學(xué)校圖書館以外,山東省各地設(shè)有青年圖書館(煙臺(tái)、濟(jì)南、青島等),還有與博物館共存的廣智院圖書館和創(chuàng)辦較早的尊孔文社藏書樓等。本文通過對(duì)這4所不同類型、性質(zhì)的教會(huì)圖書館進(jìn)行深入分析,以窺民國時(shí)期山東教會(huì)圖書館之全貌。
2 山東四大教會(huì)圖書館
2.1 齊魯大學(xué)圖書館
齊魯大學(xué)圖書館的前身是創(chuàng)建于1868年的登州文會(huì)館的藏書室,1904年登州文會(huì)館和青州廣德書院合并為濰縣廣文學(xué)堂,藏書室改名為廣文學(xué)堂圖書室,1917年廣文學(xué)堂又與濟(jì)南共和合醫(yī)道學(xué)堂合為齊魯大學(xué),三校藏書亦合組為圖書館,即齊魯大學(xué)圖書館,當(dāng)時(shí)三校合計(jì)藏書也只有19 000余冊(cè)。[5]
圖書館開始設(shè)在校內(nèi)柏爾根樓上,不久又移到考文樓。美國長老會(huì)傳教士奚爾恩出任首任館長,聘王天綱任圖書館主任,辦理全館事務(wù),另有館員5人,分別負(fù)責(zé)編目、出納、閱覽、典藏、文牘和購書等事務(wù)。1921年,齊魯大學(xué)接受加拿大危培格(Winnipeg)之奧古斯丁(Augustine)長老會(huì)支會(huì)捐款,開始在校內(nèi)的東南角修建一所新的圖書館,于1922年竣工并投入使用。為了對(duì)奧古斯丁長老會(huì)表示感謝,此館亦稱為奧古斯丁圖書館。奧古斯丁圖書館曾先后聘巴達(dá)、桂質(zhì)柏、皮高品、陳鴻飛、邢云林等為主任,諸君皆為中國近代圖書館界的重量級(jí)人物,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下,圖書館無論是藏書、文獻(xiàn)組織、業(yè)務(wù)管理等都有長足的發(fā)展,走在了全國的前列。另齊魯大學(xué)圖書館設(shè)有一醫(yī)學(xué)院分館,醫(yī)學(xué)文獻(xiàn)資料均存放于此館。為了方便檢索館藏,館藏目錄卡片制作兩份,一份存總館,一份存分館。
齊魯大學(xué)圖書館藏書主要由各學(xué)系自行購入,但須經(jīng)圖書館查重,再送圖書館保藏,同時(shí)接收社會(huì)捐贈(zèng)。1929年“館內(nèi)原有書籍約24 000余冊(cè),中西書籍約各半數(shù),并備有西文雜志200余種,中文雜志400余種”,“民國十九年度復(fù)籌款添購中國書籍約50 000余冊(cè)。”[6]至1931年藏書已達(dá)到74 000余種。1935年“圖書館又新購中文書2 140冊(cè),外文書1 200冊(cè),共3 304冊(cè)”[7]。1936年增至118 000余冊(cè)。

表2 齊魯大學(xué)圖書館1917-1946年藏書統(tǒng)計(jì)表[8]
1938年,濟(jì)南淪陷,齊魯大學(xué)西遷成都辦學(xué),一部分藏書隨學(xué)校轉(zhuǎn)移至華西協(xié)和大學(xué)暫存,另有89 000余冊(cè)由山東省圖書館接收。抗戰(zhàn)勝利后的1946年,省館又將書全數(shù)返回齊魯大學(xué)圖書館,“本館現(xiàn)存中文圖書87 000余冊(cè),西文圖書18 000余冊(cè),共計(jì)105 000冊(cè)”[9]。1952年,新中國推行院系調(diào)整,齊魯大學(xué)被分割解散,齊魯大學(xué)圖書館也隨之消失。
2.2 煙臺(tái)青年圖書館
1896年,美國教師韋豐年(George Cornwell)在煙臺(tái)創(chuàng)辦了青年會(huì),1915年青年會(huì)全國協(xié)會(huì)為其頒發(fā)證書,1916年,會(huì)員達(dá)到700余人。[10]青年會(huì)大力宣傳平民教育和公民教育,先后舉辦公民教育、職工研究團(tuán)、農(nóng)村演講等,后又特請(qǐng)南開大學(xué)校長、天津青年會(huì)董事張伯苓等來煙臺(tái)青年會(huì)演講,轟動(dòng)一時(shí)。
1930年,基督教青年會(huì)為了進(jìn)一步體現(xiàn)青年會(huì)宗旨、擴(kuò)大青年會(huì)的影響,創(chuàng)辦了“青年圖書館”,成為煙臺(tái)第一家公共圖書館,“膠東王”劉珍年還獻(xiàn)上他親筆書寫的“文化淵藪”賀匾。青年圖書館從啟動(dòng)到建成,每個(gè)階段皆群策群力,悉心籌備。首先公舉籌備委員會(huì)長1人、委員2人。據(jù)統(tǒng)算,購書建筑兩項(xiàng)費(fèi)用,共需銀1.2萬元,創(chuàng)辦費(fèi)用不足,分別動(dòng)募,成績亦佳:“決定先由青年會(huì)內(nèi)部捐募,以示提倡,于是地方長官,商界領(lǐng)袖,聞風(fēng)興起,解囊捐助。”[11]不到數(shù)月,創(chuàng)辦費(fèi)已達(dá)半數(shù)。其次派代表參觀江浙各大公私立圖書館,對(duì)其建筑、藏書、布置等都一一詳細(xì)研究。再次主要向大的出版社采購圖書,如上海商務(wù)印書館、中華書局等,以為圖書館公共閱覽為采訪原則,共萬余卷,數(shù)量在當(dāng)時(shí)來說也算比較豐富。拆除舊房,改建二層樓房1所,內(nèi)部計(jì)30間。管理員的人選非常嚴(yán)格,必須是有學(xué)識(shí)、有愛心、有耐心之士,因此派專門管理人員赴上海東方圖書館學(xué)習(xí),以資參考。
青年圖書館在傳播知識(shí)的同時(shí),也成了中共煙臺(tái)地下組織的活動(dòng)陣地。中國共產(chǎn)黨在煙臺(tái)發(fā)展的第一名黨員、后任煙臺(tái)臨時(shí)市委第一任書記、1931年8月在濟(jì)南英勇就義的許瑞云烈士以及1927年介紹許瑞云入黨、1928年5月被選為煙臺(tái)歷史上第一位黨支部書記的徐約之等早期共產(chǎn)黨人,都經(jīng)常在青年圖書館秘密開展黨的工作。[12]
1945年,煙臺(tái)基督教育青年會(huì)領(lǐng)導(dǎo)人離開煙臺(tái),青年圖書館隨之關(guān)閉。
2.3 尊孔文社藏書樓
尊孔文社藏書樓既是青島第一座圖書館,也是我國最早的現(xiàn)代圖書館之一。1914年尊孔文社藏書樓在禮賢書院內(nèi)落成。禮賢書院為衛(wèi)禮賢于1900年在青島成立的教會(huì)學(xué)校。當(dāng)年的禮賢中學(xué)是清末民初膠州灣地區(qū)最新式學(xué)堂樣板,是我國北方地區(qū)建立最早的現(xiàn)代中學(xué)之一,也是衛(wèi)禮賢留給青島的最大的一筆“遺產(chǎn)”。衛(wèi)禮賢,德國傳教士,1899年進(jìn)入中國傳教,在其57年的生涯中,有24年是在中國度過的,其中在青島多達(dá)21年。他本人喜愛漢學(xué),尤其尊崇孔子,對(duì)儒家學(xué)說佩服不已,學(xué)習(xí)中國文化孜孜不倦,“衛(wèi)君最好學(xué),手不停揮,目不停覽,雖炎夏不避,危坐譯讀晏如也,是故精通華語及文義”[13]。其將《論語》《孟子》《易經(jīng)》等20多部中國典籍翻譯成德文,在西方廣為傳播,著名學(xué)者季羨林將衛(wèi)禮賢稱為“東學(xué)西漸”的功臣,被譽(yù)為“中國在西方的精神使者”。
辛亥革命后,大批清朝遺老跑到青島,其中就有著名學(xué)者、學(xué)部副大臣勞乃宣。1912年,衛(wèi)禮賢在禮賢中學(xué)校舍旁成立了尊孔文社,由勞乃宣主持社務(wù)。1914年又在其旁建立了尊孔文社藏書樓,收藏圖書,開展借閱活動(dòng)。雖名藏書樓,性質(zhì)上已是為公眾服務(wù)的現(xiàn)代圖書館。“藏書樓”匾額由當(dāng)時(shí)寓居青島的恭親王愛新覺羅·溥偉題寫。勞乃宣在《青島尊孔文社藏書樓論》中寫道:“德國衛(wèi)君禮賢以西人而讀圣人之書,明吾圣人之道也。時(shí)居青島,與中國寓島諸同仁結(jié)尊孔文社以講求圣人之道,議建藏書樓以藏經(jīng)籍,同人樂贊其成。”
2.4 廣智院圖書館
廣智院的創(chuàng)設(shè)者為英國浸禮會(huì)傳教士懷恩光,于1887年在山東青州府建設(shè)博物堂,因其規(guī)范狹小,參觀人數(shù)每年不過5 000余人[14]。為擴(kuò)充起見,于1893年附設(shè)于“郭羅培真書院”。1904年膠濟(jì)鐵路通車,濟(jì)南既為省會(huì),又交通便利,人文薈萃,故于1905年造新學(xué)堂于濟(jì)南南關(guān)山水溝旁,同年落成典禮,更名為廣智院,意為“廣其智識(shí)”。教育學(xué)家黃炎培寫到“院長英人懷恩光君,自購地建屋,于今十年,燦然大備。院長謂十年購地建屋及一切布置陳列約超耗費(fèi)銀九萬六千圓,皆陸續(xù)捐募得之”[15]。山東巡撫楊士驤參加開幕慶典,懷恩光任首任院長。其后潘亨利、魏禮謨、斐禮伯、胡維恩、林仰山先后任院長,均為浸禮會(huì)傳教士。設(shè)有各國人種模型室、萬國史記室、商務(wù)研究室及閱書報(bào)室、體育室等,“所陳列各種標(biāo)本模型寫真與圖表等項(xiàng)有二千余組,共計(jì)一萬余件”[16]。廣智院的建立可以說是濟(jì)南科普教育的開端,它對(duì)開闊人們的眼界,傳播新知識(shí)、新文化具有重要啟蒙作用。
廣智院作為社會(huì)教育機(jī)關(guān),雖然沒有設(shè)立獨(dú)立的圖書館,但其開展的讀書閱覽活動(dòng)一直未曾中斷,初創(chuàng)期就設(shè)有閱報(bào)室,后又增設(shè)巡回文庫,反映了其新式公共空間的特征。閱報(bào)室有報(bào)章雜志數(shù)十份,任人閱看,“閱報(bào)室陳列圖書報(bào)紙,閱書用盤使,授受時(shí)書不著手。英文報(bào)告,一年閱書報(bào)者總數(shù)三萬九千人”[17]。1920年上海廣學(xué)會(huì)向廣智院捐贈(zèng)大宗圖書,又創(chuàng)辦巡回文庫,由職員攜書至各機(jī)關(guān)、學(xué)校、商號(hào)、寓所等巡回送閱,方便了民眾的閱讀,也擴(kuò)展了他們的視野。為了方便在官兵中布道,1913年4月,懷恩光還在濟(jì)南緯十二路的辛莊軍營附近設(shè)立“軍界廣智院”,設(shè)有演講廳、閱覽室、俱樂部、課室等,到1919年,“前往參觀者達(dá)47 000人,其中軍人占3萬人,當(dāng)年前往閱書室讀書者達(dá)3 600人”[18]。
1917年廣智院被并入齊魯大學(xué),名齊魯大學(xué)社會(huì)教育科。1941年12月,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該院被日軍接管,改為科學(xué)館。
3 教會(huì)圖書館的讀者、藏書及本土化
3.1 為特定讀者群體服務(wù)
早期的教會(huì)圖書館受創(chuàng)始人(管理者)、館舍建筑、館藏條件、服務(wù)理念等限制,服務(wù)群體有其特定性,即讀者中教徒占多數(shù),如教會(huì)齊魯大學(xué)圖書館服務(wù)對(duì)象主要是在校師生,不對(duì)校外讀者開放,在其借閱條例中有“凡本校教職員學(xué)生,均享受借閱之權(quán)”,顯示了它的服務(wù)對(duì)象是在校師生。而齊魯大學(xué)在招收學(xué)生時(shí),要求“至少須有百分之五十的學(xué)生,是由基督徒的家庭來的,或者他們本人是已做基督徒的”[19]。1924年齊魯大學(xué)基督徒學(xué)生比例高達(dá)89%,1934年仍為70%[20],進(jìn)一步說明圖書館讀者以教徒為主。
尊孔文社藏書樓初創(chuàng)時(shí)期依附于禮賢中學(xué),“現(xiàn)只供禮賢中學(xué)教員及學(xué)生應(yīng)用”[21],服務(wù)群體以禮賢中學(xué)的教職員和清朝遺老為多。煙臺(tái)青年圖書館創(chuàng)建之初亦主要為青年會(huì)服務(wù),也向社會(huì)開放。隨著圖書館本土化的發(fā)展,教會(huì)圖書館開始面向公眾,具有了公共圖書館的性質(zhì)。
3.2 以西文文獻(xiàn)為主的館藏結(jié)構(gòu)
教會(huì)圖書館的性質(zhì)、讀者群體的高教徒比例及創(chuàng)辦者的理念,決定了教會(huì)圖書館的館藏結(jié)構(gòu)以西文文獻(xiàn)為主,重視外文文獻(xiàn)的收藏也成為各教會(huì)圖書館的主要特點(diǎn)。如齊魯大學(xué)作為西式教會(huì)大學(xué),為使西方文化“涵化”中華文化,無論是出于傳教的目的還是教育目標(biāo),在教學(xué)中大量引進(jìn)西方科學(xué)知識(shí),開設(shè)數(shù)學(xué)、物理等現(xiàn)代科學(xué)課程,故對(duì)西文書籍有較大需求,大量西文書刊被引入圖書館,“統(tǒng)計(jì)館內(nèi)書籍有一萬六千余卷,其中之六千余卷為漢文,余一萬卷為英文”[22]。1926年新館落成后,“館內(nèi)藏書統(tǒng)計(jì)約一萬九千余卷,內(nèi)有漢文書籍約六千卷,英文書籍約一萬三千卷”[23]。從這些數(shù)據(jù)中可以看出,西文書籍比漢文書籍占比要大。
在以西文文獻(xiàn)為主的館藏結(jié)構(gòu)下,教會(huì)圖書館無論是西文文獻(xiàn)還是中文文獻(xiàn),在搜集時(shí)又以宗教類的圖書優(yōu)先入藏,而且藏量很大。同時(shí)這些圖書館亦非常重視珍本善本古籍收藏,如尊孔文社藏書樓,多方收集經(jīng)史子集等文獻(xiàn)。1935年許晚成編《全國圖書館調(diào)查錄》記載:尊孔文社藏書樓的“藏書有6 000余冊(cè)中文,3 000余冊(cè)德文,2 000余冊(cè)英法文,共12 000多冊(cè),其中有不少善本”[24]。而齊魯大學(xué)國學(xué)研究所的成立,將圖書館館藏特別是古籍善本書的收藏又提到一個(gè)新的高度。欒調(diào)甫從一開始就特別注意圖書資料的完備,1930—1932年共購入7 000余部,并專門成立善本書室,且編有《善本書目》及《書庫總目》[25]。到1935年齊大圖書館藏書近10萬冊(cè),擴(kuò)充的部分大都為國學(xué)文獻(xiàn)。
3.3 教會(huì)圖書館的本土化
隨著傳教士在中國的發(fā)展,特別是20世紀(jì)20年代的收回教育權(quán)運(yùn)動(dòng)和北伐,更使許多傳教士認(rèn)識(shí)到教會(huì)圖書館本土化的必要性。“當(dāng)他們開始比較了解中國文化而尊重中國文化時(shí),他們便試著使西學(xué)與技術(shù)來適應(yīng)中國國情”[26]。表現(xiàn)之一就是教會(huì)大學(xué)把服務(wù)鄉(xiāng)村建設(shè)作為傳播宗教的媒介,使鄉(xiāng)村服務(wù)與傳教有機(jī)地結(jié)合起來。如齊魯大學(xué)在鄉(xiāng)村建設(shè)上利用書籍進(jìn)行鄉(xiāng)村教育,充分發(fā)揮自身教會(huì)圖書館的優(yōu)勢,在龍山試驗(yàn)區(qū)內(nèi)創(chuàng)辦了“書報(bào)室”,把學(xué)校的圖書資料免費(fèi)向民眾開放,“有日?qǐng)?bào):平民、大公、申報(bào)三份。周報(bào)三份:農(nóng)村新報(bào)、民教周刊、興華報(bào)”[27]。并指導(dǎo)民眾認(rèn)字讀書看報(bào)。表現(xiàn)之二是出版書刊。衛(wèi)禮賢主持編寫了《德華課本》《德華教科書》《德華單字、語法、翻譯》和《德文入門》,這是我國教育史上最早的中學(xué)德語教材,也是中德文化交流碰撞的一個(gè)重要載體。表現(xiàn)之三就是重視漢文書籍和地方文獻(xiàn)收藏,從圖書館的始建時(shí)西文占比較大,到后期漢文書籍超過西文書籍,也說明圖書館在收藏上逐漸本土化。
4 教會(huì)圖書館與近代山東社會(huì)
“圖書館應(yīng)該是傳教士的外會(huì)客室,在傳教事業(yè)上是一種最直接最有力的工具”[28]。雖然教會(huì)圖書館是其傳教的工具,但同時(shí)也應(yīng)看到其對(duì)山東乃至中國近代文化的發(fā)展所起到的一定的促進(jìn)作用。
4.1 促進(jìn)了中西方文化的傳播與交流
山東教會(huì)圖書館的出現(xiàn),在客觀上使得以藏書樓為基本形式的傳統(tǒng)圖書館開始向現(xiàn)代圖書館轉(zhuǎn)化。經(jīng)過傳教士在收藏文獻(xiàn)上的主動(dòng)選擇,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學(xué)文獻(xiàn)得以在山東收藏、傳播,同時(shí)也使中國的文化在西方得到認(rèn)可。如,衛(wèi)禮賢作為一名德國傳教士,特別喜愛中國文化,劬勤不倦。他在后來的《中國心靈》一書中曾寫道:“我們希望通過翻譯、講座和出版的方式,在東西方文化之間架起一座橋梁。康德的著作被翻譯成中文,中國的經(jīng)典也被翻譯成德語。”他翻譯的20多部中國典籍在西方廣為傳播,為東學(xué)西漸做出了重要貢獻(xiàn)。從這方面看衛(wèi)禮賢的尊孔文社既是一個(gè)研究儒學(xué)的機(jī)構(gòu)、學(xué)習(xí)漢學(xué)的最佳場所,又是聯(lián)系流亡到青島的清朝學(xué)者和德國在青人士的組織,也是20世紀(jì)20年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載體。
4.2 對(duì)山東地方文獻(xiàn)的搜集與保存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
山東教會(huì)圖書館在文獻(xiàn)的采選上基本上都偏重于西文,但隨著教會(huì)的本土化,收藏也開始向中文文獻(xiàn)偏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齊魯大學(xué)圖書館在其國學(xué)研究所1930年成立之后,根據(jù)自主購書權(quán),國學(xué)研究所可以根據(jù)所需有選擇地采購,抗戰(zhàn)前的收集主要集中在齊魯文化方面,1936年之后,幾乎收集了山東所有地區(qū)的地方志,“據(jù)1935年年報(bào)統(tǒng)計(jì),圖書館當(dāng)年收集到的志書數(shù)目達(dá)到了726部9 613卷,叢書達(dá)到22 338種,并都進(jìn)行了系統(tǒng)編目,制作了子目通檢和一萬多張目錄卡”[29]。這些地方文獻(xiàn)都是調(diào)查研究山東社會(huì)、歷史和農(nóng)村等方面不可缺少的珍貴資料,由此也形成了齊魯大學(xué)圖書館藏書中的地方志特色。同樣,尊孔文社藏書樓因創(chuàng)辦者衛(wèi)禮賢的個(gè)人喜好,四處張羅募集和購買經(jīng)、史、子、集、諸子之書,館藏有不少的古籍善本。地方文獻(xiàn)被圖書館搜集、收藏,使其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并流傳下來。
4.3 對(duì)山東早期圖書館事業(yè)產(chǎn)生有益影響
教會(huì)圖書館十分重視規(guī)章制度的建設(shè),制度保證了圖書館工作的正常運(yùn)行。所涉及的內(nèi)容主要集中在借閱規(guī)則上,如1936年齊魯大學(xué)的借閱規(guī)則就有5大條30小條,包括了借閱范圍、借閱冊(cè)數(shù)、借閱時(shí)限、借閱手續(xù)、賠償制度、閱覽管理等非常詳細(xì)的條目。同時(shí)制度也涉及購書、編目、藏書等。齊魯大學(xué)在編目時(shí)采用先進(jìn)的編目規(guī)范,依桂質(zhì)柏先生編譯之杜威書目十類法,西文書依杜威氏原本,另編著者號(hào)碼表、西文書著者號(hào)碼。詳細(xì)的規(guī)章制度和先進(jìn)的工作方法為山東早期的圖書館事業(yè)提供了借鑒。
4.4 對(duì)山東當(dāng)?shù)厝嗣耖_啟了思想啟蒙
山東的這幾所教會(huì)圖書館幾乎都向公眾開放,煙臺(tái)青年圖書館面向社會(huì),前來借閱的除青年會(huì)會(huì)員外,亦有洋行、商號(hào)職員,教師,學(xué)生和平民百姓。廣智院圖書館在1924年的擴(kuò)充計(jì)劃中曾寫到“本院近三年來承廣學(xué)會(huì)惠予書籍,特出資聘用人員接洽,商學(xué)各界巡回送閱頗著成效,奈濟(jì)南地廣人眾普遍難,期時(shí)引為憾,倘荷閱者,贊助或惠寄書籍或慨捐款項(xiàng),使地方人士多獲讀書之益,禆益社會(huì)寧有既極”[30]。從中可以看出該院的巡回文庫很受民眾的歡迎。“1924年,閱報(bào)室有閱覽者35 000人,由巡回文庫借書看的有200余處,看過1 000多冊(cè)書”[31]。 民眾通過圖書館獲取所需知識(shí),開啟了思想啟蒙。
5 結(jié)語
教會(huì)圖書館是隨著學(xué)校或文化機(jī)構(gòu)的興辦而發(fā)展起來的,是其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國近代史上最先出現(xiàn)的新式圖書館,不僅有中國了解和觀察西方近代圖書館的史料,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而山東的這些教會(huì)圖書館更是山東較早出現(xiàn)的具有現(xiàn)代意義的圖書館,推動(dòng)了圖書館事業(yè)在山東的傳播,促進(jìn)了民眾對(duì)圖書館的認(rèn)識(shí),對(duì)研究山東的圖書館史具有很高的史料價(jià)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