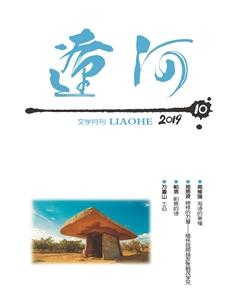莧菜情思
荊淑敏
我是東北農村長大的丫頭。那個年代經歷的一切,走到今天,該是怎樣一種定義?無論貧窮和艱難,每每回憶起來,卻有了財富一般的感覺,我有,別人沒有的。我的散文《捋豬菜》在2015年首次入圍中國散文排行榜時,我就感覺我的財富是一只潛力股。
隨意翻翻我的《捋豬菜》,眼前各種野菜活靈活現一棵棵一片片浮現在我的眼前。沒有我道不出名字的:徽菜、莧菜、馬齒菜、豬毛菜、刺菜……
偶得閑暇,我從野菜的名簽里,抽出一支,它叫莧菜。
我想閑聊,漫無邊際,天南地北,無拘無束,無規無矩。
從我、從豬食、從營養、從醫學,誰讓它是我一生心中的那盤菜?
在東北農村長大的孩子,都見過一種叫莧菜的野菜,春末夏初的田間地頭,路邊道旁,遮蔽著蓬蓬勃勃的莧菜,像綠色浪花,翻卷的云霞,掐下上面的葉子,不幾天又生出新的葉片來,層出不窮。莧菜,青的柔嫩,紅的厚潤,是瓜菜代飯的年月里不可缺的一道時蔬。
莧菜在初夏不但人可以吃,也可以做豬食,我家住在村東頭,父親在屋邊用土坯壘起一個很大的豬圈,春起時,媽就抓來三頭豬仔,到了年底,這三頭豬能剩兩或一個,每當這時,母親情緒很低落,嘴不時的叨咕著那些假如,要是諸如此類的假設的未來。
看著難過的母親,我就放學的時侯就去捋野萊,燒豬食,把嫩嫩的莧菜焯好,變著法兒哄著媽說;想吃莧菜包的包子。
父親在一旁咧著嘴贊許的樂著,目光里透露出深厚的慈祥。
捋豬菜的日子,快樂并不情愿著,放學后的小伙伴,跳著皮筋,打著沙包,拍著皮球。我只能挎著父親專門為我編制的柳條筐,筐梁比較矮,更適合我用胳膊挎著。每天我都慢慢悠悠走向南壕溝土埂上。這里的野菜很多,莧菜卻是我的首選。滿滿的一筐后,該是我自己尋找樂趣和自由了。抽一根野草梗,逮些螞蚱串上,放在莧菜筐里。偶爾編一束野花環戴在頭上,嘴里哼哼著樣板戲《紅燈記》里李鐵梅唱段:“我家的表叔數不清,沒有大事不登門……”拐過那座小橋,小表哥站在那里:“舅媽說了,天黑不放心。”我筐里的螞蚱,掙扎著小腿,拱得綠綠的莧菜葉也慢慢動著。
小表哥接過野菜筐,我就像快樂的小山羊咩咩地跑在回家的路上。
我很會烀豬食,也很會喂豬,野菜倒進鍋,放入小土豆,小到走不上人們的餐桌,從大土豆里甩出來的。加清水,燒火,開鍋。用木桿將土豆野菜碓碎,一鍋豬的美食便誕生了,將豬食盛在一大缸里。
“啰啰,啰啰”我喊著小豬。舀一瓢豬食放在木槽里,抓一把米糠撒進去。香得小豬耳朵直扇動。
我家豬長得快,每年年底都能殺一頭豬,幸運的話還可賣一頭。貧苦的歲月里,殺一頭豬,那是一家人全年的油水和額外熱量的補充,賣一頭豬,換來一百元多錢,為羞澀的日子增添了活力。
北方夏天里的野萊,長的早,來的快,早早地給剛從風雪走出的人們帶來新的希望。人們在田野上肆意的揮霍著剩余熱量。
我知道作家張愛玲喜歡吃莧菜,她在書中說:“炒莧菜沒蒜,簡直不值一炒。”我不知道南方的莧菜和北方的莧菜有無區別。看來做莧菜蒜瓣是點晴之筆。那時張愛玲時常去街對面的舅舅家蹭飯,而母親會常帶一份清炒莧菜。她是這么描敘的“莧菜上市的季節,我總是捧一碗烏油油紫紅夾墨綠絲的莧菜,里面一顆顆肥白的蒜瓣染成淺粉紅。在天光下過街,像捧著一盆常見的不知名的西洋盆栽,小粉紅花,斑斑點點暗紅苔綠相同的鋸齒邊大尖葉子,朱翠離披,不過這花不香,沒有熱乎乎的莧菜香。”
有地方把莧菜叫為銀菜,也叫米莧或蔊菜,蔊菜這一叫法源自《本草綱目》:“蔊菜生南地,田園中小炒也。”莧菜見土就長,野生的東西生命力極強。夏天,餐桌上一盤青青的莧菜讓人頓生涼意,味道很美。
洗莧菜不同于別的青菜,不論青紅,洗是揉洗,這樣味道更美,古諺云:好莧菜,揉三揉。
我喜歡吃母親炒的莧菜,那時油少,就多放大蒜,火候適中后用大蒜收鍋,吃起來嫩嫩香香,十分爽口。莧菜不易炒,掌握不了門道,炒不出莧菜特有的味道,母親說,炒莧菜倒入適量的油就更好了。
母親還常把莧菜在開水里燙一下,曬在窗檐下,冬天雪花飄飄的日子,包包子吃別有風味。清人顧仲在《養小錄·蔬之屬》中提到:“灰莧菜,熟食,炒、拌俱可,勝家莧,火證者宜之。”清人薛寶辰《素食說略》記“莧菜有紅、綠兩種,以香油炒過,加高湯煨之。”這種做法也很妙,因為先炒再煨更能使之香濃,更凸顯莧菜的鮮美。
莧菜梗也是一道美味,汪曾祺在《五味》一文中提到故鄉高郵,許多人家都有臭壇子,腌芥菜擠下的汁放幾天即成臭鹵,臭的東西中,最特殊的是臭莧菜桿。這樣的吃法也許是當地的特色,但是莧菜梗味道不錯,將其掐成段,鹽漬一下,與紅辣椒爆炒,辣辣脆脆,濃濃的原生態味道,下飯好菜。
杜甫:“登于白玉盤,藉以如霞綺。莧也無所施,胡顏入筐篚……”雪白盤櫻桃紅的,如霞如綺,像一首絕美的音樂。宋陸游《園蔬薦村酒戲作》:“身入今年老,囊從早歲空。元無擊鮮事,常作啜醨翁。菹有秋菰白,羹惟野莧紅。何人萬錢筋,一笑對西風。”豪放之氣,溢于詩間,山珍海味又何妨,我這一盤野莧菜羹,三杯兩盞薄酒,可盡享人生的清幽。
野莧菜其實是一味中藥,降血壓降血脂,是腸胃的清道夫,對減肥效果尤佳,于是我這位想瘦成竹的女子特別偏愛莧菜。李時珍《本草綱目》中說:“六莧,并利大小腸。治初痢,滑胎。”《隨息居飲食譜》也說:“莧通九竅。其實主青盲明目,而莧從見。”“莧”音同“見”,亦有見意,吃了其黑色的小果實,可明目。有一故事:清代雍乾年的名醫徐大椿曾見一人患頭風,痛得不得了,兩眼都要痛瞎了,到處求醫無效。有一天遇見一個鄉下人教他用十字路口及屋邊的野莧菜煎湯,裝在壺內,將兩眼就壺口蒸汽熏之,漸至見光,終于復明。莧菜是人見人愛保健食品。
莧菜,普通的與“野”聯系在一起,汲天地日夜精華,成全于生命之時是那鍋豬食,那盤菜,那劑藥。不是野人參和野蟲草。
如今土菜野蔬之風盛行,呼舊情返璞歸真,一是對綠色的期盼,一是對淳樸自然的向往。
莧菜,永遠是最樸素的味道。
莧菜,你永遠是丫頭心中那道最美味的佳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