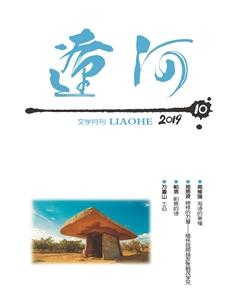村莊的時間
祿永峰
跟別的地方沒有什么不同,村莊的時間也是一天一天過的,一年一年過的。一棵樹是這樣,一頭驢是這樣,一場風是這樣,村莊的每一個人也是這樣。沒有誰一下子長大,也沒有誰一下子變老。也不論誰,快樂的時候時間是那么一點一點過著,痛苦的時候時間還是那么一點一點過著。一個人一輩子中,快樂的時間拉不長,痛苦的時間裁不短。這一切,都是由村莊的時間掌握著,由不了自己。
我第一次偶遇鋸倒的一棵大樹,令我驚訝無比的是,一棵樹倒在大地上比一棵樹聳立在大地上顯得高大威猛多了。其實,鋸倒的這棵樹,跟生長著的時候一樣粗壯。但是,它一旦倒下了,我怎么看怎么都不像原來生長著的那棵樹。這是樹的神奇,還是一個人的錯覺?站在一棵樹前,更讓我驚訝無比的是,樹樁上出現一圈一圈的年輪,是那么清晰,它是樹生長的年輪,一年長一圈,從里到外,樹生長了多少年,就會留下多少圈。一棵大樹,生長了幾十年,把幾十圈的年輪留在樹身上。我驚訝的不是樹身上那些清晰的年輪,而是一棵樹的好記性和好耐力,它竟然能夠把自己生長的全部時間留痕,留據。從里向外,毫不馬虎。我不知道,一棵樹生長一年留出來的年輪,跟村莊一年的時間在長短上是否一樣,跟一個人一輩子經歷的時間在長度上是否一樣,樹所走過的樹路,它是靠什么測量時間的呢,是靠太陽、月亮、一場風、一場雨,還是靠樹自己?由此,我不知道,大地上生成的一株株莊稼,是否也會像樹一樣,也會在自己的身體上留下自己的日輪、月輪或者年輪呢?還有,除了村莊的樹、莊稼之外,存在村莊天地間的其它事物,又是如何記述自己的生命輪回?
或許,正是村莊大地上的一切生命留痕,因此在村莊的所有時間里,誰也不愿虛度自己存在村莊的光陰。樹急著趕自己的樹路。牛急著趕自己的牛路。風急著趕自己的風路。雨急著趕自己的雨路。村莊的人也一樣,急著趕自己的人路。他若是游手好閑,不好好趕自己的路,一個人便會像一塊莊稼地里的一根雜草一樣特別顯眼,村莊人一眼便看得見。被村莊人所指的人,一定會渾身不舒服,并感覺不好意思的。畢竟,大家都生活在同一個村莊的同一塊大地上,都耕種著村莊的田地,都走著同一條村莊的道路,都喝著同一口井里的水,都呼吸著一個村莊新鮮的空氣,自己有什么理由盡失一個村莊人淳樸的品質。過日子,就是得有份好耐力。磨刀不誤砍柴工。把鋤頭擦亮,把鐵锨擦亮,把鐮刀擦亮,把所有倚靠在黃土窯里的農具一一擦得锃亮,最好能夠照得見自己的影子。一戶人家的光景就是需要從一件件走過村莊大地的農具獲取。
一個村莊人,一天干不完一年的事情,一年干不完一輩子的事情。在大地上勞作,投機取巧不行,弄虛作假不行,強取豪奪不行,還得一步一步來。這個道理,生長在村莊大地上的每一塊莊稼,似乎比人還明白得多。麥子,跟村莊別的農作物一樣,也是要生長夠時間的。秋天播種,出苗,冬天盼望著一場厚雪落在上面,好蓋著一層雪白的被子擁擁擠擠、暖暖和和地過冬。第二年春天,驚蟄,抖擻抖擻精神,伸展伸展筋骨,接著生長。到了夏天,布谷鳥叫著“算黃算收”“算黃算收”,生長了四季的麥子,才算長成。經歷四季的時間,成熟的一顆顆麥粒,吃進肚子,果然比村莊大地上成熟的其他糧食耐飽。麥子也便成了村莊人的主糧,磨成的面粉蒸成饅頭或者搟成面條,兩天不吃,肚子便感覺空落落的。改天趕緊吃一頓,肚子里立馬實在了不少。也因此,村莊人自詡“面肚子”,這話擱在村莊,的確不假。我想,如果村莊的麥子生長周期短一些,那么村莊人食用麥面后會不會感覺沒有那么瓷實呢?
同樣,那些村莊里的樹,之所以能夠當屋脊上的檁、扛起檁的梁、撐起整個屋頂的椽,原因或許就在于,每一根檁、一架梁、一根椽上,沉淀著不同的時間。
清晨,村莊比城里來的稍靠前一些。城里人還在睡覺,村莊的雞已經叫過第三遍。雞似乎并不是平白無故的叫,每一遍叫聲傳到村莊人耳朵里,村莊人睡意朦朧中便曉得該是什么時間了。雞叫過第三遍,距離黎明的曙光也不遠了,男主人也該起床準備到農田里忙活了。女主人呢,也趁早安頓家里。剛剛邁出屋門,豬哼哼著醒了,羊咩咩著醒了,牛哞哞著醒了,雞也從架上跳下來,朝著女主人奔跑過來。一夜了,它們都餓了,紛紛用叫聲向著主人傳遞著信號。忙活好一陣子,才喂完它們。這時候,女主人又要趕在孩子睡醒之前抓緊準備早飯。待早飯好了,太陽已經跳到西邊窯門的高窗上了。一束束陽光經過高窗打在窯壁上,亮亮的。尿脹醒了的孩子,哭哭啼啼地喊著母親抱著自己到院子撒尿。母親走到跟前,朝孩子屁股打了一巴掌說,都什么時候了,太陽都快照到屁股上了,還不起床?挨了打的孩子不敢再哭哭啼啼,剛剛吵醒的其他幾個孩子,乖乖的自覺起床,各穿各的衣服,一聲不吭。母親讓大點的孩子到地里去喊父親回家吃飯。喊父親吃飯的孩子一點不敢怠慢,一溜煙似的跑到地頭大聲喊,“我媽讓你回家吃飯!”地中間的父親應了一聲,地頭上喊話的孩子已經轉頭朝家的方向跑去了。父親回來了,幾個孩子坐了一炕,父親沒有坐定,誰也不敢動筷子。
早飯畢,父親喝了幾杯濃茶,緊緊張張的到地里去了。母親把飯菜搭在鍋里,等上學的哥哥和姐姐放學回家吃飯。還沒有上學的孩子,母親帶到了地里,大一點的幫助大人干一些力能所及的農活,小一點的去地中間像個能動的草人一樣,穿梭,趕鳥。太陽一點點升起來,趕鳥趕累了的孩子,悄悄地想坐在一塊農田旁邊乘乘涼,可是陽光射下來,他還是顧得了屁股顧不了頭。孩子向著母親嚷嚷著,太陽照到頭頂啦,晌午啦,回家啦!母親嘿嘿地笑著說,“我這瓜娃,嫌熱,咋不會跑到地頭那幾棵樹下涼涼!”孩子到樹下,感覺樹下就是比地里涼快。樹上的鳥,像他一樣乘涼。偶爾叫一兩聲。樹上的鳥不用趕,他涼他的,鳥涼鳥的。不知不覺,他竟然睡著了,幾只鳥的糞便掉到身上,他卻渾然不知。
毋容置疑,村莊的時間是精確的,它不僅能夠精準到時,還可以精準到分,甚至秒。例如,現在正是三伏天的晌午時分,村莊的大地似乎冒著滾燙的熱氣,頭頂頂著烈日,人行走在農田里,整個村莊像個大蒸籠,在農田里忙不了一個來回,脊背上的汗水一層接一層從衣衫上滲了出來。牛和驢累得熱得打不起精神。看來這個點是該回家的時間了。村莊四面八方在農田里忙活的人、牛和驢,紛紛從農田里趕到了村頭,然后不慌不忙地各回各家。家家戶戶窯頂的煙囪里,開始慢慢悠悠地冒出一股股青煙,彌漫過整個村莊。這是村子里的炊煙,除了一股淡淡的刺鼻味,還飄散著一股炒蔥花味。正是這個味!三伏天調一鍋酸湯或者漿水湯,女主人搟了幾案子細面,面條筋道細長,挑一些,盛上酸湯或者漿水湯,連吃三碗,夠爽!飯后瞇一小會兒,待村莊的騰騰熱氣隨風飄走一些,人們又不約而同地趕去農田里忙碌了。直到忙到傍晚時分,忙完早點的人,太陽落山前回家了。田里的農活還沒有忙完的,一直忙到摸黑。反正晚上的村莊涼爽多了,在農田里多忙活一陣子,免得第二天曬晌午的太陽!
一到晚上,村莊似乎一下子進入了“休閑”模式。這是忙碌一天之后最輕松的時候。走路可以慢下來。吃飯可以慢下來。隨便找個地方坐下來,晚飯比較簡單,算不上是一頓正餐。這是村莊人一天里的最后一頓飯,吃點晌午剩下的剩飯,或者熬一些小米粥,涼拌一碟菜,一人端一碗粥,一人夾一個饃,這便是村莊人常說的“喝湯”。可謂名副其實。村莊人這一頓晚餐,絕不會像城里人,不僅把晚飯當正餐吃,而且零點過后還可能走上街頭吃點夜宵。村莊的后半夜,人是幸福的,牛驢馬羊是幸福的,夜空的星星和一棵棵樹、一株株莊稼都是幸福的。它們和人一起融入村莊的深處,蓄精養銳,沉淀時間。我不知道,一樣的雞仔,成長在村莊成了土雞,蛋成了土雞蛋,售價卻比現代化雞舍養的雞、下的蛋貴出好幾倍。其中作祟的,不是別的,恐怕正是村莊的時間。
時間留給村莊的味道,像美酒,陳醋,黃酒,借助大地之氣,日月之光,醞釀著,時間越久,味道越濃越香。這份濃香,綿延不絕,足以從時間的這一頭奔到了時間的另一頭。一年兩年太短,十年八年等得及。大地上生長的一棵棵杏樹、桃樹、核桃樹、棗樹,栽種下這些果樹,村莊人何嘗不是在時光中追隨來自大自然的美味?村莊人知道,一棵果樹從幼苗長成果樹,從果樹到掛滿枝頭的果實,桃樹要等待三年,杏樹要等待四年,核桃和棗呢,竟然要等待十四年之久。一個人一輩子有多少個十四年,可是,村莊人在莊前屋后不僅僅栽下了桃樹和杏樹,還默默地栽下了核桃樹和棗樹。或許,直到自己老了,才能看到那些成熟的核桃和棗。我知道,村莊人栽樹,似乎不全是為了自己。一個人老了,給子孫后代留點什么好呢?還是留幾棵核桃樹和棗樹吧,子子孫孫結婚的日子,怎么能少了核桃和棗呢。核桃象征著美滿、和美,棗子象征著早生貴子。暖暖的婚床上,壓著核桃和棗——早(棗)想和(核)你在一起。這寓意,多好!多美!新婚之夜,新娘哪知道床下面藏著核桃和棗,待她剛剛美美地躺下去,墊的脊背生疼,新娘不懂問新郎,新郎說,這是爸媽留給咱倆吃的。吃了核桃,咱倆就會美美滿滿;吃了棗,咱倆就會早生貴子。新郎話音剛落,新娘卻羞得鉆進了被窩。新郎趁機也鉆了進去。在被窩里,夫妻倆一會兒摸個核桃,咬碎,吃了;一會兒摸個棗子,吐出棗核。藏在床上的一堆堆核桃和棗子,夫妻倆吃了多個夜晚。自然,每一對夫妻,兒子會有的,女兒也會有的;孫子會有的,孫女也會有的……村莊就是一對對夫妻新婚之夜吃核桃和棗子,在時間的長河之中一輪一輪地延續著。
村莊的時間,不屬于村莊人獨享,它屬于村莊的萬物和大地。包括,年復一年,豐收的大地之上盛開的一片片藍天和一塊塊白云,它們都屬于時間在村莊的沉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