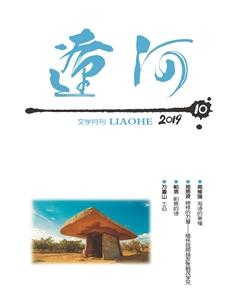回到童年
馬河靜
張王李趙四大酒星喝酒,從中午喝到太陽落山。
張狗蛋硬著舌頭說:“越喝越沒味了,一點也不甜。”
王月娃說:“酒甜?呵呵——沒有西瓜甜。”
李磨子說:“西瓜甜,走,咱們出去吃西瓜。”
華燈初上,瓦斗抬頭看了看路燈,迷茫地說:“太陽怎么這么低?”
賣瓜的是個青年小伙,穿的白背心上印著紅色“7”字。他的拖拉機斗里只剩下三個貨底了。月娃挑了一個切開,狗蛋嘗了一口說:“酒沒酒味,瓜沒瓜味。”“啪”地一下把一牙瓜扔進了垃圾箱。月娃說:“就是,這瓜沒一點甜勁。嗨!你說現在到底咋回事,吃啥都沒先前的味道呢?”
賣瓜的不愿意了:“我經常在這兒賣,沒有一個人說不好吃,像我這瓜不好吃,啥瓜好吃?”
月娃說:“偷——偷瓜好吃。”
狗蛋說:“對,偷的瓜好吃,那年咱們去偷我家的瓜。你們跑了,我爹把我打了一頓。”
大家想起小時候在月光下光脊梁偷瓜的事,一起開懷大笑。
賣瓜的說:“你們真的想吃好瓜?走,我拉你們去摘,人家的瓜比我這好的沒茬。”
于是王月娃攙著趙瓦斗,他們坐上了拖拉機。賣瓜的一邊開車一邊說:“咱去的這塊地北頭有個墳頭,旁邊種著三苗西瓜。那瓜甜啊,天上沒有地上缺,就是主家不賣。主家是村長,問題大著哩,給小寡婦……”
“別說了,走,偷他狗日的!”磨子大喝一聲。
上到南嶺,賣瓜的停了車,指著坡下不遠的瓜棚說:“見到沒有,北邊那個墳頭,去吧。可別說是我給你們拉來的。”說罷,他開上拖拉機“突突突”向西走了。
磨子說:“聽我指揮,瓦斗你還看衣服,狗蛋你還照坡,我和月娃倆去偷。”說著他脫了褲子和汗衫,溜到坡下,爬到地上像壁虎一樣向墳頭爬去。月娃也脫光了衣服,緊跟在后面,眨眼兩個人不見了。
不大一會兒,倆人各抱了個竹籃大的西瓜爬了回來。磨子悄悄地說:“撤!”倆人就往坡上爬。月娃走在前面,腳下一滑,西瓜順坡轱轆到了坡底。坡上的瓦斗看見了,順坡滑下來說:“我——我也去偷,不然吃,吃時,沒有我的份。”他起身腿一軟,從坡上栽了下去。稍頃,只聽他在坡下吆喝:“哈哈!我拾了個大西瓜。”磨子咬著牙說:“吆喝個啥!”
三個人在坡上等了半天,不見瓦斗上來,磨子返身下坡拉瓦斗,只見瓦斗正拿著一大塊瓜啃,吃得滿臉滿胸膛流水。磨子也拾了一塊,一嘗,就是甜。兩個人把瓜瓤吃完上了坡,只見狗蛋和月娃倆打開西瓜在猜枚:“哥倆好啊!”磨子說:“小聲點!”話剛落音,只聽一聲大喝:“干啥哩!”只見一個老頭手拿羊叉,氣喘吁吁從坡下上來,說:“你們,你們一大把年紀了咋學會偷瓜了?”
這個時候,四個人面面相覷,似乎睡醒一樣。瓦斗說:“這是啥地方?”
磨子呵呵一笑,對老頭說:“聽說你是村主任?”
老頭說:“誰給你說我是主任?”
瓦斗說:“開——開拖拉機,穿背心……”
磨子踹了他一腳,說:“老鄉,我問你,你這瓜為啥真甜哩?”
“你們摘的是瓜種啊!是我培育的新品種,知不知道?你們想吃,進瓜園管飽吃,也不能干這種下三濫的事吧!”
狗蛋說:“我們喝醉了,想不到摸到了你門上,嘿嘿,真是緣分啊,你開個價,說多少錢,我們給你!”
“多少錢?十萬!”老頭說。
“你留的是瓜種,肯定值錢,不過,也不會比金子貴吧?再個,我們現在去哪弄十萬?就是有,給了你也不好意思要,是吧?”磨子說。
正說著,一個年輕人趕來看了磨子說:“你是公安局——王局長吧?”
磨子說:“我當過局長,不過我姓李。”磨子指著月娃說:“他是王局長,農業局的。我們都退休了,退幾年了。”
月娃說:“我吃了你的瓜,覺得它像“安農二號”品種,個兒大,含糖量達10—12度,汁多,不倒瓢,就是抗性不高,容易裂。”
老漢說:“老天爺呀!你算說到地方了,我正愁哩,你看這一地上萬斤,明天氣溫高,中午又有猛雨,西瓜熱脹冷縮,非炸爛不可。”
月娃說:“你可以讓它與“黑美人”品種雜交,結的瓜韌性強,耐儲運。”
磨子突然說:“瓦斗,我的褲子哩,把手機拿出來。”瓦斗提起衣服摸了摸說:“沒有手機呀!”狗蛋說:“估計是掉拖拉機上了。”
老頭說:“你們是坐小賴的拖拉機來的吧,這個狗日貨,好吃懶做,把我的瓜拉去賣了三天,寧說賣賠了,不給錢。”
磨子說:“月娃,用你手機給我兒子打電話。”
月娃打通了電話遞給磨子。磨子對著電話說:“兒子,明天你來南坡拉一萬斤西瓜,給你公司員工分了。啥——啥價?人家要啥價你給他啥價?記住,不準搞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