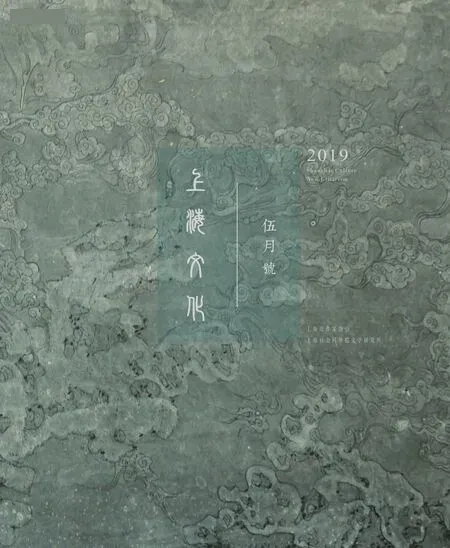苦行者與高溫下的寫作 紅柯《太陽深處的火焰》及其他
張春梅
以西部之名
提到紅柯,就會有這樣一個公式呈現:新疆+關中,并因“騎手西去”而凝結為“西部”。引申下來首當其沖的問題則是:“西部”對紅柯到底意味著什么?
紅柯的世界明顯分為兩個部分:新疆(常常與西域混為一談,并垂直聯系著中亞、波斯文化)與渭北平原,這樣一種建立在大漠與平原之間、原始的粗獷與世俗的隱秘之間、游牧文明與農業文明之間的架構,充滿地域決定論的味道。然而,今時今日,當時空在迅疾變遷的訊息、交通時代早已改變了過去的形勢,打破地域界限的互聯之網已然混入了各種內容,進而在人心世界造就各種新的不同以往的折疊。紅柯筆下來自渭北的張子魚(《喀拉布風暴》)、從烏魯木齊來的姑娘(《雪鳥》),甚至那位來自大漠深處的吳麗梅(《太陽深處的火焰》),都不是簡單的新疆或者關中能夠說得清楚。張子魚獨自漂流到新疆,不是為了尋找,而是要逃避那些撲向他的愛情,當與精河的沙塵暴相遇,這種簡單粗暴的力量使他駐足。精河,生命之河,地精,生命之華,在整個《喀拉布風暴》中紅柯反復地不厭其煩地吟哦著的字眼,暗示著膽怯的、無法去愛的張子魚將在這自然界強悍的偉力之下重新找回生命力的無限可能。當關于張子魚的第一個描述展開時,讀者基本可以確定此種可能已然變為現實:“臉上那些被風沙打磨過的傷痕平添了幾分男人的粗獷豪氣”。而由張子魚開啟的《燕子》自此成為全文的基調,它聯結起上世紀初的斯文·赫定,生長在新疆精河的葉海亞,并將中原之地的陶亞玲呼喚至大漠胡楊之上,進而獲得地精之子。從這個角度看,大漠、胡楊、沙暴為這些蕓蕓眾生托底,實際上,這些生靈都不是一清二白的底子,都有屬于自己的情感世界、生活世界,是滄桑者,也是loser,是身負創傷的一群。對于創傷的療救,是否必須來自西部的自然之力,也就是說,這種理論是充分條件,還是必要條件?在我看來,根本的怕不是所謂的地域,而是創傷體本身。但這樣一來,為紅柯所青睞的、玩味不盡的“西部”就變成了劇情展開的巨大布景,掛在那里,任劇情轉移而巋然不動。對此也可以做這樣的理解:所謂的喀拉布風暴、太陽深處的火焰、西去的騎手、雪鳥,都是為拷打靈魂而設的極端生存之境,當生與死就直截擺在你面前,你是否還有什么折疊藏著掖著的可能?你是否還會去玩弄心機、聽任愛的河流干涸?于此,“西部”成了證明“無法消失的河流”的一個必要條件,卻未必充分,世事人心哪是一個考驗就能畢露原形!
《太陽深處的火焰》中的吳麗梅和徐濟云、吳麗梅和王莉、吳麗梅和徐父就構成了布景和劇情的關系。與《喀拉布風暴》相仿,雖然背景從生命之河——精河挪到了塔克拉瑪干的深處塔里木羅布荒原,這一變動更加傳奇、浪漫而荒遠,也更具想象和加工的可能,關于這一地域的描寫與吳麗梅的關中生涯共震蕩。羅布荒原變成一種生存鏡像,時刻與吳麗梅的現實生活相映照,有這層鏡像,吳麗梅的感官便有了尺度,有了標準,并最終重返沙漠深處,其最終歸宿——太陽墓地——成了見證太陽之子的眼睛。吳麗梅來了,又去了,留下的只有那件來自原始羊毛由她親手編織的毛衣,穿在徐濟云身上成為裝點學問的“皇帝的新衣”。這件衣服幫助徐濟云找到了安穩魂魄的力量,也讓王莉安心:還是那張蒼白的臉,還是那雙失神的眼睛,在粗羊毛的掩飾下還是顯露出那么一點點生機(《太陽深處的火焰》)。然而,這些都不是重點,敘事的重點顯然還是世俗人心,相比之下,吳麗梅的極西之地,不管是從徐濟云聽者的角度,還是吳麗梅的講述,更多的恐怕還是敘事者背后的作者樂此不疲的敘說,這地兒被高高掛起成為對照現實的充滿神采的背景,它在那兒,但并不左右世事人生,活死人、蔫人、碎善狗子客……依然在那里樂此不疲,饕餮般張牙舞爪。因此,比較起來,地域重要,還是拷打世俗人心重要,從我的觀看角度,紅柯也把“西部”當成了背景,而他所關注的從來都是那些可惡的碎善狗子客們,是在每一個小的社會單元里都可見的“蔫人”,“志殘”者們。也只有看到這點,才能理解紅柯寫作的原因。若還將紅柯簡單列為西部作家,或者新疆作家,無論對西部,還是對紅柯,都是不準確的。
看到這點,再來看紅柯的寫作,其浪漫主義情懷愈加強烈而凸顯。在他的文本中,有一種強烈的渴望,渴望從現實中拔出,像他所崇拜的的斯文·赫定,去亞洲腹地,去探求未知,去冒險,去做一個英雄。他渴望能像他筆下的吳麗梅敢于從大城市退回最偏遠之地,遠離塵世,遠離人世,與大漠為伍。他渴望像《雪鳥》中的兒子娃娃在冰雪中與嚴寒搏斗,生命不息,戰斗不止。但是,他最多成為《喀拉布風暴》中的張子魚或者孟凱,或者那個冬夜來到冰山腳下的姑娘,而最終他依然生活在蠅營狗茍人世中的徐濟云、周猴、老徐、王鏡、朱自強……中間。這恐怕是生為紅柯的最大痛苦:精神與生活分在兩處,只有不斷分向尋覓,卻難有匯合的可能。
在這個意義上,面世于2013年的《喀拉布風暴》盡管有始終回蕩著民歌《燕子》的情韻,有斯文·赫定對中亞大漠終生不改的赤誠,但依然充滿了對未知的探索,關中人未必明白,新疆人也未必清楚,只有當那具有巨大審美力量的聲音(對于精河人葉海亞)、席卷一切的沙暴(對于張子魚)、有穿天之力的地精(對于孟凱)、生命不息的胡楊(對于陶亞玲)開始撞擊并掀翻以往所有認知的時候,生命之力歸來。這種力量在《喀拉布風暴》中定位在生命之根、愛的無限力。陽剛之力將所有的虛寒陰冷驅除干凈。相比之下,發表在2017年《十月》第4期的《太陽深處的火焰》已經不再尋覓,它知道,這種力量就在那里,但“虛寒”的人們畏懼它、遠離它或在形式上借用它,就像那件成天掛在徐濟云身上的毛衣。假如《喀拉布風暴》、《雪鳥》等作品還有探索和渴求,在《太陽深處的火焰》則變成一群“活死人”的鬼蜮之舞,紅柯眼中的現實,他對人性的期許,他的理想世界就都只能在不斷重復敘述的胡風、黃土、大漠、樓蘭、福樂智慧中安置,直至老子出關西行。由此看,這部作品的現實性和悲劇性超過了他之前的系列作品。作者很沉痛。
于是,紅柯找到了一個永恒的主題:愛情。這些生活世界,或者靈魂世界的loser,唯有愛情能夠拯救之。在《喀拉布風暴》里,失去愛的能力的張子魚、為愛而迷惑的孟凱、以情報方式來探查男人心的陶亞玲、對張子魚一歌鐘情的葉海亞,這些來自不同地域的人們,都面臨著生命的難題。紅柯將這些難題命名為:無法消失的河流。或許干涸,但曾經存在。這預示著一種追尋的必然。他相信只有無邊無際的沙海、烈日才能讓日漸冰涼的心靈復蘇,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紅柯就像一個苦行者,他要讓自己的身體置放于最激烈拷打和煅煉之處,要被火燒,讓火烤,只有在這里,才能與綿密的世俗人情與人性之“小”劃清界限,才能蕩滌心靈,獲得寧靜。在一個個文字中,紅柯化身為一個殉道者或者精神疲軟志殘拯救者,他要讓“整人”者和“蔫人”現行。或者,他所生活的環境充斥著這種人,他要做的,是要尋找一種力量改變它,挺直它。各種力量中,能燃燒一切的愛情矗立在那里。火熱的愛情!
無論愛情,太陽深處的火焰,人跡罕至的大漠,席卷一切的風暴,或者雪鳥,或者太陽墓地,在紅柯的思想體系里,都直接指向先驗的具有本質意義的內容,每一個極烈之地都有強烈的想象意志在內。然而,無人或罕有人至之地到底有多少拯救的可能?或者,滾滾紅塵中的男男女女,是否需要那來自同樣深處的火焰?是否來自西部的騎手真的具有改變現實的力量?所有“是否”的關鍵在于相信,紅柯相信自己的理想精神本身恰恰是現實所缺乏的,這從而成為紅柯寫作的態度和方式:他無法決定他人“是否”相信,但他能做到而迫切要做的,是不斷地說,不斷地吟唱,甚乎吶喊……當我們傾聽西部,分明清晰地聽到節奏不同的呼喊早已以各種形式出現,周濤之“沙漠深處的參天大樹”、昌耀的“太陽說,來,向前走!”紅柯聽到的更加遼遠,一個個波斯的苦行詩人、為愛瘋魔的馬杰農、跋涉西東的玉素甫·哈斯·哈吉甫,還有很多,這幾乎構成一個紅柯世界的方陣,以交響樂般鳴響在紅柯的文字,千錘百煉,密密匝匝。這種來自西部的聲音響了許久,在新絲綢之路重啟的今天,是否已經被人們聽到,或者人們愿意靜下心來去傾聽?答案依然未解。無論如何,紅柯以他的“不斷呼喊”成為諸多聲音中特殊的一個。只是,以西部之名,終使得西部成為一顆“芳香而神秘的蘋果”(徐濟云關于吳麗梅的想象),而其實存也變得一片虛空。
高溫下的寫作:照耀、暴露與呼喚騎手歸來
從以上關于紅柯思想的分析可以窺知,對現實人生的認知引發從《少女薩吾爾登》、《雪鳥》、《喀拉布風暴》到《太陽深處的火焰》的變化,后者成為紅柯寫作的終結,而對人性寒涼的諷刺、批判也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變的,是以“西部”作為參照的高溫錘煉下的生命體驗,這樣的痛徹、如此的渴望決定了紅柯的寫作方式和表達。
在《喀拉布風暴》展開不久,一句針對張子魚的天問橫空而來,“你怎么那么早就失去了對美好情感的敏銳的感覺?”如何恢復對生活和美好情感的敏銳感,這是紅柯不斷對自己提出的問題,并以直截的方式建構在人物的情感結構之中。這種“敏銳的感覺”在《太陽深處的火焰》一開始便借吳麗梅的手呈現:好多年以后徐濟云還那么清晰地記得電流穿身而過的感覺,接著是火焰,從血液里噴涌而出的熱浪在熊熊燃燒,燃燒到極致竟然感覺到一股可怕的冰涼,正是這種冰涼,讓他看到了吳麗梅身上散發出的光芒……這種生命之光很快就從吳麗梅冰涼的小手轉化成柔軟細膩的羽毛……瀑布般的晨光撲面而來,吳麗梅羽毛般的小手嘩啦一下成了翅膀……這是故事的開頭,也是紅柯講故事的語言特色——用“對美好情感的敏銳的感覺”來體現思想、展示人心。
正如我們前面指出的,在《喀拉布風暴》時期的紅柯,還充滿對未知世界的探索渴望,他相信,在他看不見的地方有一種力量能夠恢復自己對美好生活的感覺,正是這種對現實的“不足”,結構起全篇的人物關系結構:葉海亞、孟凱、張子魚。緣起在于葉海亞,敘事者顯然偏愛這個女子,或者說正是這個女子的“不足”之感帶動了改變現實的可能:“葉海亞看了孟凱一眼,孟凱吃驚地往身后去看,身后沒有人呀,可他明明感覺到葉海亞的目光穿越了他,葉海亞在看一個極其遙遠的地方。”葉海亞的行為促發了孟凱的疑惑,作品的原動力由此獲得。這與本身就是陽光就是火焰的吳麗梅不同,身處沙暴身處的葉海亞并沒有和地域融為一體,但充滿面對未來的無限可能,她的“目光”帶著讀者走向沙漠、胡楊、駱駝直至地精——人之力的根源。
以感覺,尤其是關于愛的感覺開篇,接下來紅柯的文字便充滿來自“西部”的味道。這里的“西部”大概有以下內容構成:胡風、黃土、毛驢、牛糞、羊羔、幽默、太陽墓地、羅布泊、大漠美女、樓蘭美女、曲子、玫瑰等等,并在敘述中擔負起超敘事的功能。這樣一種理想精神,進而投射到具體的人的身上,曾在這種境界中行走過、愛戀過、煅燒過的人們就此從歷史的深處走來,并凝結為作品中一個不必出場但精神豐沛無比的人物。《太陽深處的火焰》中有著“西部”和“關中”雙重體驗的吳麗梅是最集大成的一個,《雪鳥》中的破冰人和老母親則是純粹神性精神的代表,《喀拉布風暴》中的葉海亞、張子魚、孟凱等是正在頓悟的一群。這些因“西部”而獲得美好情感的人們共同高揚起生命的熱旗,并以此與同時進行的現實生活敘述成為對照的兩極,以此暴露現實中隱秘的丑陋,和正大光明力量的缺失。總之,在紅柯的筆墨里始終占據至高精神位置的必然是古之西域,或今之西部,這在敘事中成為反照現實的鏡子,是紅柯的精神標本和旗幟。顯然,這與現實中的西域或者西部未必重合,而是打著紅柯印記的極西之地。
在紅柯的作品中,顯明的陰陽之比較觸目驚心。陰如果代表黑暗,陽就是太陽,而太陽深處的火焰就是熔化和逼視陰暗的生命之力。大漠、西域、絲綢之路,是火之所在。這又讓我看到維克多·雨果的影子,雨果那句擲地有聲的“黑暗與光明同在”似乎就在紅柯的文學視界周邊環繞,但紅柯很少提到這位作家,在紅柯的表達譜系中反復展現的是中古時期的波斯詩人們,這倒讓人有索羅亞斯德教——一個崇奉太陽的宗教的聯想。此教在武俠小說《倚天屠龍記》、《笑傲江湖》中也叫正大光明教,或者明教。而有意味的是,反對折疊人世的紅柯所主張的其實就是正大光明。唯有火,能逼出一切的蠅營狗茍,讓碎善狗子客們現行。維克多·雨果與魯米們,在精神上與紅柯連綴成了一個整體,即:烈火焚燒一切黑暗。
而有了兩樣生活、兩種生命形態的大結構,敘述的基調也就確定了下來。講到大漠(這是必講的),調子是昂揚的,仿佛貝多芬的《歡樂頌》在歡唱,使整個語境充滿象征感;到了現實篇,調子開始尖利起來,卻也和緩得多,作者似乎有更多的余力來講述現實人生中的褶皺、隱秘和人心算計。人物也被分為兩極,如《太陽深處的火焰》,一種以“西部”為生命之基,如吳麗梅,另一種則如徐濟云,深通“立世”門道,卻不過是從“墓塋”過來的死人。于是,關于行動者活著還是死了的討論就成了關于徐濟云及其群屬的最大特征,諷刺的意味自然在言語間濃烈起來。死了的人依然活著,活著的人已經死了。敘述者反復提及徐濟云中學演講《一塊銀元》的情景,其中關鍵早已不是原作的批判,而是利落地指出徐濟云的“蔫壞”早在體驗吞食水銀的那一刻注定。而徐濟云與他一手打造的“大師”,“明星”周猴等在精神實質上屬一類,都是行走著的活死人,猶如果戈里筆下的死魂靈。周猴痛說革命家史、徐濟云非得把吳麗梅親手編織的毛衣穿在身上才能感到身上一點光亮,作者評價為:“一點點生機”和“生命的火焰”,其意不言自明。
關于學術場現行記,是《太陽深處的火焰》最震撼人心的部分,相當有批判性。以徐濟云為中心,他的碩士和博士環繞他構成一個學術場域。我們知道,紅柯本人就是大學教授,作為親在者和見證人,他對大學群像的勾勒更見真實、徹底。弄虛作假一詞,應該可以作為這一群體的靈魂圖譜之一面,也是他們的生存法則。徐濟云與佟林教授的關系,類似“借魂”,“畢竟是不同的兩個人,里里外外衣服全換,完全是佟林教授的風格”,猶如“神靈附體浴火重生”;而王勇博士與其導師徐濟云的關系則是借中之借,所傳承的便是無中生有,把不起眼的東西打造成奇觀,就像給活人周猴作傳,學術場儼然與造星運動一般。這種描述可謂辛辣之極!
作者并沒有僅僅局限于學術場,兜來轉去,大小官場、鄉村政治也都被納入其中。文化官員師兄張林,玩弄同事于股掌的供銷社小股長老徐、追求傳宗接代不遺余力的老徐,沒有什么本事卻能在皮影藝術研究院某得正式職位的周猴,等等,統統奉行或被奉行一套“整人”游戲:排除有能者,制造“志殘”者。這些“高”手段被農民王勇的堂兄王進學來并活學活用、發揚光大,這個農村的“能人”,先把王勇蔫了一輩子的老爹打造成土皇帝,為自己謀得上層資本,接著利用腦殘、智障驅逐還能有腦力和語言表達能力的身體殘疾者。王進這個鄉村loser的上位,被描述為“見過徐濟云教授之后如夢初醒”,此語不失火辣!對于這些人物,紅柯的敘述不疾不徐,對這些充滿腦力的“整人”把戲從知識分子的傳教,到周圍這群人的心領神會,全都做了細致交代。這樣完備的“敘述”與關于吳麗梅的敘述交替出現,即見出鋒利,也更顯紅柯之痛。
從光明到黑暗,從關中到羅布荒原,從學校到西部小鎮,這些空間的變換所依存的大可歸納為美丑對照原則。這一原則必然要求變換敘事對象。《喀拉布風暴》的敘事者雖然主要是孟凱,但其目光不斷在新疆小伙和渭北小伙之間游走。尤其有意思的是,渭北小伙張子魚的西域探險家知識儲備原本不應該出現在大篇幅的敘事陣營,但敘事者顯然有意將此呈現出來,于是斯文·赫定的故事便開始占據大段的敘事空間。這還不夠,作者就是要讓現實中的人物去追尋斯文·赫定作為探險家的足跡,于是渭北的部分和新疆段落便交替成為敘事展開的主要地帶。斯文·赫定的探險史成為一個重要的文本參照對象。比較《喀拉布風暴》和《太陽深處的火焰》,前作的突轉始終圍繞的是對大地之精和生命之力的追尋,后作雖然將吳麗梅高高舉起,卻并沒有合適安放的現實位置,光明的太陽之火似乎與現實的利益關聯拉開了距離。從這個意義上看,從《喀拉布風暴》到《太陽深處的火焰》,紅柯的關注對象是有所轉移的,他既保持了一貫的對“西部”的篤信,但現實中人的殘忍、無恥以及種種被薩特描述為“惡心”的行為,明顯成為他思索和意圖改變的重點。當年西去的騎手,被重新詢喚歸來,只是,歸去來兮之間,能否在眾多人心留下痕跡,卻是一個未知數。畢竟,出現在作品中的吳麗梅只是一個活在徐濟云記憶里的飄蕩在太陽墓地的亡靈。
借著對紅柯的閱讀,我想簡單追溯一下關于西域的文學想象史。漢唐氣象大概是我們記憶的起點,那時的西域既有大漠,更有血腥和戰爭,蠻荒是其底色,異域風情是其活動的背景。此情此景,至元西征達至頂點。來自草原的成吉思汗打開了向西的門戶,在世界開創了蒙古的時代印記,那是能征善戰的巴圖魯,是“笑談渴飲他人血”,但“胡虜”的形象卻在強大的武力之中再次加強。移民、囚徒、極西發配之地配合著不開化的“胡虜”長期占據著關于西域的形象位置。19世紀末20世紀初尤其是伴隨著“絲綢之路”其名遠播,西域想象史開始具有了冒險、考古、文明薈萃之地等浪漫和學科史兼具的意義。在所有這些過程中,被重重關心的是那些遺留的蹤跡,那沙漠之下掩埋的古城,是一段段逝去的歷史,而在此之前曾被舍棄的百姓及其日常,開始在一本本游記中以各種身份在世間流傳,于是乎,能歌善舞、熱情好客、不事勞動、沖動好斗……這一系列依然見之于今日文字的描述成為西域詞庫的主體。王蒙的日常化書寫將新疆民間定格,周濤希望借盛唐之邊塞氣象開“新邊塞”之風并與時之中國的“尋根”遙相呼應,劉亮程則顯然建構了一個超越地域文化想象的劉亮程式的新疆。還有很多。然而,始終將“西部”作為不可缺少的背景來書寫眾生萎靡之象的恐怕只有紅柯,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紅柯開啟了另一種關于西部的想象。他筆下的“西部”進一步將新疆在特殊意象的描摹中推到世界的極遠處,推到象征的高度,成為一種精神性的存在,是另一種生命的度量衡,是奇觀,也是理想。紅柯高舉著這面鏡子,可被照的“妖”卻未必想當“人”,在《太陽深處的火焰》,則是一群活死人從墳墓走出長袖善舞于世間。至此,紅柯筆下的“西部”如劉亮程般是屬于自己的“西部”,他關于《太陽》的吶喊,對《燕子》的迷戀,吟唱著的波斯蘇菲詩人們的調子,則勾勒出一幅現世人的精神苦行圖。有多少人愿如紅柯所想做“西去的騎手”,追尋火焰、追求鳳凰涅槃般的絢爛,赤裸的暴曬自己所有的溝溝坎坎?拉展折疊是需要勇氣的。紅柯的意義,或者說紅柯的“西部”,他的反復訴說,無疑是一次次的勇氣的呈現,希望以生命之力的美好來“喚起療救的注意”。我想,這就是紅柯之為紅柯的重點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