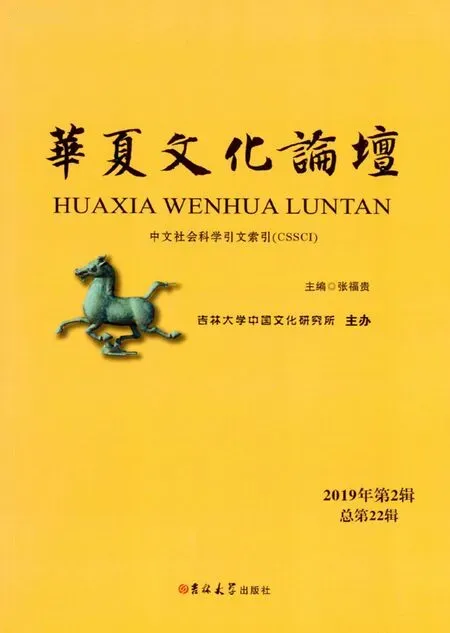“寫實”與中國藝術的現代轉型研究
朱善智
【內容提要】寫實不應只是風格和手法上的審視,寫實的本體首先和實物有關,“物”是最真實的寫實,因此物和文物的關聯衍生出了現代博物館藝術對于中國藝術研究在寫實與現代轉型上的貢獻。當然回歸寫實的傳統定義,寫實風格在繪畫、影視、攝影以及舞蹈、建筑等各大門類藝術中的展現或者回歸展現、轉型展現既是中國藝術史的重要課題,亦是藝術研究帶有哲學話語式拷問的領域。而在有關藝術寫實的探討中,寫實與寫意的辨證統一又是中國藝術現代轉型以及如何轉型永恒的話題。寫實與藝術哲學、寫實于藝術文本的編碼解碼功能中又存在著悖反抑或逆反的原理。
寫實或者寫實主義傳統、手法、風格等一直是文學藝術的“半邊天”,雖然無論是中國的詩歌藝術還是繪畫藝術,寫意才是主流,寫實仿佛是非主流狀態,但是在當下的現代文學藝術發展進程中,在文化自信書寫的大背景下,寫實或者叫現實主義創作在中國已經被強勢呼吁甚或已經大面積回歸,尤其是在影視藝術(影像藝術)大發展的基礎上,傳統藝術(包括繪畫、音樂、建筑等,甚至包含了傳統與現代融為一體的博物館藝術)無一不經歷了現代式的轉型,而在轉型的內容中,寫實亦成為了被探討的核心內容之一。
一、實物、文物與現代博物館藝術
文化人類學在中國的發展,首先推動了中國的文藝界對“實物研究”的重視,實物研究已然成為了史學界、藝術學界一個最重要的方法和視角之一。實物本身無疑是最“寫實”的形態,無論是藝術領域還是其他領域。著名寫實主義電影理論家、法國新浪潮之父安德烈·巴贊,提出了形象的“活動木乃伊”理論,認為木乃伊是有關一個人死后最寫實的“實物”,電影的本質應該像木乃伊一樣去寫實,現實是什么樣,就拍什么,因此他把電影稱之為“活動的木乃伊”。中國藝術的寫實問題與藝術史或藝術創作中的實物研究雖然看上去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方向和議題,但筆者認為實物研究至少可以為中國藝術史或者創作研究提供重要的“微觀”參照,在這種參照中,中國藝術的轉型問題和寫實問題可能已經有所涉及。
與實物相似的一個更高級的名詞是“文物”。實物研究是一種范式和方法,強調實物的樣本量,本文所講的文物主要是藝術文物(當然文物本身也往往具有藝術性),而藝術文物因其罕見性往往帶有很強的藝術敘事功能。所謂藝術敘事功能,指的是某一件藝術文物作為一個寫實的物件,單獨拿出來都能夠解讀出豐富的藝術信息,不需要作過多的群體參照。舉例來講,在電影藝術史的研究過程中,電影票、電影海報等的研究就是實物研究,而電影說明書、電影海報較之電影票則更快被界定為了文物,因為電影說明書有的多達好幾頁,電影海報畫幅較大,藝術設計和審美功能凸顯,更多的便具有了文物敘事研究的價值。
而將實物和文物融合在了一起的重要文化藝術載體是各種門類的現代博物館。現代博物館從體制的角度又分成了個人博物館和國家的博物館。國家類博物館更多地提供了一種“結構性的東西”,即大文物、大實物、大歷史和大文化、大背景,而私人博物館則更加凸顯藝術的現代性或者傳統史學的最大個體寫實性。許燎原現代設計藝術博物館和曹貴民的電影博物館肯定是完全不同的兩種風格,但卻提供了很多共同的點:實物與藝術寫實的脈絡、藝術傳統與現代的“無意識式”的過渡。許燎原現代設計藝術博物館吸引人的重要視角是感性與理性共現,裝置寫實與審美無限以點帶面;曹貴民的電影博物館則致力于難能可貴地將傳統電影實物規模集群化、擴大化,又不忘記加以分類,實現了分類學視野下的藝術以及藝術品的展覽與研究。
物與符號是很多人解讀鮑德里亞《物體系》的關鍵詞,從字面意義上看,物與符號恰似任何事物包括藝術的兩端,是寫實向非寫實的延展。于是,一個個現代的藝術博物館,光是在成都,名字里帶有“藝術博物館”的比較有名的博物館就超過了十家,除了許燎原現代設計藝術博物館以外,還有成都川劇藝術博物館、成都烏木藝術博物館、鹿野苑私立石刻藝術博物館、泥邦陶瓷藝術博物館、中國皮影藝術博物館、易園園林藝術博物館、成都華氏陶瓷藝術博物館等,成都大邑縣安仁古鎮更是被稱之為中國博物館小鎮,成都儼然已經成為了現代藝術實物展覽之都,在實物的背后,各種符號所折射出的中國藝術或大格局或小視野下的轉型問題頗多,非常值得研究。
藝術就是去掉物的實用功能,即無法使用。實物和文物都無法使用,增強了其藝術性指數,如果具備了更多的符號象征意義,則更容易上升為獨特文化藝術的結合體,就像近兩年比較火熱的“書信熱”一樣,從電視欄目《見字如面》、《信中國》到現實中的書信收藏和買賣,書信儼然成為了最具寫實樣態的現代文化藝術文物和實物案例,沒有書畫的高大上,更具家國情懷,而家國情懷又是我們國家正大力弘揚的文化主題,于是到了電影《流浪地球》里面,家國情懷是其燃爆國內外的重要原因也就不足為奇了。
實物是最寫實的“物”,物是最大的“寫實”,藝術文物是文化人類學意義上最真實的“寫實”研究,各種博物館尤其是現代藝術類博物館為這種寫實研究以及進一步研究中國藝術的現代轉型問題提供了豐厚的空間和土壤。需要注意的是隨著數字技術以及虛擬技術的發展,博物館藝術中的“數字成分”越來越多,“數字化的過程中要處理好‘虛擬影像’和‘真實展品’之間的關系,需要對許多不確定的效果進行預判”。
二、中國繪畫藝術的寫實與現代式轉型
現實中,無論是藝術史學界還是藝術理論界,我們在探討藝術史或者藝術這個概念的時候,繪畫(美術)藝術通常會被排在最前列,各種藝術通史包括教科書總是將畫家列為藝術形式重點探討的對象,研究繪畫藝術的學者仿佛也更多。究其原因,可能與繪畫藝術的古老性、保存完整性、可研究性等有關,更重要的是可能與繪畫藝術的流派眾多、影響廣泛有關,但從印象派到立體主義,從波普藝術后現代繪畫藝術,從抽象派到大地藝術派,這些近百年影響最大的近現代繪畫藝術思潮、流派基本上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幾乎與“寫實”無關。而且當下似乎是越抽象的繪畫作品越貴,就像《吶喊》之類的作品不斷地被拍賣出天價一樣。當下也似乎是越抽象的繪畫作品,越能解讀出更多的內容、故事、細節,從而具有更多的“哲學話語”、研究視野、“取義模式”和“跨藝術性闡釋”優先權。
眾所周知中國古典繪畫講究“氣韻生動”、“意在傳神”、“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也談不上“寫實”的特點,因此寫實更多的似乎是中外現代繪畫藝術轉型的一個特點或者重要的“點線面”,只不過西方經歷的是從寫實主流到抽象,而中國是從寫意主流到寫實的兩極轉型。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是好多有名的現代漢語詞匯或者成語是從藝術評價術語中被廣為引用的,就像“凌波微步”一詞原本是用來評價《洛神賦圖》的,后來在金庸的小說中成為了一種武功的名稱。“凌波微步”一詞基本上形象地代表了中國繪畫寫意基礎上的局部寫實,也就是說中國古典傳統繪畫就像凌波微步武功一樣,直到近代骨子里流淌的都是意象,只是形式上充滿了生活中的形似(局部寫實)。
這種情況一直到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出現了極大的改變,中國當代繪畫領域的幾個領軍式人物中,以羅中立和陳丹青為代表,從《父親》到《西藏組畫》,出名的原因都和注重寫實有關,而且是一種“照相意義上的放大寫實”,一種“皺紋式寫實”。照相寫實主義,又叫超級寫實主義,哲學依據同樣來自鮑德里亞的名言“模擬的東西永遠不在現實中存在”。油畫藝術一時間極大地改變了中國傳統繪畫藝術,寫實則從深層次證明了繪畫藝術的魅力。同時期的王廣義則更多的使用符號傳達現實問題和文化批判意義,他的大批判系列之一將可口可樂和工農兵放在一起,儼然是“藝術現實”的另一種境界,是一種反諷修辭學意義上的“對比寫實”。無獨有偶,1984年的美國《時代》雜志封面上是“一個中國人手里拿著可口可樂微笑的畫面”,則體現了現實意義上的“無反諷”功能,這幅畫或者照片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真實寫照,其藝術性已經完全包含在現實性中被“融化掉”了,但修辭格的體現依然明顯,仍是藝術寫實與符號化的藝術符號化關聯式創作。再往前追溯,西方繪畫寫實主義對中國繪畫的影響實則始于20世紀初,并兼及雕塑領域。在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使用了復印技術的冷軍,是中國繪畫藝術超級寫實與現代轉型進程中的另一個重要人物,他的代表作有《文物——新產品設計》(1993)、《蒙娜麗莎——關于微笑的設計》(2004)等,實際上超級寫實主義本身就是后現代主義藝術的一種。無獨有偶,同樣是20世紀90年代,以方力鈞、岳敏君、張曉剛為代表的“玩世現實主義”踏著反叛現代主義藝術的注腳,也乘上了寫實與寫意混搭的油輪,《打哈欠的人》、《處決》、《大家庭》系列在國內外均引起巨大反響。
此外,在油畫寫實方面,高小華也是一個代表,他的代表作《趕火車》充滿了寫實的高度感染力,“《趕火車》表現了‘四人幫’劫難后,人們心有余悸,在改革開放初期那種難以捉摸的復雜心態:幾分惆悵、幾分彷徨、幾分期許、幾分生機盎然,雖猶經滄桑,歷盡苦難,但仍信念堅定,人們朝著各自的目標要去趕時代的列車。這些人物心態描繪是有高難度的,沒有厚實的寫實能力和堅毅的意志是難以完成的。”
“中國油畫的發展并非是單向度的,多元文化環境促使畫家在寫實之外探尋更多樣的表現形式……陳均德、閆平、王克舉等人的‘意象性油畫’則將中國繪畫的寫意性融入油畫……劉迅、葛鵬仁、周長江等在抽象油畫方面的持續探索,形成了作品獨特的視覺感受和心理體驗。所有這些都與傳統的寫實拉開了明顯的距離,豐富著中國油畫的維度。”中國油畫似乎成為了中國現當代繪畫藝術的先鋒,在寫實的此岸向寫實以外的彼岸不停地嘗試擺渡、架橋,勾勒寫實內外的天際彩虹。
以《三把椅子》為代表的觀念藝術極大地影響了現代藝術的創作,尤其是繪畫藝術的創作。實際上這是一種寫實與非寫實(觀念寫實)的有機結合,既帶有裝置藝術的風格與影響在里面,也是流行藝術的一種業態表現,同時又是傳統繪畫藝術在技術和理念層面實物化、立體化、抽象化相結合的結果。旅美和旅法的華裔著名畫家趙無極和丁紹光之所以能夠創造出獨特的風格,當然和他們在西方受到的現代主義藝術思潮的影響有關,同時也和他們站在西方看中國的視角有關。《西雙版納》和《紅》表面上看是兩個風格的對立與極端,仔細研究就會發現它們有著天然的異曲同工之妙,都有著中國繪畫寫意傳統和現代寫實的有機串聯,是中國藝術走向世界的繪畫領域凸顯。
現代繪畫藝術的寫實特點與西方的焦點透視法也密不可分。近代以來的中國年畫也是借鑒了西方繪畫技法,將寫意與寫實的結合并演繹出新的文化藝術標出性能的產物。“年畫用簡潔的手法表現智慧和情趣,雖然其中也有偏重寫實的作品,但在造型上普遍偏重裝飾化,注重大膽夸張、變形等表現手法,即寫意、寫心,隨心所欲,任意變化。以寥寥線條、夸張動態來高度概括形體,意到為止。”
三、影視藝術的傳統寫實與現代寫意
“近年來,現實題材電影出現了兩種創作誤區,一種曲高和寡、追求自我表達,一種墨守成規、偏宣教說理,導致作品經常處于叫好不叫座的尷尬境地,難以在電影市場中獲得相應的價值認同。而2018年暑期檔上映的《我不是藥神》為現實題材市場化找到了一種正確的打開方式。創作者在遵循真實性的創作原則、堅持正向價值觀表達的前提下,探索類型化的創作方法,以張弛有度的敘事節奏、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生動立體的人物形象,為影片營造了更深層的表意與解讀空間。”當下中國電影界有一個關鍵詞叫“良心電影”,筆者多次撰文呼吁“良心電影應該寫入中國電影的辭典”,但凡近年來的良心電影幾乎全是寫實風格的作品,除了《我不是藥神》外,還有諸如《心迷宮》、《山河故人》、《老炮兒》、《一個勺子》、《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師父》、《烈日灼心》、《狼圖騰》、《可可西里》、《一九四二》、《萬箭穿心》、《告訴他們,我乘白鶴去了》、《天注定》、《白日焰火》、《百鳥朝鳳》、《驢得水》、《我不是潘金蓮》、《八月》、《戰狼2》、《二十二》、《無問西東》、《芳華》、《紅海行動》、《七十七天》、《無名之輩》等等。《二十二》、《七十七天》等不僅是現實寫實題材,已經幾近真實的記錄了。
美洲的魔幻現實主義從文學到電影、電視劇,從《百年孤獨》到《毒梟》均實現了文藝上的“出類拔萃式的成功”。一向以寫實和長鏡頭大師而著稱的臺灣導演侯孝賢則根據魔幻現實主義的成功提出了創作上的“地心引力理論”。“何以魔幻寫實的拉美文學如此迷人,絲毫沒有奇幻文學的令人不耐?是魔幻寫實地貼緊了現實。現實,就是物理作用,就是會讓人落回地面的地心引力……魔幻寫實描寫的是現實,以敘事技巧來顯得這樣的現實荒誕不經,或者是,在文明富庶的第一世界人們眼中,自然而然就覺得第三世界的生活方式是非常荒謬的。相較之下,奇幻文學架構在天馬行空的平行世界,不受現實的約束,沒有地心引力不用落回地面,然而沒有了通則的制約,會讓觀者有種‘都由你來說就好了’的不耐情緒。”這種總結很到位,其實說白了魔幻現實主義好多時候就是真實的寫照,就是完全的寫實,根本不是我們一般意義上所理解的“魔幻”與“現實主義”的脫節式合體。《人民的名義》之類的電視劇的成功是寫實完整性意義上的成功,離真正的“寫實主義”創作當然還有差距。
很多人喜歡并認同張藝謀的電影《秋菊打官司》和《一個都不能少》并將其視為中國現當代寫實主義電影的高峰,而陳凱歌的《霸王別姬》則具有了寫意的精神,“從影片的具體進程中流瀉出來的人性、人情、人本的真實,是最具有藝術震撼力的藝術大真實,它不僅使得影片中出現的不只一處的有關日常生活的局部細節的‘誤譯’變得情有可原,而且更進一步地凸現了影片鮮明的創作品格——這在某種程度上即造成了‘為了大真實,人為小細節’的獨特的創作品格,使小的細節同影片的內在主題之間在《霸王別姬》特有的語境里獲得了完美的寫意性融合。”同為經典,但從中國電影創作的當下實際需要來看,我們更需要《秋菊打官司》之類的影片,《霸王別姬》雖好,畢竟在中國電影史的百年記憶中仍未納入主流,依然處在“禁片”的行列。
傳統寫實與現代寫意的結合需要警惕的是過度的寫意形式對寫實性的過度顛覆,如果說畢贛的《路邊野餐》尚且都能控制寫意與寫實的關系,那么其《地球最后的夜晚》則明顯失控了,觀眾“看不懂”一詞的簡單式話語尷尬,實則可能是意識流作者本身都無法把控自己的創作意識的一種“流式尷尬”。萬瑪才旦導演的于威尼斯電影節獲得地平線單元最佳劇本獎的《撞死了一只羊》也存在著類似的問題。和畢贛一樣同為80后導演而年齡較長一些的李睿君做的要更加得心應手一些,無論是《告訴他們,我乘白鶴去了》還是《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寫實的內容與寫意的形式在全片貫徹始終,首尾呼應,敘事為主,寫意為輔,既有新現實主義電影的風格,同時又具有中國式東方美學的意境與美感。
當下的寫實主義創作傾向,業已波及到了可以視為文藝的電視節目領域,主旋律也開始從電影銀幕釋放到更廣的電視熒屏。《趕考路上》、《閃亮的名字》是為代表,“在電視節目領域,《閃亮的名字》《趕考路上》等綜藝節目與主旋律基調的融合也正在帶來一場全新的語態變革。”從電視劇藝術的角度,2019年出品的焦點作品《都挺好》和《新白娘子傳奇》作為寫實主義和非寫實主義的兩極,都指向了一個探討話題,即《都挺好》是否存在過于寫實而與藝術創作存在矛盾的議題,《新白娘子傳奇》雖然玄幻但整體觀感卻沒有以前同類作品因大量使用特技而帶來的虛假感,美的意境和畫面,具有了更多實實在在的美感。電視劇藝術的本身特點使得寫實與現代轉型問題可能更加復雜、具體,但好在我們擁有大量的現實故事更加適合熒屏敘事,中國是電視劇創作世界第一大國的身份讓這種轉型有了更多的“現實可行性”。《破冰行動》從劇本歷時兩年多的打磨到最后的真實性呈現,便譜寫了藝術來源于現實并升華“可行”的故事。
四、其他藝術領域的寫實與現代轉型問題
一般人都會評價楊麗萍的舞蹈《雀之靈》是真善美(靈與肉)的化身,真與美、靈與肉的統一正是中國藝術追求的終極目標之一,也是本體寫真與現代生命旨趣象征的完美契合。楊麗萍的《云南映象》則整體上回歸了意境美的范疇,“映像”一詞本是胡塞爾現象學中翻譯過來的術語,胡塞爾致力于研究事實本身,卻仿佛始終未曾抓住并構造本真現象。
譚盾的音樂一直存在爭議,但其經常灌入作品中的天人合一的美學思維,成功地將有機音樂的種子種到了中國音樂文化的現實叛逆中,書寫了與西方音樂藝術相融而又相異的中國現代藝術轉型之路。有人甚至將他的音樂創作視為行為藝術,殊不知,行為藝術也是一種“寫實”藝術,一種真實的美學表演,只不過可能并不美。行為藝術和身體又緊密相關,身體是當代藝術最為豐富的表達主題之一,“藝術家對自己身體行為和創作過程的自覺意識,為各種現場藝術(live art)形式鋪平了道路——即興起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行為藝術,如偶發藝術(Happenings)、激浪派藝術(Fluxus)、行為藝術(Actions)、人體藝術(Body Art)。”
王澍和貝聿銘作為華人建筑大師成就斐然,但都沒有忘記中國藝術“因地制宜”的現實內核,并能夠開創性地結合不同的環境實現藝術的最大質感和直感。“王澍的建筑自始至終沒有一個可以視為‘中國元素’的標志性符號,但是處處流溢著中國感。它的整個設計是物感呈現而非符號性的,這使它在凸顯中國性的同時又是高度現代性乃至后現代的,顯示出古代建筑所無法具有的簡潔、大氣和骨髓深處的現代氣質,呈現出鮮明的現代性質感。”貝聿銘的蘇州博物館設計,表面上甚是簡單,無非就是園林、山水或相依或交映呈現,光線與白色鑲嵌其間,但其整體性以及整體體現出來的藝術美感,在現代性與寫實方面可謂與北京的雁棲湖國際會議中心的整體設計異曲同工。
近年來獲獎的攝影作品基本遵循了寫實的手法,在記錄寫實的前提下可謂充分實現了“現代式轉型”,如《紫禁城的秋天》(洪磊)、《on the wall》系列(翁奮)、《宿舍》(王慶松)以及李暐的創意“飛天”系列等。《紫禁城的秋天》充分運用色調和環境的搭配,帶有油畫的特點;《on the wall》系列表現的是當下孩子對城市化的迷茫;《宿舍》使用了現場擺拍手法,追求真實上的立體效果;飛天系列充分運用了電影上的吊威亞特技,實現了武俠片式的無限創意攝影,表面上仍充分顯露出寫實的功能。攝影本來就是紀錄的工具,探討攝影藝術作品的寫實性似乎是一個學理性悖論,但不可置否的是任何事物、稱謂一旦打上了藝術的烙印,必然會接受藝術創造美學的規則,任何天馬行空都可能成為極具現實性的現實可能,盡管這種現實、寫實已經大打折扣。
朱光潛在《談美》中說:“藝術須與實際人生有距離,所以藝術與極端的寫實主義不相容。”肯·弗里德曼(ken Friedman)在《激浪派譜曲》(Fluxus score
,1971)中說:“從這句話到你的眼睛之間的距離是我的雕塑。”寫實與現代藝術既有距離,也有一般人很難發現的個中美麗與風景。五、寫實與現代轉型的雙重原理解讀
世界現代藝術的進程中藝術哲學的話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基本成為了藝術理論的核心,理論指導實踐創作的反推力使得藝術創作與轉型很多時候面臨困境,一方面藝術門類眾多,不可統一定式發展,敘事藝術更多地存在著藝術原理建構的內容;另一方面中國藝術整體現實主義的訴求似乎和藝術哲學又存在著悖反的情況。于是,我們看到,一邊是繼續呼吁中國藝術的哲學背景、哲學深度,如正在構建的中國電影學派就呼吁中國電影的哲學沉思,一邊是更加通俗而富于真實改編或者摹寫的現實主義力作的不斷出現,當然也包括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的回憶寫實與文化懷舊。寫實與中國藝術的現代轉型從此層面來看是一個艱巨的任務,寫意的中國傳統與西方文化的沖擊、西方對中國藝術的認知片面性使得我們需要進一步思考中國藝術“詩化”的現代特征和現代轉型,同時我們又必須意識到新時期寫實應該成為中國藝術的第一標簽,讓近現代以來的中國文化、歷史、人文風情、中國夢等成為中國藝術既具隱性又具顯性的有機統一體。
任何文本包括藝術文本都是一個編碼解碼的過程,按照這一原理,越寫實的藝術文本,觀眾的解碼性就越弱,越抽象的藝術作品,解碼性就越強,但有時也存在著逆反,即抽象的作品許多時候觀眾不愿意去解碼,使得解碼性直線下降了,甚至為零,相反寫實的作品更能引起共鳴,在共鳴的基礎上反而引發了藝術探討的風暴,使得解碼性出現了拐角式、分叉式提升。無論是繪畫、音樂還是影視作品在當下的解碼似乎都存在著逆反的情況,音樂可能會被反復聽以至無限“演繹與演義”,催生新的含義,如楊超越和她的《卡路里》,從破音變成了優美的減肥“神曲”,電視界出現了追劇行為,追劇的結果是一個人、一個符號的指代性含義超過了劇作本身,蘇大強這個符號有時比《等著我》強大很多,也就是說解碼的方向和注意力經濟使得解碼會發生甚至天翻地覆式的變化,這已經不僅是一種簡單的流行文化對藝術的影響范疇了,而更多的是現實的需求使得觀眾、受眾更加注重藝術作品與自己的關聯,藝術現實真正地成為了生活現實、審美現實。
結語
中國藝術創作對“寫實“的回歸與呼吁,既是時代的需求,也是現代轉型的需要,因為無論是傳統藝術還是新興藝術門類,在當下過于強調解讀消費語境的情形下,“寫實”本身是最好的現代性詮釋和最好的轉型手法之一。
中國藝術的寫實,在繪畫、電影、電視、舞蹈、攝影、音樂、建筑等方面表現的不盡相同,但原理相似,都是基于中國文化和中國人對藝術的熱情從未消減的歷史長河中,“靈與肉”的完美上演,寫意傳承及其基礎上的有的放矢的“嬗變”!在這種嬗變中可能存在著原理上的悖反與矛盾,但無疑藝術現實是最大的審美特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