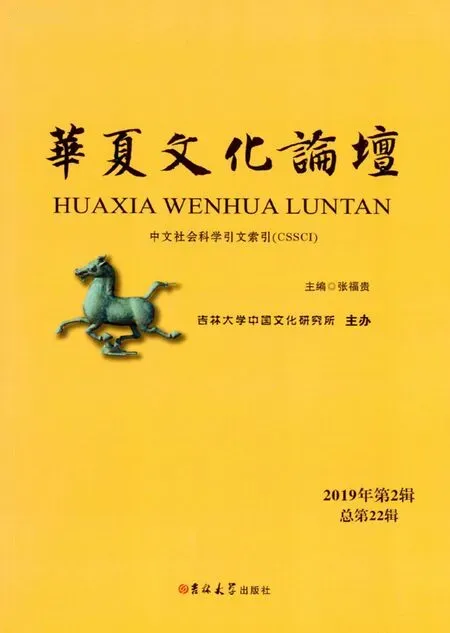馬克思恩格斯城鄉觀的小說文化表達
張志昌 張旖華
【內容提要】城市化導致了城鄉的分離、對立及融合,城市內部也形成類似城鄉之間的文化鴻溝和斷代,因而城市相對于鄉村具有較高的文化勢能。《復活》中貴族大地主的憐憫無助于土地問題的解決;《白鹿原》敘事表明只有農民成為土地的主人,革命成功社會進步才有可能;糾結于守土離鄉矛盾心理的《秦腔》《高興》體現的城鄉觀根子上是民族自信問題,這些作品都是國家現代化進程中城鄉關系的小說文化記錄。文學的創造性書寫表達作為歷史合力之一亦會對社會歷史的發展有著推動作用。有活力和精神的城市與宜居美麗的新農村才是城鄉融合互動物我合一的理想藍圖。
檢閱馬克思恩格斯城鄉觀研究的既有成果,大體上分為五類。第一類是關于馬克思恩克斯城鄉關系理論的內涵研究,包括背景、制度、沿革等;第二類主要涉及這一理論的當代解讀,包括城鄉融合統籌、城市病及其治理、“空心村”成因及對策等;第三類是關于基于方法論視角的研究,既涉及馬恩研究問題的不同介入角度,也涉及以田野調查和工農業經濟發展的數據研究等;第四類是對列寧及以后的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人對馬恩城鄉關系理論的發展及實踐研究。第五類即本文尤為關注的是從城鄉文化變遷的角度,或以鄉土小說或以文化地理為個例進行的一種精細分析。學者們基于不同視角對這一問題的研究都是把城鄉觀作為歷史唯物主義創立過程中的一個重要范疇來對待,兼顧了系統性、邏輯性和前瞻性,態度科學嚴謹,成果豐富細致。本文擬從文化學的角度,從馬恩等經典作家的調研和論述為依據,重點以托爾斯泰、陳忠實、賈平凹等作家小說中的城鄉觀敘述為樣本,借助小說敘事魅力,試圖更深入地挖掘闡釋馬恩城鄉觀。
一、基于文化學的馬克思恩格斯城鄉觀的內涵
(一)城市化導致了城鄉的分離、對立及融合
生產力發展帶來的社會分工是城鄉關系分離的原因。馬克思說:“一切發達的、以商品交換為媒介的分工的基礎,都是城鄉的分離。”這種圍繞商品交換的社會分工造成城鄉對立運動,構成了經濟史的全部內容。在資本主義環境下,國家制度的不合理和優質資源被資本家壟斷就會讓扮演不同經濟職能的城鄉分離逐步固定化。“德國為了建立城鄉分離這第一次大分工,整整用了三個世紀。城鄉關系一改變,整個社會也跟著改變。”英國的工業革命使得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創造了比以往都要多的生產力,隨之城市一派繁榮之下是農村土地擱置、人口向城市的聚集和鄉村空心化現象。
城鄉對立其實是一種歷史性狀態,是社會發展的產物,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相應地,城鄉融合也是一個與城鄉對立相反的歷史范疇。“城市和鄉村的對立的消滅不僅是可能的,它已經成為工業生產本身的直接必需,同樣它也已經成為農業生產和公共衛生事業的必需,只有通過城鄉融合,現在的空氣、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蘊含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資本論》、《共產黨宣言》、《政治經濟學批判》、《論住宅問題》等一系列著作中的城鄉融合思想表明,“通過消除舊的社會分工,通過產業教育、變種工種、所有人享受大家創造出來的福利,通過城鄉的融合,使全體社會成員的才能得到全面的發展”,從而,城鄉融合表現為:社會沒有了分工和私有制,生產力高度發達,人人都可以得到全面且自由的發展,勞動成果由全體社會成員所享,滿足每個人按需分配的要求。
(二)城市之間及內部也形成類似城鄉之間的文化鴻溝和斷代
不同城鄉之間及同一城市內部同樣可以見到文化的斷代和鴻溝。城市功能定位及不同區域功能的差異、不同層次人群聚居和文化的差異、治理階層注意力和投資建設的差異、歷史和文化傳統的差異等共同構成城市間的文化鴻溝和斷代。
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的調查表明,占人口很大比例的工人階級過辛勤勞動創造了巨大的社會財富,但他們什么也沒有。工人階級最集中的許多大城市中,“一小撮強者即資本家握有一切,而大批弱者即窮人卻只能勉強活命,一方面是不近人情的冷淡和鐵石心腸的利己主義,另一方面是無法形容的貧窮。”物質和精神上的雙重差距達到了難以想象的水平,當時的英國大城市、較小的城市和農業地區同樣如此。
從人的全面自由發展角度看恩格斯描述的資本主義社會驚人惡果,“城市和鄉村的分離,立即使農村人口陷于數千年的愚昧狀況,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專門手藝的奴役。它破壞了農村居民的精神發展的基礎和城市居民的體力發展的基礎。”鴻溝在倫敦等一切大城市如此,在上海直到解放前亦如此。在舊上海,穿考究的衣著、喝講究的咖啡、操熟練英語的社會階層出入南京西路,居住別墅洋房,奢華閑適;里弄、平房、棚戶區中則是一派尋常質樸的市井生活,居民多衣衫襤褸饑寒交迫,傷痛悲苦在底層文化心態浸淫延續,楊華生的《七十二家房客》集中敘述了1947年的上海市井階層的住房和心理窘態。脫胎于市民階層的大資產階級追求時髦雅致、傲慢排外和未脫徹底的市儈氣息與市民的務實自私人情淡漠附庸風雅形成天壤對比。這種城城之間和城市內部的文化差別今天乃至今后在短期內難以消除。
(三)城市相對于鄉村具有較高的文化勢能
城市與鄉村的分野源于生產力的“有所發展但又發展不足”。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得非農人口非農產業涌現,同時,生產力的發展又沒有得到足夠充分的發展,“鄉村農業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業人口的集中,僅僅適應于工農業發展水平還不夠高的階段”,馬克思的觀點依然表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這一矛盾體所構成的生產方式的演進是推動文明更替前進的動力。
城市成為先進生產力的引領和先導。漁獵社會的主要存在形態是氏族部落;農業社會則是鄉村;工業社會中城市成為主要存在形態。聚集輻射效應使得城市集中了大量勞動力和生產要素,成為工業和貿易中心,也成為信息和知識生產中心。歐洲中世紀鄉村城市化和資本主義取代封建生產方式的進程不謀而合,這一進程即是城市對鄉村的擠壓和農民利益的剝奪,痛苦卻必須,代表著歷史前進的方向。“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產工具、資本、享樂和需求的集中”,資源配置和市場上的優勢在供需關系的調整和生產力的有效調動下,資本周轉更加迅速,建筑用地得到補償,城市崛起、工業化、城鄉分離、人口集中、商業財富迅速集聚等風起云涌,“村鎮變成了小城市,小城市變成了大城市”,漫長野蠻的鄉村城市化文明過程就這樣歷史性地展開了。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標志著城市相對鄉村而言根本上的統治地位。“資本主義使農村屈服于城市的統治。它創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農村人口大大增加起來,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脫離了鄉村生活的愚昧狀態。”馬恩在《共產黨宣言》中也正是從世界歷史的角度分析和預判了更廣闊意義上世界市場形成的依據。
世界各地崛起的城市如布滿天空的星辰一樣成為商業經濟和政治文化中心,在此基礎上形成的風格各異的城市文化遂成為人類文明的集中體現。五大古老文明均是以人群的聚居相通形成一定的中心城市、思想的多元融合形成不同流派、制度的明晰形成相應的體系、器物的豐富絢爛呈現不同的外部表象等為差別和特征的。城鄉間在上述元素上的差別構成不同的勢能。城市高于鄉村的文化勢能不再是同一文明時代社會分工造成的差別,而是以資本為中心的工業文明和以土地為中心的農業文明之間的差別。
城市相對農村的較高文化勢能還表現為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和就業容量,更優質的教育醫療文化水準和更豐富的精神生活,加之所有制形式下利益差別、資本資金的集聚調動能力、城鄉人群社會分工的不同缺陷,城鄉二元對立呼之欲出了。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城鄉分離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大分工,每一個體都將屈從于分工,從而工業掘進的同時伴隨著農業的衰退和農村文化貧瘠和農民精神的困頓。典型如作家哈代(Thomas Hardy)的敘事。他筆下1872-1896年代的英國鄉村風光田園質樸,宗法世界下的威塞克斯滿懷希望,創造快樂,可人們封閉保守,愚昧宿命,鐵路、火車等工業文明快速蔓延,環境被破壞,機器取代人工,土地流失,人們四處流落打工。鄉村文化熏陶的理想人物苔絲姑娘避免不了自身悲劇結局,成為處于高低位文化勢能差的犧牲品,因為存在“一股遙遠而不能阻擋的力量,正是這股力量似乎決定了農村和農民的命運。”
二、土地問題:城鄉觀的小說文化學例證
敘事小說是要鋪陳故事的,而故事必須借助明確的時間空間來組織情節,因而提取時空情節人物心靈等要素,充分考慮到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從新史學和“知識考古”的角度還原真實記憶與社會痕跡,進一步研究以土地問題為核心的城鄉關系變遷仍是有潛力可挖掘的。
(一)《復活》:貴族大地主的憐憫無助于土地問題的解決
托爾斯泰的《復活》創作前后耗時十年(1889-1899),歷經三稿。當時俄羅斯處于1905年大革命前夜,山雨欲來風滿樓。為了創作《復活》,托爾斯泰參觀多處監獄,旁聽審判,采訪律師囚犯等,查閱檔案資料,深入農村調查農民生活,持續十年的創作激情鑄就經典之作。列寧高度評價了其作品對現代一切國家、教會、社會和經濟制度的激烈批判,“作為俄國千百萬農民在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快要到來的時候的思想和情緒的表現者,托爾斯泰是偉大的。”
忠實代言封建宗法制農民利益,托爾斯泰敏銳捕捉到了社會劇變前夕的復雜矛盾,深感于類似聶赫留朵夫的內心痛苦和瑪絲洛娃的悲慘遭遇,按捺不住自己的沖動和思考,愿意提出矛盾的解決方法和人物出路。他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探索土地改革和農民解放,以農民運動為基礎的創作,又反過來促進了農民運動的發展。聶赫留朵夫曾經成長于受益于沙皇專制制度,精神上一度昏昏欲睡,生活窮奢極欲,無所作為。作為貴族其物質生活居于物質文明的頂端,窮奢極欲的消費理念及對物質華麗貴重的要求,遠遠超出了下層民眾滿足一般需要的程度。貴族們對社會進步和歷史發展的推動換句話說對社會精神的貢獻并不必然匹配。豈不知,一個個高貴華麗的皮囊下行走著的是一具具偽善頹廢的靈魂。痛苦的聶赫留朵夫在承襲了大量產業后一度是高興的。他當年是斯賓塞的忠實讀者,信服“正義不容許土地私有”,身為大地主,他不愿意違背信念而占有土地。雖然心理上不時受到斯賓塞、喬治兩位經濟學家土地私有不合理這個“光輝論證”的叩擊,但是他畢竟奢侈生活過慣了,除了土地他沒有其他生活資料,怎能說放棄就放棄?把土地無償分給農民只是自己年輕時圖慕虛榮想一鳴驚人的欲望,實踐中無法當真的。作家是矛盾的,也是有局限性的。托爾斯泰以救國救民為己任,在描寫了大量俄國社會復雜矛盾的基礎上,極端苦悶,真誠地為社會找到的救世良方是皈依宗教,尋求慰藉。在批判決裂的同時,托爾斯泰筆下的主人公聶赫留朵夫打開了《福音書》,“據說什么問題都可以在那里找到答案。”
社會盡管存在諸多的不合理現象,現有秩序還能維持下去,為什么?要讓社會更穩定和諧地繼續維持下去還缺少什么?“社會和社會秩序所以能維持,并不是因為有那些受法律保護的罪犯在審判和懲罰別人,而是因為盡管存在這種腐敗現象,人們畢竟還是相憐相愛的。”人與人之間虛弱的關心愛憐在聶赫留朵夫身上可能是應驗的,因為他是精神上走向復活新生的一個代表,但是大量的貴族特權階層應為維護固化階級利益的根本需要,卻絕不會像他一樣背叛本階級。
大革命前夕的社會是混亂的,情急之中的作家真誠地為社會開出的良方只能是一個祝愿。十九世紀最偉大的作家給全世界人民貢獻了長篇小說的明珠,但提出的辦法卻是局限于自身世界觀的。依靠一兩個善心地主,解決不了農民和地主階級之間的尖銳矛盾。
皈依宗教,遵守戒律而非奮起反抗,推翻舊階級的統治,通過暴力革命建立起新無產階級專政的新政權,這就是托爾斯泰為社會找出的救世良方。聶赫留朵夫這類脫下舊貴族外套實現自我救贖走向精神復活的新新人類拯救社會的使命也大抵就是如此了。文學的表現形式是觀察和描摹基礎上的表達和體驗,本質是基于社會進步意義上的批判。《復活》等三部巨著之所以能成為俄國社會的一面鏡子,就是因為通過長篇小說這種特殊形式,誠實的托爾斯泰完成了對社會的觀察和批判。
(二)《白鹿原》:只有農民成為土地的主人,革命成功社會進步才有可能。
生活在城市和鄉村都是生存的不同方式。千百年來,城市以富庶發達成為文明的集中地,鄉村以樸素生態詮釋著絕大數生命的延續。富強民主自由是最終目的,一體化協同發展應該是共同美好的前景。陳忠實筆下《白鹿原》市井繁華的民樂園地區類似于張恨水、魯迅筆下的北京前門地區,都分別成為商業文化、會館文化登堂入室的代表,顯現出恣意活泛的親民文化內涵。與此同時,圍繞買地賣地奪地的風波在朱先生“為富思仁兼重義,謙讓一步寬十丈”的勸誡下卻成為白嘉軒、鹿子霖處理土地問題的最終認同。滋水河畔,終南山麓,“大地簡潔而素雅,天空開闊而深遠。”鄉村以一種特殊魅力詮釋著生活的另一種方式,成為記憶和希望的“如夢如幻的地點。”
陳忠實早年生活在農村,當了專業作家后進入城市,體驗了水泥森林下的城市生活,寫作《白鹿原》時卻矢志蝸居在鄉下西蔣村的老屋里,孤獨苦悶,愉快悠然地抒寫生命體驗。如何準確真實地反映小說中人物所處的時代脈搏和精神,藝術追求上達到當時時代的文學水準,對陳忠實而言,小說篇幅長短是其次,深度廣度卻是關鍵,無關城鄉居住地的差別,卻關乎長年累月的忍受寂寞和持之以恒的韌勁。
民族的發展和城鄉的進化同樣充滿苦難和艱辛,同樣存在一個對腐朽落后的劇痛剝離問題。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忽視這一點就不是一種客觀科學的歷史辯證的正確態度。黑娃和初期的鹿兆鵬尚不是用科學理論武裝起來的革命者。從小說敘述的情景來看,打土豪分田地,從而解決諸如像李寡婦那樣貧苦農民依托的戰略性策略還尚未在白鹿原大地上全面展開。解決貧苦農民的土地問題是階級斗爭在白鹿原白熱化的導火索,財東鄉紳占據大量土地,革命要革到自己頭上時,國民黨的反撲就開始了。田福賢等貪官污吏未得到懲罰,農協計劃中的土地分配未及開始,“四一二”政變發生,“斬草除根”的行徑異常兇猛和殘酷地上演了。
1925年冬至1927年春,毛澤東先后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著作,指出農民問題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無產階級領導農民斗爭的極端重要性。1923年開始彭湃起草的《廣東農會章程》、《沒收土地案》等指導了蓬勃興起的全國農運,為中國共產黨領導土地革命和全國農運提供借鑒。1927年10月至1930年2月,毛澤東率領紅軍在井岡山解決了農民的土地問題。“紅旗飄飄五角星,共產黨來哩有田分。”“窮人最先得好處,人人都有土和田。”“土豪劣紳都打倒,山林土地回老家。”當時就傳唱的民謠反映了農民千百年期盼滿足之后的興奮。
小說人物黑娃缺乏的正是這些科學理論和正確實踐!農民出身的黑娃一生中沒有機會掌握一套科學思想武器。在三個月農講所學習中也沒有受到系統的革命理論培訓,沒有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思考自己受壓抑,社會不平等的根源和中國革命的現狀、問題和戰略,錯過了走上馬克思主義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正確道路的機會。鹿兆鵬對他的啟蒙也只是來去匆匆,只言片語,臨去延安前交給他一本毛澤東的著作,也缺乏進一步的講解啟發。黑娃在白鹿原上開展的“風攪雪”式的革命也只是對不合理現象的報復,不計后果且沒有科學理論指導,思想的空虛和迷茫始終存在。傳統儒家文化雖然把黑娃改造成了一個知書達理學為好人的謙謙君子,但并沒有給出解決社會問題的出路。和朱先生、白嘉軒一樣執迷于傳統文化的鄉村精英們包括黑娃一類的后學新秀在與現代化思潮的對決中日漸衰落。文化上的落寞和孤單無依靠是一個人或一個群體提不起精神的誘因,但問題的最終實質卻是對社會發展規律和趨勢的茫然無知。在人生最緊要的關頭,一種先進理論的支撐和武裝足以成為信念信仰動力,一個代表先進生產力和文化的階級足以成為其前行的引導力。
《白鹿原》塑造的白嘉軒、鹿子霖是代表中國農村社會的兩類典型農民形象,然而更是代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兩類典型人格。現實生活中,我們希望有時候要有白嘉軒的固本堅守,有時候要有鹿子霖的詼諧達觀;有時候反感于白嘉軒的不近人情和精于算計,有時候痛恨于鹿子霖的淪喪無底線。白嘉軒不大進城,鹿子霖時不時進城,文學形象非線性復雜性讓我們咂摸著家國、家園;咀嚼著黃牛、狐貍;體會著繁華和落寞。
毛澤東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就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而奮斗,而且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斗;一切這些的目的,在于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抓住農民問題,解決了土地與人民之間的隸屬問題,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革命才取得了全面成功。從土地這一角度看,《白鹿原》的文學書寫作為歷史真實寫照才鑄就經典,意味雋永。
(三)《秦腔》《高興》:守土還是離鄉——城鄉觀根子上是民族自信問題
城鄉觀不僅關乎城鄉差別,從根子上說還是一個民族自信的問題。發現問題、正視問題才能解決問題。“人類并不是生來就為了要像螞蟻那樣擠成一團,而是為了要遍布于他所耕種的土地。能夠更新人類的,往往是鄉村。”因此,把農村建成宜居生態的家園,把城市建成藍田白云的花園,讓身處不同城鄉的人們凝心聚力安居樂業,是執政黨的膽略和擔當,是國家長治久安的戰略性布局,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生動體現。
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國家在治理上的一個現實可行的辦法就是長期實行城鄉二元制的社會結構,把近八億到十億的農民穩定在廣袤的鄉村從事農業集體生產,加快消除城鄉差別,鞏固國民經濟的工業基礎是新中國建國后長期發展的寫照。在以后的年份中,當然有一些腦瓜靈活的農民進城務工,做生意,掙了錢,也有走上邪路的,更多的農人則扎根這片土地上。城里人就真正生活優越,精神富足嗎?大多數城里人生活在城市底層,依然過著貧困、卑微屈辱的日子或過著與池莉的《冷也好熱也好活著就好》、劉恒的《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中主人公一樣的泛喜劇式生活。
社會轉型是復雜而漫長的,建設新農村,加快城鎮化是一個大趨勢,重要的是改變農民心里根深蒂固與時代不相適應的傳統觀念。有些觀念無所謂先進或落后。人對自己的苦日子是淡然相處習以為常的。生下來是農民,不種地又能干什么?社會給他們又提供了什么平等的機會嗎?《高興》中黃八認定農村就應該和苦瓜一樣苦,這種天經地義的觀念并無所謂先進落后。實際上,社會不公正、苦難、貧窮是這個物質繁榮時代的一種現實,人們包括農民,思想的解放,理想的飛揚,人格自覺的空前提升,同樣應是這個時代的現實。
城市是率先實現代化的場域,是現代文明的傳播核心,是商品生產、制造、流通、消費的中心,匯集除了農業以外的所有行業。人口高度聚集,消費潛力巨大,工業布點集中,存在大量的崗位需求和巨大的生存與發展機遇空間。農民眼中的城市是財富的象征,誘惑力巨大。《高興》中的主人公劉高興在一批批榮歸故里的打工返鄉者的示范下,義無反顧的走進城市尋求屬于他們的一方天地。
城市里情況復雜多了,遠遠超過鄉村的一兩個村子那樣簡單的產業結構和人際關系。長期生活在城市福利城堡中的市民,天生在社會資源與競爭方面占據著優勢,心理上行為上難免流露出農民工的偏見和歧視,某些市民還形成身份上的優勢意識。劉高興憑借辛苦和善良撿垃圾賣錢生存,物質貧困,精神自得,滿足于既有現狀,愿意適應和奮斗。他面對城鄉差異和心理落差,是一個天然的樂觀派,堅持能改變的去改變,不能改變的去適應,不能適應的去寬容,不能寬容的就放棄,一心想成為西安人。時不時的社會不平等讓他的精神游離于城鄉之間,扎不下根又回不去鄉,“做起城里人了,我才發現,我的本性依舊是農民,如烏雞一樣,那是烏在了骨頭里的。”城市化進程中,行將過去的故土在渴望強大,活得儒雅的需要中在夢塋牽繞,無法釋懷。
在中國農村全方位改革和城市化進程中,賈平凹的《高興》和《秦腔》都是反映傳統文化和傳統生產方式崩潰過程的代表性作品。社會變化給農村帶來的生活方式的變遷和農民受到的心理沖擊是前所未有的,作家的責任是想清楚,說清楚。《秦腔》寫的是社會變遷沖擊下農村的生活狀態和農民的生存方式;《高興》寫的青年農民劉高興進城打工極力融入卻又不被城市接納的尷尬狀態,兩者有邏輯上的銜接關系。作家精神自由、責任充溢地觀察現實,描摹生活,探索出路,尋找現實條件下農村發展的出路和農民進城后的心靈安放、產業承接方式,痛苦難解。
習近平同志指出:“人要在城市落得住,關鍵是要根據城市志愿稟賦,培育發展各具特色的城市產業體系,強化城市間專業化分工協作,增強中小城市產業承接能力,特別是要著力提高服務業比重,增強城市創新能力。”城鄉發展一體化是國家現代化的重要標志,讓更多的“高興”無論守土還是離鄉,都真正高興起來,才正是中國共產黨的使命擔當和中華民族自信和魄力所在。
三、小說文化表達的啟示
(一)鄉村的欠發達制約城市主流或相對強勢文化的繁榮和傳播。
主流和非主流、強勢和弱勢是文化交流過程中的必然現象,能夠對其他文化單向流動并且發揮影響的就是強勢文化,相反就是弱勢文化。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逐漸消解與弱勢文化對強勢文化的努力滲透是城鄉文化交融的常態。十九世紀末愛爾蘭鄉村農業的傳統落后會使都柏林的主流文化興盛與發展受到限制,才使得喬伊斯(James Joyce)小說《阿拉比》中小主人公神往的阿拉比大集市交通不便,貨物稀少,質次價廉。《白鹿原》中主人公白嘉軒也只有在人財兩旺后,才坦然走進鹿家上房,和鹿泰恒大叔商量翻修祠堂、興建學堂這類“無量功德的大善事”。村經濟發展的不足自然制約人們對高質量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因為物質條件的滿足和延續是首要障礙。
“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沒有生產方式的轉型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也就沒有生活方式的轉型和精神文化的消費。確保農村居民逐年增收才是消滅文化高低勢能差的關鍵一招。
(二)在城鄉反差和融合中凝集文化書寫人性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所講的城鄉文化發展的這種斷裂,反過來又加劇了城鄉差別擴大的程度。因而,不獨《秦腔》中作家夏風和妻子白雪之間的都市文明與鄉村傳統秦腔之間的沖突,王海鴿小說《新結婚時代》中從沂蒙山區考到北京的何建國與北京本土女孩顧小西之間發生的鄉村與都市文化沖突,都是轉型時代的產物和吊詭。現代化給中國人帶來物質極大豐富,同時卻是人情趨淡和傳統沒落,“與物化時代水火不容卻又符合人本心的需要(如鄉土田園般美感的純美愛情),現代人失去了它靈魂自然無所依附!”
“作家是受苦與抨擊的先知,作家的職業決定了他與社會可能要發生摩擦,卻絕沒企圖和罪惡。”作家的前瞻性決定其它的任務不是頂禮膜拜,也不是歌頌宣傳,而是懷疑批判,但這種批判是建立在對世界對人生意義懷疑的立場上,而不是為批判而批判,為名利而批判。作家與社會的關系的適度緊張有助于出現好作品,有助于強化作品的深刻和厚度。賈平凹的看法是基于自己多年的創作實踐和社會體驗提出來的批判意識和社會責任感的體現,反映了他的創作道路和出發點。以農村雞零狗碎的人和事,以白描為主要手法完成的《秦腔》亦堪稱是這種矛盾心理的代表。
“巴黎本身即是巴黎市民集體的記憶,巴黎跟記憶一樣,連接著事物與場所。”這些“事物與場所”就是歷史和鄉愁,足以喚起當下人們的自豪和尊嚴。廣袤的中國鄉村曾經現在仍然是波瀾壯闊的歷史發生地,有什么理由不能激發人文化上的莊嚴感從而提升文化軟實力呢?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借助馬克思的理論,把巴爾扎克《人間喜劇》描寫的巴黎當成心理地理學;從盤古開天辟地以來的神話傳說及歷史故事遍布中國城鄉,完全能通過傳統、慶典、符號、記憶、鄉風民俗等建立輻射力廣泛的文化凝聚體。
(三)土地問題始終是城鄉觀和治理層關注的重點
作家是矛盾的,也是有局限性的。托爾斯泰面對大革命前俄國的社會矛盾,提出的土地問題方案并不為農民接受,主人公在《福音書》的尋找是徒勞無功的。要徹底解開把農民和地主間鎖在一起“結實的鎖鏈”就要把土地無償交付農民,不必付任何租金贖金,這是革命民主主義者提出的正確策略。沒有科學的理論指導,無法提出偉大的社會變革方案,自然這本身也不是作家分內職責。
白鹿原的革命還沒有接觸到群眾最關心的根本問題——土地,只是不斷地進行外圍的形式改革,有足夠的震撼,但沒有觸及根本利益,目標也零散,沒有提出或者嚴格貫徹一個科學系統的綱領。工農革命推進到一定程度就必然會涉及土地和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問題,這是廣大群眾的呼聲和焦點。土地越集中,矛盾越尖銳,社會越衰退,只有農民成為土地的主人,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才能適配,社會才能進步。
中國是現代化工業正在崛起的傳統農業國家,農民勤勞善良,貧困落后,從農村肇始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改變了農村面貌,農民吃飯問題得到根本解決,但改革沒有借鑒榜樣,前路怎么走?賈平凹以故鄉商州清風街為例,寫出世事的亂象和困惑。“一切都充滿了生氣,一切又都混亂著,人攪事,事攪著人,只能撲撲騰騰往前擁著走,可農村在解決了農民吃飯問題后,國家的注意力轉移到了城市,農村又怎么辦呢?農民不僅僅只是吃飽肚子,水里的葫蘆壓下去了一次就會永遠沉在水底嗎?”農村農民農業問題重重,土地和勞動如何有效結合進一步驅動財富創造也不是作家的責任,說清楚事實就行。
(四)文學書寫亦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合力之一
“政治現代化的源泉在城市,而政治穩定的源泉卻在農村”。邁向現代化是不同國家的目標,在實現這一目標的時段中,總會有人厭倦繁瑣,想要回歸純真。這種愿望代表了人類的一種普遍情感,并且通常要借助文學和藝術來實現。要塑造有活力和精神的城市,要建設宜居美麗的新農村,要讓人類文明進步之花開篇城鄉,城鄉之間的融合互動物我合一才會實現馬克思主義城鄉關指導之下的理想藍圖。“山是殘山水是剩水,只有狗的叫聲如雷”絕不是現代物質文明沖擊下的宜居鄉村。理想圖景中的鄉村決然不是一幅民生凋敝的慘相,城市也不是以文明之名壓抑人性的水泥動物園。
恩格斯的“歷史合力論”認為經濟是推動社會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力量,但不是唯一的力量。政治的、文化的、法律的,甚至是個人意志、文學的創造性書寫等,都會對社會歷史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艾利森(Ralph Ellison)說:“描寫廣大復雜的美國經驗中我最熟悉的片段,這些片段不僅使我可能對文學的成長有所貢獻,而且對自己心目中理想文化的塑造也可能略盡綿薄之力。”從小說文化學的角度而言,關注土地在城鄉關系中的流變,關注人和人性,從而探求現代性的物質追求的合理性存在和鄉村自在自為間的關系是當務之急。
(五)中國城鄉和城鄉中國須臾不可分離
除了城市,就是鄉村;除了鄉村,就是城市。中國城鄉,城鄉中國猶如鳥之兩翼,須臾不可分離。“城市工業就能騰出足夠的人員,給農業提供同此前完全不同的力量;科學終于也將大規模地、像在工業中一樣徹底地應用于農業”這不僅是發展的指向,也是路徑。天人合一、田園棲居、詩情畫意是中國城市傳統文化的精華,城鄉一體化的總體思路大致一理。美麗的田園風光對英國人已經成為一種世代相傳的民族遺產、文化符號和國家財富,為了所有人的利益,這份財富應當得到珍惜與保護。“亞細亞的歷史是城市和鄉村無差別的統一”歷史上如此,未來,“從事農業和工業的將是同一些人,而不再是兩個不同的階級”
以“城鄉文化命運共同體”為目標,城鄉文化應該在個人與社會的融合發展中“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文化傳播從來就是雙向互惠的,魅力鄉村和國際化大都市上海、羅馬等一樣也不是依靠某一群體的一己之力一天建成的。城市文化的強勢先進開拓創新;鄉村文化的仁厚精髓質樸向善都應是不同質性文化輸入輸出的側重點。不然,離鄉游子走在城市繁華街道上和初涉鄉村的城里人一樣茫然。“田園將蕪胡不歸?”精神陷入迷途,自然“奚惆悵而獨悲!”“覺今是而昨非。”
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談到城市和自然的融入問題時強調,“依托現有山水脈絡等獨特風光,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以“人物”“事件”“物像”“場所”為紐帶,以街區、村落、建筑、遺跡、工農業遺產、湖泊、林草、山水等為載體,有效保護不同城鄉的自我風貌,喚醒鄉愁延續認同文化記憶是戰略性部署。西湖、西子、白居易、蘇軾、《白蛇傳》與杭州;外灘與海納百川胸懷、弄堂與王安憶書寫的凡人凡事與上海;耿直勤勞重諾守節耕讀傳家與《鄉約》、白鹿原與陳忠實的生命體驗;商山洛水、賈平凹與雅致靈韻等才會成為有機融合的凝聚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