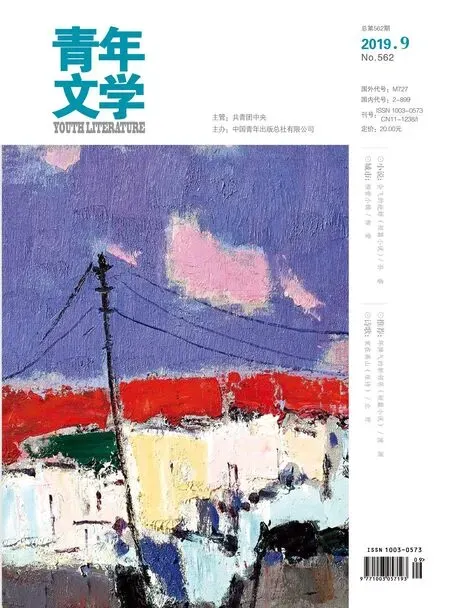聲 囂
文/陳思安
宇宙收納手冊撰稿人
生命、宇宙以及任何事情的終極答案根本不是“42”。所有人都被小老頭兒道格拉斯·亞當斯給騙了。在他的小說《銀河系漫游指南》中,“42”是“生命、宇宙以及任何事情的終極答案”。
而她非常確信,唯一正確的答案應該是——收納。她曾一度癡迷于尋找一切能夠將“42”和“收納”聯系在一起的證據,最終所有線索都只導向了一個結果:收納就是收納,收納本身即是答案,并不需要其他任何佐證。
沒有任何一種欣喜能超越將萬物規整,分門別類,收納入箱的快樂。在她的家中,任意一項物品,無論大小,都有其所對應著的收納箱或收納盒在等待著收納它。如果一項物品找不到適合門類的箱子或盒子被收納起來,那么它就不該存在于這個家中。
她深刻理解一個道理,每個人關于收納的哲學都大相徑庭。重要的不是認定一個絕對統一的收納標準,那跟人所痛恨的暴君還有什么兩樣?重要的甚至不是尋求理解。重要的,是在紛繁復雜的各種收納哲學中,形成屬于自己的系統和哲學。這是重要的。
很多人無法理解在收納中所包含的哲學。她也理解這一點。畢竟就算是你把宇宙真理整理好寫成書放在很多人面前,他們即便讀懂了每個字也未見得能明白其中道理。
塑料底座的臺燈該歸于照明系統,但鐵制的手電筒是該歸于照明系統,還是該歸于鐵制品呢?也就是說,定義它的,是它的功能屬性,還是它的出身質地呢?稀有藍水晶打造的昂貴酒杯,不舍得用它來盛酒喝,而是把它擺起來用作觀看。那么衡量它的,是在于其本身的實用價值,還是在于它作為裝飾品的觀看價值,抑或是它作為奢侈品的溢出價值呢?你看,這些,都是哲學。
任何人獲取真理的道路都是坎坷的,輕易就能獲得的東西也絕對不會是真理。歷經三次巨大的精神變革和數十次小的技術調整后,她總算是形成了自己相對穩定的收納哲學。盡管每次大小變動都意味著家里家外搞起裝修一般的龐巨工作量,成百上千只收納箱開開合合,所有物品重新分類反復歸整,但她在其中得到了自己一步步靠近真理的無法言喻的滿足感。定義一件物品的,應是它的功能屬性,而非出身質地。衡量其價值的,應是它自身的實用價值,而非溢出價值。
真理若是總結成語言,即是語言表現其蒼白的時刻。所幸,她時刻以收納的行動來見證著朝向真理的道路。
每日她行走在大街上,看著那些歪七扭八的胡同小道,高低錯亂的怪異建筑,纏繞一團的街道馬路,她便升起一簇簇說不清的煩惱。要是這一切都能夠被規整、收納,那就完美了。她時常幻想自己當上了市長,第一條政令便是將全市所有的建筑、道路、社區,分別按照區塊、個頭、長度進行分類歸納。最好可以定制一批巨大的收納容器來包裹覆蓋住它們。那樣世界將該有多美好。
可惜她只是一個普通文員。本市尚未產生女性文員當選市長的先例。不過她還有另外一個身份,不知道這個身份是否能為她的競選加分。
她是一位宇宙收納手冊撰稿人。這本《宇宙收納手冊》是她以行動見證朝向真理道路的哲學思考總集。上至宇宙星辰、銀河、星系,下至個人房間內部零碎物品,分別該如何分類歸納,她都進行了細致到個體物品的描述總結。她相信,一旦這部作品完成問世,整個世界將發生一些異常顯著的微小改變。
手冊中,個人房間、家庭內部及工作空間的收納部分業已完成,城市空間和全國各主要城市的收納部分在經過大量考證和查閱城市規劃類書籍后也已經艱難地接近完稿。在是否要將世界范圍內的其他國家一并納入書中的這個問題上她糾結了很久,最終選擇了暫時放棄。她更傾向于自己去做一個引導者、啟發者,而不是為所有人指定好一切細節的全能者。《圣經》《金剛經》《大藏經》寫出來的時候也沒考慮中國不是嗎,可沒妨礙我們閱讀和理解啊,所以我也沒必要考慮其他國家。哲學就是哲學,哲學是超越這些小事的。
最令她感到焦灼的,還是宇宙收納的部分。各類關于行星研究的書籍和網頁塞滿了她的書架和瀏覽器,她還要時不時跑到天文臺觀測塔用自己的眼睛感知一下這些遙遠球體的存在。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她不再為如墮一片星辰的深海般感到焦灼,而是獲得了神秘的寧靜。
每個夜晚,當她浸泡在發散著微弱光芒的星體中間,伸出她白嫩細長的手指將那些叫不出名字的光芒之球一一挑出,輕巧地放入一只只透明的收納箱中時,她清楚地知道,收納就是收納,收納本身既是答案。
痕跡
他曾在這里被禁錮了太久。現在卻沒有了蹤影。只有他的聲音在墻壁上留下了各種痕跡。像是兇猛的飛鳥拼命抓撓留下的。像是還不夠兇猛的斗牛以角反復撞擊留下的。像是憤怒絕望的獵槍里射出的子彈留下的。看著這些聲音留下來的痕跡,能夠幻想出他曾被困就此地時身體的形狀。不是痛苦的形狀。痛苦是所有形狀里最不接近他的那個。能說出口的總是太輕易。聲音拼湊出了他的形狀的交響曲,回蕩在空蕩蕩的房間里。他曾經反抗嗎?聲音的印跡無法證明他曾經反抗過。這樣說來,沒有任何事情可以證明任何人曾反抗過。如果不是為了反抗,那么他發出聲音,那些鋒利的聲音,又是為了什么?為了證明即便禁錮之下他仍有聲音想發出可發出嗎?人們嘗試把每一顆嵌入墻壁內的痕跡用紅色的線繩連綴起來。仍有信仰的人堅信只要找到正確的順序和方式將它們連綴起來,就會得到一部屬于他的抗爭的贊曲。或者說是,證據。人們又說,一個哪怕五音不全樂理不通的人,只要站在這間房間中央,撫摸著墻壁上的那些痕跡,便能唱出世界上最動聽的歌來。歌聲不是為了給任何人獻祭,只是需要掙破一根根喉嚨,與痕跡匯聚在一起。他還活著嗎,他已經死去了嗎?他是為了持續見證而忍受著不是痛苦的形狀繼續活著嗎,他是為了絕望地反抗而孤獨地死去了嗎?傳說疊加著傳說,一幀幀渲染墻壁上聲音的疤痕,編造著幽暗的神跡。
我的全家
我帶著我的全家一起生活。不,應該說,我的全家就是我的身體,跟我生活在一起。
左手是我的爸爸,他熱衷于將所有物體的油脂刮擦下來,盡其所能吸收入他的體內。頭頂滲出的發油,飯碗盤子底殘剩的脂肪,樹木被暴曬流出的汁液,汽車發動機迸濺出的機油,一切都可以成為他饑渴吸吮的對象。這讓我時常感覺到惡心,但我從不會反駁。爸爸總是對的。吸收這些可以保證我的潤澤和健康。
右手是我的媽媽,她是掌控著我全身這艘大船行駛方向的主舵手。大海航行靠舵手,萬物生長靠太陽,對于大多數習慣使用右手的人來說,右手就是他的舵手和太陽。不該吃的食物媽媽絕不會伸手拿,爸爸要是偷偷拿起來塞進嘴里,媽媽會把東西從嘴巴里摳出來。不該說的話媽媽時刻提醒嘴巴不要講,嘴巴要是不聽話,媽媽會一巴掌扇到嘴巴上。不該摸的人媽媽會指揮著爸爸一起把雙手插在臂環下。跟爸爸一樣,媽媽也總是對的。時刻監督著我不要偏離了人生的正確航向。
左腿是我的爺爺,他肌肉發達,彈跳有力,跟腱又長又有韌性,永遠是我的主力腿。右腿是我的奶奶,她相對纖弱,動輒發作的神經痛關節痛風濕痛是她的勁敵,好在她格外堅強,努力做到不拖累所有人,當好一條多病但好強的動力腿。跟我見過的大多數夫妻一樣,爺爺奶奶同時擁有保證我步伐一致穩健向前的感人默契和讓我一腳踏空撲倒在地的可怕爭執。好在爭執歸爭執,但是跟爸爸媽媽一樣,爺爺奶奶也總是對的。他們永遠能幫我走到我應該去的方向和應該到達的地方。
肝臟是我的姥爺,為我濾掉所有毒物毒素和藥物,凡想毒害我的必先過一遭我姥爺這關。腎臟是我的姥姥,幫我保持激素平衡,凡想影響我內分泌的必先得經過我姥姥的允許。胃是我的叔叔,給我腐化攪碎所有堅硬的外來之物,只為我留下柔軟和營養。腸子是我的姨,替我分辨一切好的壞的,該吸收的便吸收,不該吸收的果斷排出體外。
這就是我的全家。這就是我的身體。我的全家就是我的身體,跟我生活在一起。
真是,沒有比這更幸福的人生了。
同一條河流
為了能夠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他無法停下自己的腳步。被河水泡得發白腫脹的雙腳踩踏著水花,河底的砂石在他已經磨礪得如盔甲般堅硬的腳底板上碰撞刮擦出火花,旋即被水淹滅。他無法停下自己的腳步,沿著河水流動的方向大步向前,努力與水流的速度保持一致。漸漸地,他能夠用皮膚的毛孔感受到河水喘息的頻率,能夠用耳朵聽到水滴撞擊水滴發出的響動。他把自己心臟跳動的速度調整得跟河水喘息的頻率一致,把自己的步幅調整得跟水滴在河中飛翔的速度一致,他相信,總有一天自己能夠完全追上曾經踏入過的同一片水流。有人勸告他,這樣做毫無意義,因為你永遠無法真正跟上河流,即便速度跟上了,其中的每一粒水分子都已經改變。他的回答叫人不知該如何反駁。他的雙眼被河水浸泡得玲瓏透亮,仿佛也變成了一顆巨大的水分子。他用這樣剔透的雙眼望著勸說的人,喃喃回道,既然每個水分子每時每刻都在不斷改變,只要他付出的時間足夠多,追逐的距離足夠長,那么總會有那樣一個時刻,恰好可以踏入在他第一次邁進那條河流時每一個水分子當初的樣子。他不停歇地繼續奔跑追逐下去,沿著汲汲的小河跑進滾滾的大河,隨著滾滾的大河奔向分岔的小河。待到他終于隨著河水奔跑到入海口,他便折返回最初起始的地方,一切重新來過。傳言說,他之所以要這樣做,最初似乎只是因為愛人負氣的一句話。只是到了現在,因為什么而開始已經變得不再重要。終有一日滾燙的河水將煮沸他的身體,將他的血液毛發肌肉骨骼一一拆分為晶瑩的分子,與永恒變換的水流糾融為一體。他將永遠屬于河流。
收房
他并不算喜歡自己的工作。世界上除了離婚律師以外,最容易吸收伴侶關系負能量的職業,大概就是房地產中介了吧。尤其是租房中介。尤其是在大城市。尤其是負責合租。他和這行業里每個跟他差不多年紀的青年小伙子一樣,日復一日把頭發用發膠抹得锃亮,套著廉價的工裝白襯衫黑西服,踩著小電驢飛馳在負責區域的一個個樓盤里,反復聽著那些年輕的或已不再年輕的伴侶客戶討價還價斥責埋怨相互爭吵。這樣的日子過久了,他偶爾也會后悔自己怎么就干上了這個,搞到現在不管是對親密關系還是對房子都產生了抗體,具有了強大的免疫功能。
雖說談不上喜歡吧,但也不至于討厭。在出租房子這一整套流程中,他還是有一個算是喜歡的項目,那就是收房。這個小喜好是他不敢跟其他同事分享的,因為其他同事最討厭的事兒就是收房。
不講衛生的年輕租客跟這個城市里的外賣垃圾同步快速增長,中介們每次去收房的時候打開房門前都要先做上半小時的心理建設。沒人知道那些看起來普通的房門背后是一片怎樣狼藉的戰場。他所經歷過最狼狽的紀錄是,一戶曾住過三個單身男孩的房子在收房打開門時,地上堆積著兩百多個還遺留著剩湯水的外賣袋子,四百多個空啤酒瓶啤酒蓋啤酒罐,堆成一米多高灰白小雪山似的臟手紙,污黑到辨不出原本顏色的黏膩糊在一起的破襪子爛球鞋,以及仿如原子彈爆炸現場般碎裂滿地的各類電子元件。其他同事捂著口鼻開窗通風想趕緊散盡屋子里窖藏了陳年老尸似的惡心氣味,他卻被屋子里那幅好似當代裝置藝術布展現場般的景象給吸引住了。能折騰成這樣,不僅得有點忍耐力和韌性,簡直還需要有點想象力啊。
拋開這樣的極端個例不提,每次去收房時,他還是會對那些被前主人們留下的東西感到驚訝。那些曾經緊緊依附于主人生活場景中的物品,孤兒般被遺棄在主人離開了的出租屋中。換句話說,它們對于主人已經再也不重要了。不重要到,連被主人親自丟進垃圾桶的必要都沒有,就那樣被留在人去房空的屋中,任由中介去處理。盡管同樣是被扔掉,他覺得被主人親自扔掉總歸要好過于被帶有怨氣的中介扔掉好。套用那句流行的雞湯話說,就是被主人親自扔掉,至少還得到了一個好好的告別嘛。為了給這些已經不被需要的物品一個好好的告別,他經常自告奮勇主動承擔清理雜物的工作,在將那些物品丟進垃圾桶前鞠一個躬,輕聲說一句,之前辛苦了你喲,現在就請安心地去吧。
長相奇特的各種毛絨玩具,破損的衣服鞋襪床品,凌亂的書籍,油鹽醬醋鍋碗瓢盆,用舊掉的櫥子柜子架子椅子,世界各地的明信片冰箱貼,鍵盤鼠標硬盤數據線充電器,廉價的戒指耳環項鏈掛墜,前愛人們的照片筆記本小相冊,壞吉他破笛子斷弦二胡掉頭小提琴……這些都是他經常鞠躬告別的物品。整理這些不再被需要的物品,與它們短暫地相處,再體面地告別,這個簡短但可稱溫馨的過程柔化了這份工作的堅硬,也柔化了這座城市永遠灰突突的色調。這是他能夠堅持生活在這座城市里的一種途徑。
然而總有一些東西,是他沒有辦法輕飄飄地告個別再丟進垃圾桶的。這個道理是他在打開了一扇房門,發現里面蹲著一只喵喵喵叫喚個不停的小花貓時才猛然意識到的。同事們勸他把貓放進小區院子里,做流浪貓也好,被其他人家收養也好,總之是不能自己帶回家。這個頭一開可就麻煩啦,現在的租房客最講究“斷舍離”,不需要的東西轉手就要立刻丟掉。人生已經夠沉重的啦,怎么還能負重前行呢。他把小花貓捧在懷里啜喏道,要是感到沉重,一開始又何必要背上呢,它也是生命啊。
同事們說得一點沒錯。這個頭一開,他自己租著的房子日漸變成了一家小型動物園。仿佛整個城市的租房客都聽說了有這么一個可以接手被遺棄寵物的租房中介員,特地跑來租他的房。兩只三花小奶貓,一只白色老公貓,一只手掌大的巴西龜,六只灰殼獨角仙,一只棕毛折耳兔,五條紅艷艷的小金魚,三只被染了色的肥倉鼠,相繼來到他的房子里。
他相信自己不會在這座城市里一直生活下去。他不喜歡一個讓人可以輕易丟棄一切的城市。他也相信自己無論何時離開,一定會帶著租住房子里的一切一起離開。他對自己說,在那之前,就暫且由我來負著這城市里一角小小的重而前行吧。
對稱
沒人說得清楚到底從何時起村子里形成了這種風俗。
地上蓋著活人居住的房屋,地下以同等規模尺寸蓋起死者居住的墓穴。
地上與地下的房屋結構嚴格對稱,形成兩個鏡像相對的空間。
人們生前在地上的房屋里活動,死后旋即轉入地下休憩,陰陽僅由一層薄薄的土坯相隔。
生與死的過渡平滑如水中游鰻,除了進出人體的那縷呼吸外,地上與地下仿佛一切照舊。
新出生的嬰孩,啼哭聲穿透地層,撫摸祖父的皺紋。
思念母親的女人將耳朵附于墻面,傾聽下方空洞里發出的陣陣嗚鳴緩除傷感。
因死亡錯過兒子大婚的父親,借助空氣的抖顫指導新人們不夠嫻熟的親熱動作。
在這個村子里出生的人,無論走到再遠,死前也會掙扎著將自己運回故鄉。
那個地下世界密詔般時時呼喚著他們。
對此,他們毫無其他選擇。
扮演
她正面朝下趴在按摩床上,全神貫注地扮演著一個時刻逆來順受,無論身體抑或心靈有再大傷痛也要沉默忍耐的人。按摩師的手指按壓著腰椎兩側硬度賽過大理石的勞損的肌肉,她牢牢咬緊牙關用力憋緊嘴唇,誓死要將所有沒出息的呻吟都悶死在喉嚨深處。旁邊房間里其他客人的呻吟尖叫聲此起彼伏,她在內心默默贊賞自己的隱忍,看來這一輪扮演還是相當成功的。深入角色內心的秘訣是,她不斷在腰肌痛到幾近暈厥時提醒自己,怎樣的痛才痛得過心靈受傷之痛呢?這點皮肉之痛相比之下算什么!
進入按摩院之前,她扮演的是一個在不公正的愛情關系里無故遭受不白之冤,被愛人深深誤解無可挽回乃至遭到拋棄的人。她不得不獨自坐在身旁仍散發著愛人屁股余溫的空座椅上,眼角掛著冰冷的淚珠,自己享用完一碗辣得讓嗓子開花的熱干面。扮演這個人物的難度系數較高,畢竟從大學畢業以后迄今為止七八年來還沒有再談過戀愛。不過沒關系,作為體驗派的勤奮學習者,她能夠通過努力釋放自己的感受想象力來解決這些經驗的問題。她一邊喘著粗氣艱難地咽下掛滿了辣子的面條,一邊對自己說,不管他是不是真的不要你了,你都要把自己喂飽喂好,因為你也值得得到很好的照顧啊。
走進熱干面面館之前,她扮演的是一個將生命中絕大多數個人時間投注于健身事業的開朗的肥胖癥患者。盡管她只有四十七公斤,但這并不能妨礙她扮演一個一百四十七公斤的肥仔,想象力的能量和表演的激情能夠驅使腎上腺素加速分泌,幫助她舉起三十公斤的杠鈴。我是個胖子,但我絕對不會絕望!終有一日我要瘦到讓你們所有人嘆為觀止!她望著鏡子里瘦削的人影,握緊雙拳給自己打氣。
去健身房之前,她扮演的是一個在公司里八面玲瓏如魚得水,上至董事長下至清潔工都有成噸的話可聊,樹敵不多未來大好的精致白領。每天朝九晚五不時加班演出的節目是哎呀我好忙哎呀我的工作好重要哎呀公司離開我簡直運轉不下去。跟其他臨時角色不同的是,這個角色參演的是一部長篇連續劇,不是即興短劇,因此需要持續接得上戲,不能有太多不符合角色設定的超綱發揮。不過還好,對于社交恐懼癥患者的她來說,演出完每日戲份已經足夠疲憊了,精力上沒有太多超綱發揮的余地。
曾經她對此感到厭倦甚至反感,一部連續劇演上幾年十幾年,怎么著也會感到素材庫空虛,自我重復吧。不過很快地她主動扭轉了思維。有限制,才能強迫你發揮創造力啊同志們。就好像沒有監獄做對比,哪能顯得自由分外美好,沒有霧霾天做映襯,哪能讓人對藍天格外感恩呢。更何況,在長篇連續劇之外,這不是還有諸多即興短劇可以調節情趣,釋放天性嘛。
通過不斷扮演各種角色,她獲得了所謂“生活”的真正樂趣。自己體內和顱內深埋著無盡寶礦,她不斷在其中掘出悄無聲息隱藏起來的各式各樣的人格,抖去陳年累積的塵土,煥發出新的色彩。她同情所有尚未發覺這種真正樂趣所在的可憐人類。今時今日的世界上,哪里還有什么真實的生活啊,就算有,那種生活里哪還有什么激動人心的內容存在啊。所謂生活的真諦,只在于全身心投入地去扮演好角色們罷了。
生命被死亡用力托起的時刻
生活在大陸深處那片荒原地帶中的居民,他們每個人一生中都會死去三次。
第一次死亡是在他們出生當天。青紫的嬰兒以強有力的啼哭宣告自己帶有死亡氣息的降生后,旋即沉入絕對的安靜,使產房凝為死寂。嬰兒的呼吸停止,心臟也不再跳動,周身的皮膚由青紫向黑色逐漸過渡,仿佛一幅迅速且過度風干的油畫。
醫生們不會呼天搶地地給嬰兒做心肺復蘇企圖搶救,他們只是用干凈的巾被將黑色的嬰兒輕輕包起,交到父母手中。嬰兒在父母溫熱的懷抱里身體一點點蘇醒,嫩粉色緩緩摻入黑色的皮膚中,如兌入其他顏色的顏料,呼吸也在某個靈光般的時刻重返他們微弱的身體,生命于是再次降臨。死亡自此成為他們最親密的朋友,由出生之日起便盤旋在他們的身旁,與他們相伴的時間比父母親人更加長久。
第二次死亡是在他們人生的中段。這個中段,不是一個大概的數字,而是將他們一生所有被稱之為是“活著”的時間除以二,一秒也不多,一秒也不少。對于這里的居民來說,死亡并不令人恐懼,他們早就跟死亡朋友般地相處,然而在三次死亡中,如果說有一次是令人傷感的,那么就是這第二次死亡。因為在那一個時刻,他們將清楚地得知自己還有多少剩余的時間屬于這個世界。
這第二次死亡的到來沒有任何預兆,他們有可能正在做著任何事。也許正站在自己婚禮被所有人祝福的舞臺上,也許在地里插秧,也許臥在愛人繾綣的臂彎里,也許恰好抱著正在自己懷里從死亡中漸漸復蘇回來的剛剛出生的孩子。
與他們出生時遭遇到的第一次死亡的情形類似,沒有人包括他們自己會在經歷第二次死亡時痛苦萬分涕淚橫流。最多,只是有一些傷感。他們會從自己死去時倒在的地上迅速爬起來,努力在已經確知的余下的時間里認真生活。有人會從第二次死亡后復蘇的第一時間查看鐘表上的指針,以保證自己能夠完全掌握余生點滴的流逝。也有人完全不去在意時刻,甚至故意用力忘記第二次死亡的時間,好去享受一個仍然不確定的未來。
有時一個嬰兒在清晨出生迎來第一次死亡,中午卻會死去第二次,人們于是用整個下午為它準備喪葬用品及遺奠,因為它將在晚上迎來第三次死亡。這第三次的死亡,是真正的死亡。徹底地死去。呼吸不會再如靈光般返回,血液不會重新汩汩流動,也不會再有粉紅色如顏料般摻進黑色的皮膚中。
這里的人們不會為了過早的夭折而哭泣,也不會為了長壽而開懷。如果家中有三個人,在每日餐飲時則擺有四副碗筷。多出來的那一副,是留給死亡的。死亡是他們家中的成員,迎來不必慶祝,送走也不感傷。
在這三次死亡之中,伴隨著出生而到來的那第一次死亡,是令每個人都略感欣喜的。因為那是他們確定了,生命是被死亡所用力托起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