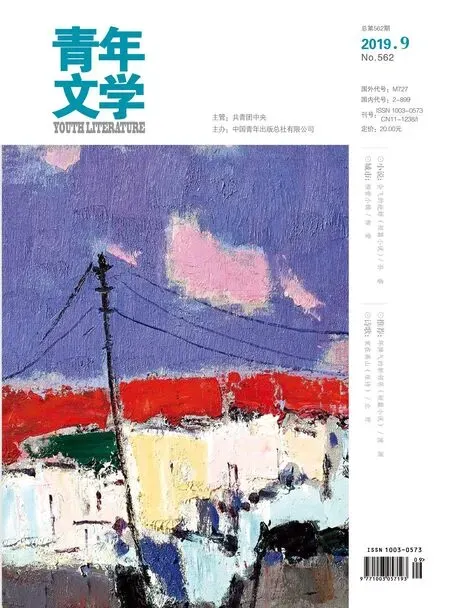頭發那些事
文/林 肖
頭發這東西真怪,任你怎么剪剃拔吹蒸燙拉染,它非但無礙,反倒源源不斷地長出,如新如故。人體其他各種零部件,一旦有損壞,大多不能再生,即使再生也不及“原裝”的好使;而頭發不然,百摧不屈,無怨無悔,“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頭發的最初形態應是純乎自然的。原始人不論男女都披頭散發,想來他們生長于荒野叢林,生存環境惡劣,不會有什么心思去打理頭發;何況原始人通體毛發叢生,頭發多長多亂,也就無甚關礙了。后來人類文明發展,人們才意識到是該打理一下頭發了,可是受“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古訓所囿,頭發不能隨便剪斷,于是只好把頭發綰起來,插上簪,編成個髻,或頂在頭上,或扣在腦后。這個變化,當是文明的一大進步,這時,文明社會中如果還有披頭散發的,大約是非常之人,要么困厄而披發佯狂,要么憤世而披發行吟,要么隱遁而披發入山,皆非常人所能相擬。這種人雖不在多數,但頭發綰起后又放下,世俗百態已昭然若揭。
高高的髻頂在頭上,男的還要綁上頭巾,戴上帽子,尤其是士大夫一族,“峨冠博帶”是身份的象征,來不得半點含糊。屈原就是戴著高高的帽子,系著寬大的帶子投了江。孔圣人的得意門生子路,在衛國內亂中慘死于亂兵刀劍之下,死前還不忘把被砍斷的帽帶系好,“君子死,冠不免”,這其中含著幾分令人肅然的正氣。女人的髻花名目肯定繁多,不然中國文學里描寫美人的詩文不會動不動就牽扯上頭發。曹植在《洛神賦》里寫他心中的美人時就說:“云髻峨峨,修眉聯娟。”“峨”即“高”的意思,想來古代女人以發髻高為美。《漢書·馬廖傳》里更說:“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一尺高的發髻堆在頭上盤旋如云,會不會有點嚇人且不說,至少說明古人的審美眼光迥異于今人。最常見的還是“云鬟霧鬢”之類修飾語。杜甫想念他夫人時寫:“香霧云鬟濕。”溫庭筠的《菩薩蠻》里也有“鬢云欲度香腮雪”的句子。更有陶慕寧著《青樓文學與中國文化》一書,將女人長長的秀發從唐朝一路拖到晚清:“花映垂鬟轉,香迎步履飛;口嗑櫻桃破,鬟低翡翠垂;綠鬢云垂,旖旎腰肢細;髻鬢低舞席,衫袖掩歌唇……”長長的一串,非“鬟”即“鬢”。美人盤起的發髻再迷人,兩鬢松松掉下的幾綹烏云再撩人,早就沾染了千年的閨中香艷和才子筆墨,終究抵不過審美疲勞的暗中滋生。還是曹雪芹寫晴雯頭發用的“挽”字,形神畢現。抄檢大觀園風波時,晴雯“挽著頭發闖進來”;寶玉的雀金裘被燒了個洞,她“挽了一挽頭發”咬牙補了一宵。這匆匆的一挽,比起“云鬟霧鬢”來要風姿卓絕得多,曹雪芹不愧為寫言情文學的高手。
把頭發與煩惱關聯起來的說道,自古就有,可究竟典出何處,細加考證似無必要,只知道詩人愁悶至極便說:“白發三千丈,緣愁似個長。”聽了這話,和尚就要發笑,笑世人想不透看不穿,像他們那樣斬去三千煩惱絲多好,圖個內心清凈無欲無求。滿清入關,下剃頭令,“有頭皆可剃,無剃不成頭”,但奇怪的是,這種頭剃得陰不陰陽不陽,還拖了條豬尾巴似的辮子叫外國人嘲笑了三百年。不過到了晚清,人們突然發現辮子也非絕無一用。馮驥才的小說《神鞭》里的傻二,腦后一條辮子竟然練得神出鬼沒,抽得洋人鬼哭狼嚎找不著北。頭發戰勝了刀槍,“豕尾”變成了國粹,這是國人萬萬沒想到的,泱泱中華可炫可耀的資本何其多哉,難怪辜鴻銘老先生要晃著腦后的辮子說,“這是我的護照”。辮子之可贊美真可謂彰然明矣。
西方人頭發天生鬈曲,頗具“藝術感”,古典時代的貴族們尚嫌不夠優雅,還要戴上假發,撲上香粉,堂而皇之出入社交場合。晚近西方人對這些虛偽的繁文縟節狠狠顛覆了一把。蓋自“披頭士”樂隊始,西方男子蓄發成風。“披頭士”之長發落拓不羈,含納蔑視世俗、反抗傳統的精神追求,然而世人多屬無聊跟風,以致“嬉皮士”泛濫成災。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國沿海城市的街頭也開始出現長發“怪客”,彼時國人思想觀念封閉已久,男女老少的發式都踐行著“響應組織”的號召,頭發長及耳根者常被視為異端,招來白眼,就連孩子們都會跟在長發男后面指指點點:“看,壞人。”及至上世紀九十年代搖滾樂盛行,校園里經常可見長發及肩的歌手,遠看男女莫辨,近看仿佛丐幫弟子,經常鬧出笑話。說起藝術家的怪發亂發,我等天生缺乏藝術細胞,不能領略其妙處。藝術家即“異術家”,想來必異于常人,普通人難知就里,又不敢枉自揣度,只能心存仰慕,或者敬而遠之;至于名士之流不修邊幅,怒發蓬松,招搖過市,那也是當地人文一大勝景,輕易抹殺不得。
文明真是愈加燦爛了,當今男女頭發爭相引領風光,至少說明在物質豐盈的時代,人們很愿意把心思花在頭發上。于是,女人們在拋棄了“兩條辮子”“清湯掛面”和“雞窩頭”后,開始把頭發染成金色栗色玫瑰紅各種色彩,燙成洋人頭發般的波浪起伏,甚至怪發莫名,翩翩而過,風情堪稱旖旎,讓人產生置身外國街頭的錯覺。友人某君有個笑話;其妻體型肥大,某日新染了一頭金發,某君夜半睡醒,駭然發現身邊躺臥一“金毛獅王”,頓時驚出一身冷汗。此類笑話只資助談興,女人們不管這些,對她們來說,不吃飯是為了減肥,折騰頭發那叫本能。男人們則相對簡單,除了蓄長發以外,頂多就是學學心儀的明星的發式,鼓搗范圍有限。倒是足球場上怪發頻現,如今球員們球技不見長進多少,整起頭發來卻是挖空心思:爆炸頭、莫希干頭、雞冠頭、臟辮……叫人真不知該看球還是看人。倒是很懷念八十年代的綠茵場,那時的球員平頭精神,光頭耀眼,禿頭可愛,長發瀟瀟灑灑,頭發清爽,球也踢得清爽。
傳統的人終究還是傳統,我們經受不了射在頭頂的目光,只能老老實實地走傳統路線。當學生時,頭發野性勃發,長勢極旺,生性又不愛理發,便容易攪成一團糟,個把月的時間蓄下來,腦后可以用橡皮筋扎一把了。如此“惡劣”的頭發自然不入老師法眼,遇有常規檢查,我總在被喝令理發之列。上大學后,心想是該弄個清楚點的發式了。可是對半開吧,感覺像“漢奸”;板寸吧,又好像悍匪,于是為保險起見,還是讓頭發以三七倒伏的姿態順乎天命。按理說,這種分頭剪起來是最省力的,可每次理發師都要抱怨絞薄我的頭發就像掏鳥窩,完了還得問我:“你是左邊分還是右邊分?”
折不折騰頭發看來都是麻煩,而且步入不惑后,漸漸發現身邊不少同學朋友頭發已然稀疏,甚至牛山濯濯。我雖不必為此煩惱,卻也擔憂著有一天頭發變白,一根根掉落,進而成燎原之勢。等到那一天,我想我同樣無法回到烏發滿頭的光景。唉,想想頭發嘛,不過是蓋在頭頂的一層毛,有能力作為的就讓它們風姿招展,沒能力的就只好消極努力著,不去生頭發的氣,不去惹頭發的麻煩。有人費盡心神地搜尋生發劑,乃至植發種發;或者怕以皤皤白首見人而染成油亮黑頭,以求自我麻醉,卻不知容顏老去,皮膚皴皺,其狀甚怪也。花開有花謝,樹長有榮枯,頭發亦自然一景,對不起旁人眼光時,就當自我欣賞樹林之葉飛葉落,似乎倒也不壞,或當如孟德斯鳩所言,吾力之微正如帝力之大,無論怎么掙扎究竟有何用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