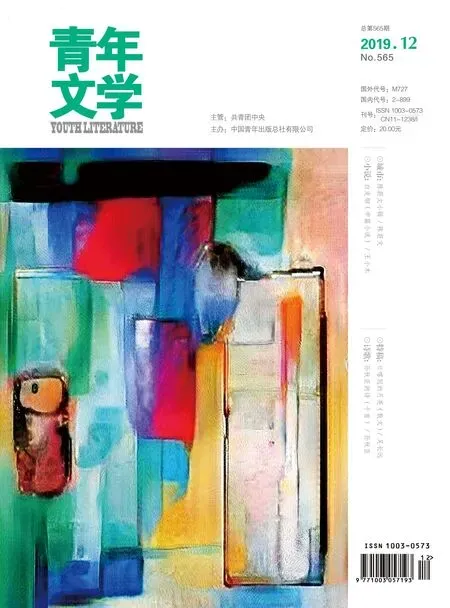微風細雨
文/蔡曉妮
一
玉秋上車的時候就注意到了那個男人。他在人群中很搶鏡,穿著黑色背心,下面是條軍裝褲,背了一個黑背包,兩條特別粗壯的胳膊露在外面。最搶鏡的是膀子上兩個花樣復雜的龍文身。玉秋見過不少有文身的男人,每次看到都躲得遠遠的:那些浮夸的紋案讓她覺得恐怖,覺得流里流氣。但這個男人有些特別,至少玉秋看到他的時候沒有感到那么討厭。那兩條文身和他很相襯,在他安靜的氣質中增加了一絲特別。地鐵里,他就站在玉秋的旁邊,她忍不住多看了那個男人兩眼。更讓玉秋奇怪的是,這個男人始終目視著前方:他肯定意識到玉秋看著他的文身,卻沒有不自然,也沒有回應,像沒看見玉秋似的。玉秋也沒太在意,畢竟萍水相逢,誰也不認識誰。地鐵時間很長,因為玉秋是坐車去機場,差不多有二十多站。坐在玉秋旁邊的男人特別猥瑣,不停地拿眼睛偷瞄玉秋,玉秋反感極了,忍不住惡狠狠地瞪了那個男人幾眼,那個男人卻不收斂。于是玉秋抽了個空,坐到地鐵車廂另一邊遠一些的位置。那個有文身的男人坐在了玉秋剛才坐過的位置上。
到了機場,過安檢的時候玉秋看到了那個男人遠遠地排在了隊伍的尾巴,她想還真是挺有緣分的,一車廂的人,居然他們倆都是去機場的,難道他也是去馬來西亞的?好巧不巧的,上了飛機后,玉秋還真的看到了這個男人,就坐在她后兩排。因為沒有錢,玉秋坐的是廉價航空,其實她的內心是很怕的。到了馬來西亞的沙巴都已經夜里十二點多了,也不知道表姐靈清約的人能不能準時接機。這是玉秋第一次坐飛機,也是她第一次出遠門,人們都說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可玉秋老覺得外面的世界很無奈,她寧愿待在老家,永遠也不出來。你說怪不怪,別的二十歲的姑娘都盼著出來,只有玉秋不肯。她初中讀完就不讀了,早就可以出來打工的,村里像她這樣的小姑娘早早地就出來闖世界了,她還封閉得很。一方面是玉秋自個兒膽小,另一方面是她媽不肯。她媽三十歲就守寡了,帶著玉秋過,日子過得自然是苦的。寡婦門前是非多,她媽門前的是非的確是不少,因為她媽年輕時長得太美了,這人一美,又是個寡婦,能沒有是非嗎?但好在玉秋的媽媽芬玉是一個木頭美人,別人對她的情意她統統都感受不出來,特別不解風情,想和她調調情你都會感到像嚼了木頭似的,一點味道沒有,還一嘴的木渣子。久而久之,芬玉得罪了不少男人。所以芬玉這些年也吃了不少的苦,男人們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編派了不少芬玉的壞話,說她克夫,那方面有問題,芬玉表面上無所謂,木頭人一個,心里恨得牙癢癢。因為不肯求人,所以家里的農活兒都得芬玉一個人干,娘家的弟兄們因為她不肯改嫁,都和她鬧翻了,加上自顧不暇,只能得空的時候幫幫她。幸好她的本家姐姐春玲不時地會來安慰她,農忙時春玲的丈夫阿豪不時地來幫幫忙,芬玉這些年的日子才勉強過了下去,一個人也算把玉秋拉扯成人了。本來她是不舍得玉秋出去打工的,但這兩年她身子越來越差了,玉秋看她虛弱的樣子,心里太難過了,這才求了春玲的女兒靈清幫忙找了現在這個工作,到馬來西亞的一家中國餐館當廚師。說起來,玉秋從小做菜就很有天賦,同樣的菜她做得就是比別人好吃,沒想到這無師自成的手藝將來能掙口飯吃。
人的一生真是奇怪,有些人就是比你強,也許你用盡全力也無法和她打個平手。玉秋從小就很羨慕表姐靈清:有父母疼愛,讀了中專,學了旅游管理,畢業后在老鄉開的旅游公司工作,被派到馬來西亞做地陪導游,賺了不少錢。春玲沒少在芬玉面前炫耀,芬玉每次都要對春玲說:“我們家的玉秋要是有你家靈清一半好我就滿意了。”春玲每次都說:“那有啥,讓靈清在馬來西亞給她找個工作啊。”芬玉每次都擺擺手說:“你家靈清多聰明啊,她能做的事情,玉秋做不了,咱們家玉秋什么都不會做,除了會做菜。可是誰要她做那些家常菜呢,現在的廚師都是在廚師學校學的,你沒看電視上經常播的那個新東方廚師學校,而且都是男人在學。一個女人哪好去做廚師呢?”春玲被芬玉這么一說,只好回道:“會有辦法的,在家也挺好的。”
閑著無聊,玉秋喜歡看一些書。她印象中有個作家說:如果你沒有美貌健康,你還有很多錢和愛的話,那也算不幸中的萬幸;如果你既沒有美貌健康和錢,但你還有愛,也是不幸中之大幸;如果四樣都沒有,那活著就是痛苦。玉秋想自己的媽媽不就是什么都沒有嗎?即使曾經有過的美貌,也被歲月磨損得雨打風吹去了。這四樣東西都不易擁有,能得一樣已是上天垂憐。這個世界上只有極少數的人越活越從容,歲月沉香,波瀾不驚。大部分的人都把生活過得破敗不堪;生命不是一襲華麗的袍,上面爬滿了虱子,而很有可能就是一襲普通的袍,上面還有不少破洞。
在飛機上,玉秋糊里糊涂地想了不少,把媽媽和自己的前世今生在離地幾千英尺的天空中翻來覆去想了個遍。廉價航空沒有提供餐飲。玉秋吃著隨身攜帶的媽媽烙的餅,感受著媽媽的情意,想著幾千里外的媽媽是不是睡不著也在想著自己。這樣想著想著,醒醒睡睡,居然四個小時就過去了。
下了飛機,來接玉秋的人還沒有來。玉秋在微信上聯系表姐,表姐說那個人會舉個牌子上面寫著譚玉秋三個字,可是玉秋在出口處等了很久也沒有等到這個人。玉秋就想去換馬幣,走的時候比較匆忙,沒有來得及換錢。七月的沙巴夜晚居然不太熱。玉秋到了自動取款機那兒,搗鼓了半天也沒有錢取出來,旁邊的一個馬來人比畫著說:“取款機沒錢了。”玉秋很絕望,連買水的錢都沒有。她正難過和害怕的時候,那個地鐵上有著文身的男人剛好經過,看了一眼玉秋說:“你怎么啦?沒有錢也沒人來接?”玉秋難過地點點頭。那個男人對玉秋說:“接你的人的電話呢,我來幫你打。”打通了電話,那個人說正在路上,快到了。玉秋瞬間覺得踏實了一些。她問道:“你叫什么名字?”
“秦正新。”
“你也是廣東來的?”
“是的。”
“我們是老鄉啊!”
“聽聲音就聽出來了。”
兩個人相視一笑。不一會兒,來接玉秋的人就來了,玉秋趕忙要了秦正新的聯系方式,兩人揮手作別。
二
玉秋到了大豐海鮮館。這家海鮮館在沙巴最熱鬧的一條街,生意非常好,在國內的美食網站上都有介紹,慕名而來的人絡繹不絕,據說有不少明星都來吃過。這樣的餐館對廚師的要求自然是很高的。玉秋為什么能來,還不是因為靈清的三寸不爛之舌,靈清的嘴真的是太能說了,能把死的都說活過來了,所以靈清做導游才做得這么風生水起的,沙巴大大小小的中餐廳都要給她點面子,她在客人面前多說一點兒就很可能給餐廳帶來不少的客源。所以玉秋不是廚師學校畢業的,也可以來做廚師,不過先要做學徒,要跟著主廚霍青松學手藝。說起來,霍青松在業界也是鼎鼎大名,做的菜火候準、味道足、口味鮮。靈清和他夸了海口,說玉秋做菜的水平那是一流的,同一道菜沒有一個人做得比她好吃。靈清愛喝酒,霍青松也愛喝酒,喝酒喝多了,霍青松就好說話了。其實霍青松一點也不老,不過四十五六歲,這個年紀對男人來說正當年。大家不知道他來自哪里,只知道他以前也是叱咤風云的人物。霍青松沒有家人在這里,日子就過得很閑,除了做菜沒什么別的事情了,最愛的就是呼朋喚友地喝酒打麻將,海吃海吹。所以大家都很愛和霍青松接觸,因為他看起來最沒有煩惱。然而,往往看上去最平淡的人,胸中的溝壑最多,多到你無法想象。靈清有一次喝醉了問霍青松為啥會到這個地方來,霍青松說:“說出來你不會信的,會嚇死你的。”靈清纏著霍青松問個不停,霍青松不肯說,默默走開了。靈清和霍青松的性格很投緣,靈清看上去精明,但實際上蠻二的,常常被人騙。之前談的那個男朋友就把靈清騙得厲害,幾乎把她這些年的積蓄都給騙光了。他把靈清甩了的那天,靈清仿佛要把一輩子的酒都喝光,霍青松一句話也不說地陪著靈清喝。喝著喝著,霍青松喝得比靈清還多,靈清本來挺悲傷的,后來都被霍青松嚇傻了,忘記了喝酒,就看著霍青松喝。靈清再傻也知道,這樣喝會死人的,酒也嚇醒了一半。她搶過霍青松的酒說:“你瘋啦,能少喝點嗎?失戀的是我,被騙的是我,又不是你,你搶我什么風頭!”霍青松冷哼了一聲說:“知道喝酒沒用了吧,知道那種男人不值得你傷悲了吧?喝完這一夜,回家睡一覺,什么都忘了,忘不了我就看不起你靈清。”說完霍青松拎著酒瓶,晃晃悠悠地走了。
霍青松外表冷冷的,臉上沒啥表情。他煙癮很大,做菜的時候也喜歡叼根煙。做菜的手法總讓你覺得他不像是一個廚師,倒像是一個將軍在指揮千軍萬馬打仗。但廚房這個戰場太小了,所以霍青松特別收斂,有些放不開手腳,仿佛生怕動作過猛,就收不了場了。霍青松肯定是不屬于廚房的,但霍青松屬于哪里呢?沒有人知道。玉秋這么秀氣的人和霍青松在一起做菜,肯定是不太合拍。霍青松每次看到玉秋把蔥、生姜、蒜瓣、洋蔥等一干配菜切得一絲不茍,如同列隊行禮的士兵,就會說一句:“你整的這些什么勞什子?”這時候,玉秋總是抬起頭,用無辜的大眼睛看著霍青松說:“咋啦,霍師傅?”霍師傅擺擺手說沒什么,就走開了。私底下,霍青松對靈清說:“你這個表妹怎么和你一點都不像呢?她那么拘謹,現在也有二十了,也是個成年人了,怎么還搞得像十五歲似的,這樣在社會上怎么混。”靈清說:“你真是閑吃蘿卜淡操心,說不定人家比咱們過得都好呢。”
三
玉秋送菜到客人桌上的時候,不小心把蛤蜊湯給灑了。她忙不迭地道歉,卻看到客人中有秦正新坐著,不由得驚喜地叫了起來。秦正新也沒有想到玉秋會在這個場合出現,趕忙站了起來說沒關系。同行的客人中,有個姑娘的衣服上沾了湯汁,丹鳳眼一豎,不肯放過玉秋,非要玉秋賠償。秦正新對她擺手說:“沒關系沒關系,認識的人。”姑娘依然不依不饒,跑到秦正新面前,把自己那件低得已經不能再低的低胸裙扯給他看,說:“你看她把我新買的衣服弄成什么樣了,很貴的呢,這是香奈兒的最新款!”她扯的幅度太大了,大半個胸部都暴露在秦正新面前,秦正新趕緊別過臉去說:“我賠你。”姑娘斜著眼睛看著秦正新說:“這可是你說的啊,別后悔。”秦正新說:“那當然了,我說話算話。”姑娘這才心滿意足地回到自己座位。玉秋認得這個姑娘,她是這里一個木材商人的女兒,愛玩愛瘋是出了名的。這個叫林寰寰的姑娘挑釁地看了過來,玉秋有點手足無措地站在邊上,眼淚都要流了出來。出來混口飯吃真不容易,家里雖然窮,可是阿媽不至于讓自己受委屈。秦正新走了過來,把她拉到邊上說:“你還好吧?”玉秋囁嚅著說:“還好,給你添麻煩了。”秦正新說:“哪里的話啊,出門在外誰不遇到點麻煩。”秦正新說他在沙巴一個形狀很像貝殼的島上做浮潛教練員,邀請玉秋去貝殼島玩。
玉秋約了靈清和霍青松一起去。不知道為什么,平時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霍青松,這次居然肯出動大駕。靈清驚呆了:“太陽打西邊出來啦,讓您老也肯出來曬曬太陽了。”霍青松訕訕笑了兩下說:“我是怕你們兩個女孩子不安全。”靈清哈哈大笑說:“你真逗啊,我走南闖北的,你忘了我是個導游啊。”霍青松無語了,說:“女孩子家不要總這么托大,這個世界上有太多意外的事情發生。”
到了貝殼島,秦正新帶他們一路逛逛,看看紅樹林,吃吃椰子。紅樹林真的很神奇,秦正新帶玉秋逛了一圈之后,說:“其實老在這個島上也挺無聊的,走一個小時不到這個島就逛完了,待久了,真的好想家。”玉秋踢踢腳下的沙說:“有啥不好的呢,這里的空氣這么好,水這么清,人的心靈也和這海水一樣,那么藍那么清澈。”說完玉秋深深吸了一口空氣。是誰說過這個世界上最美好的東西都是免費的,陽光空氣海水,這一切真美好。可是回到陸地上,那一切的不美好都回來了,而且都不是免費的。如果把世間比喻成一片海洋的話,人就是漂浮在海上的浮木,一根一根,不知要漂向哪里,在一起的也可能走一段就走散了,不在一起的也有可能因為浮力而走到了一起,漸走漸遠,漸遠漸近,一切都在變化中。回去后,玉秋接到了春玲的電話,說芬玉生病了,芬玉不讓春玲告訴她,但春玲看芬玉一個人拖著病體熬得那么艱難,還是決定要打電話給玉秋。接到電話,玉秋就立刻買了機票飛回老家。
辛苦了大半輩子的芬玉,最后還是沒有逃脫病魔的折磨。生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會被這件事打敗,你會沒有錢治病,也會有錢也治不了病。芬玉這兩樣都攤上了:即使你有機會花錢買命,你也會很痛苦,血淋淋的痛苦,血淋淋的痛不欲生。都不是最佳方案。芬玉的這種病其實是長期的情緒不愉快造成的,她心情一不愉快就吃不下飯,久而久之就得了胃病。玉秋在家中陪著芬玉一待就是幾個月,芬玉的病情始終不樂觀。這天玉秋一個人在房前屋后地忙碌著,突然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出現在自家門口,微笑地看著自己。原來是秦正新!幾個月沒見,秦正新明顯黑瘦了不少,顯然是消受了不少熱帶的陽光。他一笑露出一口白牙,對比更加明顯了。秦正新的到來讓玉秋又驚又喜。人們常說錦上添花容易,雪中送炭難。因為從小生活得艱苦,玉秋看到了很多的冷眼和嘲諷,也過早明白了生活的艱難。這個時候到來的秦正新猶如她的救命稻草一般。然而,芬玉的病終于嚴重到一口飯也吃不下,人瘦到不成樣子,家里的錢又花光了,舉債累累。她也不肯再去治了。春玲夫妻也是厚道人,砸鍋賣鐵也想著幫芬玉,芬玉對春玲說:“表姐,有你這份情意就夠了,這輩子有你做我姐姐也值了,我不能拖累你們。幫我照顧好玉秋。”春玲自然不愿意她這么說,但她知道她的錢也是杯水車薪。芬玉的命是救不回來了,她的意識漸漸開始模糊,時好時壞,每次都是秦正新背著她在醫院跑上跑下。秦正新覺得芬玉只剩下了一把骨頭,他真怕自己把芬玉背折了。芬玉清醒的時候常常會拉著秦正新的手流眼淚,讓他替自己照顧玉秋。芬玉離死亡越來越近,她曾經并不害怕死,年輕的時候拉扯孩子過不下去,也想過死。可是真正到死的時候,芬玉卻感到了一種恐懼,覺得她正墜向一個巨大的黑洞,靈魂就要離自己而去,伸出手卻什么也抓不住。到后來,芬玉的眼淚都流干了,已經哭不出來了,她知道這一次死亡真正的來臨了,她要到另外一個地方去見她的父母和丈夫了,也許那邊她并不孤獨,對她來說身體的傷痛已經足夠大,活著就是疼痛和心碎,唯一割舍不下的就是玉秋。但她無能為力。芬玉終于流干了她人生的最后一滴淚,她死的那天,寒冷的冬天出現了一抹暖陽,透過窗戶照在了芬玉的床上,那么暖和。可玉秋卻感到出奇的冷,芬玉都沒有留下一句話,就在一陣急促的掙扎中去世了,那些蒼白憔悴病痛折磨也被帶走了。玉秋的眼淚也流干了,她以為她已經不會哭了,但最后她還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淚水,任它流淌,秦正新怎么安慰也沒有用。
四
玉秋因為芬玉的死內心變得更加的空空蕩蕩,這種空空蕩蕩不是秦正新的愛可以補償的,但秦正新的愛卻可以一點點緩解玉秋的痛楚,讓她不再去想那些慘淡的歲月。過了一段時間他們還是決定回到沙巴去。芬玉走后,玉秋變得有點神經質,她到沙巴后就和秦正新住在了一起,他們一起開了一家小小的茶餐廳,專賣一些中國的炒飯炒粉炒牛河之類的快餐。開始創業總是很艱難的,難免會有一些摩擦。誠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這話說得倒是一點都沒有錯。在柴米油鹽醬醋茶的瑣碎中,人與人之間那么一點可憐的情分很容易就消磨光了。玉秋本就性格內向沉郁,這下越發沉默了,秦正新的脾氣變得暴躁了不少,常常抽悶煙,只有霍青松可以開導開導他,但兩個人的感情如果發生了變化,外人是很難勸和的,只有靠自身去彌補消化。那家小小的茶餐廳,兩個人用了自己所有的錢盤下來,還借了霍青松和靈清不少錢,不僅如此,能借的朋友幾乎都借了,開頭的日子都是甜蜜的,兩個人齊心協力,再苦似乎也覺得甜蜜。但是他們再怎么努力,依然賺不到什么錢,開頭幾個月還能支撐,后來各路債主找上來的時候,秦正新的挫敗感越來越嚴重,他的脾氣也越來越大,煙酒不離手。畢竟人生地不熟,在馬來西亞做生意也不那么容易,更何況他們倆都沒有做生意的經驗。
當一個男人對人生感到失望無助的時候,恰恰是他最容易放縱自己的時候。玉秋是怎么發現秦正新出軌的呢?她一直患有輕度的神經衰弱,晚上一有聲響就睡不著。秦正新不開心了晚上就會出去喝酒,玉秋因為生意不好和他的齟齬多了起來,也不敢管他,但他不回來她就睡不著。秦正新回來的時候,玉秋假裝睡著了。秦正新自己可能沒有察覺,他的身上有濃濃的香水味,玉秋起床看到秦正新丟在椅子上的襯衫上有女人的口紅印,一看就是不小心蹭的。她心里咯噔一下,但聽到秦正新從浴室出來,她還是放下衣服裝睡。
日子久了,這種事情越來越多,秦正新已經發展到夜不歸宿。這天他出去后,玉秋就關了店,跟上去。秦正新騎著摩托車,玉秋坐著出租車一路跟隨,沒有想到秦正新是和林寰寰約會,約在了海邊。林寰寰穿著大紅的沙灘裙,頭發上也扎著大紅色的發帶,發帶打了一個結留下了長長的飄帶。看到秦正新她就飛奔了過來,整個人撲進了秦正新的懷里。玉秋躲在海邊的石頭后面,心如刀割,不想讓他們兩個看到自己。
她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去的。秦正新回來后,他們大吵了一架,開始時吵的都是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情,后來再吵都是因為林寰寰。吵鬧之后,秦正新奪門而出。
隨著兩人冷戰的加劇,玉秋把小店關閉了,重新回到霍青松那兒做幫廚。靈清和霍青松變著法子哄她開心,但玉秋真的沒法開心起來。她把時間都用來研究菜品了,做哪些菜,做哪些口味,都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買了一堆的菜譜回來研究馬來菜和廣東菜的結合。馬來菜的重點是配料,尤其是肉骨茶。玉秋研究了多日,在大豐海鮮館除了做傳統中國菜,還開始嘗試增加馬來西亞娘惹菜的元素。選擇多了,回頭客增多了,老板對玉秋也刮目相看了。玉秋把精神寄托在做菜上,有一次看到她大汗淋漓地在廚房忙碌的時候,霍青松撇撇嘴對玉秋說:“你這姑娘,不夠聰明啊,這煙熏火燎的地方,哪是你這種身子板待的地兒?長這么漂亮的姑娘,嫁個有錢人,享福去啊。你們姐妹倆真是都不聰明,自己賺錢苦不苦啊?”說完擺擺頭,一副可惜了的表情。玉秋苦笑一下說:“各人各命,我們就這苦命吧!”
這天晚上,玉秋正在廚房汗流浹背地炒著菜,店里的跑堂急急地跑了進來說:“玉秋,外面有人鬧事,你出去看看。”玉秋放下鏟子,脫下圍裙,捋了捋頭發就跟了出去。原來是林寰寰帶了一群人在吃飯,林寰寰穿著粉色的吊帶裙,勾勒出凹凸有致的身材,長長的波浪卷發隨意披散在肩膀上。她坐在椅子上,斜著眼睛很輕蔑地看著玉秋說:“哎喲,幾日不見,你怎么變這樣了?”玉秋冷冷地說:“我咋樣了!”林寰寰呵呵一笑說:“你咋樣了,你自己看不出來嗎?這么胖。”玉秋說:“關你什么事?”
“不關我的事,對對,是不關我的事,你變這么丑是你的事,但你這桌菜做的是什么呀?這總關我事了吧,你看看,這是什么,這還是肉骨茶嗎?”
原本這鍋湯是玉秋精心熬制的,里面有不少藥材,當歸、枸杞、黨參、薄荷、玉竹、川芎、肉桂……熬制的時候,特別注意了火候,所以藥材雖多,口味卻很清淡香甜。現在這鍋湯卻顯得非常的渾濁,一看就是被動了手腳。這時候老板和霍青松過來了,老板說:“怎么了?”林寰寰的跟班拿著筷子在碗里攪動了幾下,扒拉出一個黑乎乎的長條狀東西,夾到玉秋面前:“看到沒有,是老鼠尾巴。”林寰寰做了一個被惡心到的動作,站起來對老板說:“這就是你們的創新,放老鼠尾巴進湯里!”老板反駁道:“這怎么可能!”玉秋在旁邊看著那老鼠的尾巴,覺得一陣眩暈。她捂著嘴巴,沖了出去,到洗手間瘋狂地吐起來。老板和林寰寰理論一番之后,免了她的單。林寰寰不是為錢,她是為了來找玉秋的碴,但玉秋已經吐成那樣,她只有悻悻地走了。
秦正新雖然和玉秋分手了,卻沒有真正和林寰寰在一起,林寰寰的父親也不允許他們發展戀情,但他一向管不住林寰寰,初中畢業后林寰寰都沒有繼續讀書。林寰寰的爸爸林發根只有小學文化,靠著做木材生意成了暴發戶。他娶了兩房太太,林寰寰是他的第二個老婆生的,從小嬌生慣養,林寰寰想要什么東西,只要他能辦到的就從不說二話,所以林寰寰的性格變得驕縱任性。她想要得到的東西她怎么也得得到。但是她不知道有些東西不是她想有就有的,尤其是愛情。
玉秋吐得膽汁都快出來了。霍青松到底有些經驗,對玉秋說:“你去醫院看看啊?”霍青松把自己熟悉的華人醫生的電話告訴了玉秋,玉秋感到自己的身體怪怪的,最近吃得不多,倒顯得臃腫了一些,吃了東西后常有干嘔的感覺。到了醫院,果不其然,玉秋是懷孕了。她拿著醫生給的化驗單,感覺一陣陣眩暈。她摸著自己的肚子說:“孩子,你來得還真不是時候。”
玉秋沒有把這件事情告訴秦正新,而是告訴了靈清。靈清聽了好高興,但隨即又擔心起來,覺得玉秋自己還是個孩子,居無定所的,又和秦正新鬧成了那樣,孩子生下來怎么辦呢?看著靈清陰晴不定的表情,玉秋也難過了起來。霍青松對玉秋說:“丫頭,沒關系,把孩子生下來,我去找秦正新,我來幫你和他說,你們倆還養不起一個孩子嗎?更何況還有我和靈清呢!”玉秋還在賭氣,不想見秦正新。但考慮到孩子,她一時也不知該怎么辦。
五
霍青松找到秦正新,告訴他玉秋懷孕的事情,正在工作的秦正新放下自己的橡皮艇,連潛水服都沒有脫就飛奔而去。玉秋不太想理秦正新,但看他坐了幾小時的船,又坐了一小時的汽車才來到大豐海鮮館,就抹了把眼淚說:“我給你做飯去。”兩人就這樣慢慢和好了,打算先籌辦婚禮,但想到回去領證,路途遙遠,玉秋又懷有身孕,很不穩定,就決定在沙巴先辦個婚禮請朋友們吃一頓。秦正新的父母不同意玉秋和秦正新的婚事,自然也就沒有來。玉秋懷孕后,秦正新的脾氣收斂了不少,他在沙巴市區找了一個運貨的工作,每天早出晚歸,想給玉秋和孩子好一點的環境。玉秋的肚子越來越大,開始行動不便了,所以也不能工作。老板照顧她,讓她回家安心養胎。她到租住的房子隔壁的婆婆家,借用那臺老式的縫紉機做些小孩子的衣服。看著自己親手做的衣服,覺得挺幸福的。她不知道,林寰寰一直在找秦正新,不甘心因為玉秋的懷孕,秦正新就回到了她身邊。古語說女追男隔層紗,但是像林寰寰這么個追法,很少有男人能受得住。秦正新運貨的時候不想搭理她,她卻跟前跟后地追著。知道秦正新愛喝酒,她就拉著他去喝酒,秦正新拒絕了半天,還是隨她去了。兩個人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醒來的時候,秦正新看著躺在自己身邊的林寰寰,無比后悔。他對林寰寰說:“你還是好自為之吧,我們的關系到此為止。”
秦正新對玉秋有一種歉意,對玉秋的態度更好了些,他給玉秋買了她最愛吃的蛋撻,不明就里的玉秋不解地看著秦正新說:“家里有吃的,我是個廚子,什么菜不會做啊,何必浪費呢?”秦正新看著玉秋,對她說:“我會對你好的,你好好把孩子生下來。”玉秋覺得幸福,除了一種做母親的幸福,還有一絲絲的感動。
秦正新沒有想到的是,林寰寰也懷孕了。秦正新得知后,還是斷然拒絕了林寰寰提出的要求,拒絕離開玉秋和她在一起。林寰寰最后決定去和玉秋談,玉秋不想看到她,但還是經不住她的糾纏,和她見了面。穿著火紅吊帶裙的林寰寰,有著水蛇一般的腰身,輕蔑地看著玉秋說:“你看看你什么樣子,你什么地方比我強啊。你有的我都有,你知道嗎?我也懷孕了。”玉秋看到林寰寰緊身的吊帶裙果然在腹部微微隆起了一塊,頓時覺得眩暈:“你和我說這些干嗎?和我有關系嗎?”
“不要裝了,你難道不知道孩子是誰的嗎?”林寰寰居高臨下地對玉秋說,玉秋回答她:“孩子是誰的,和我沒關系,我也沒興趣知道。我現在要走了。你不要攔著我,我希望你以后不要來打擾我們的生活。”回去的路上,玉秋恍恍惚惚,看到命運這只大手揮舞著示意一些人快速向前,又示意一些人快速后退。好多條隊伍,有前有后,玉秋夾雜在人流中,她不知道自己該走向哪里,她只希望命運能對她善意一點再善意一點。悲哀感壓迫著她,玉秋的肚子一陣緊縮,羊水已經破了。跌倒在地的玉秋痛苦呼喊著,幸虧有路過的人看到了,把她送到了醫院,緊急剖宮生下了一個女兒。醫生說再晚點,大人孩子的命就都難保。
生了孩子的玉秋,臉上有了做母親的幸福笑容,但是她看著自己懷里的孩子,卻又不時地回想起林寰寰的話,在幸福的同時又多了一絲憂愁。這次死里逃生的經歷讓玉秋覺得自己一下子老了不少,才二十歲的人卻長了幾根白頭發。靈清看到有些心疼,她對玉秋說:“你不要想太多了,安心把月子做完。”這段日子,靈清給了玉秋不少錢,從芬玉生病到玉秋懷孕,除了秦正新外幾乎都是靈清在支撐,玉秋自覺自己欠得太多,但是靈清說:“你要覺得欠我的,等你以后好了,你再還給我。”玉秋說好,但玉秋知道這輩子即使還得了錢也還不了這欠下的人情債。
霍青松的前妻到沙巴來找霍青松,大家才知道原來一直孤身一人的霍青松是有過老婆的。他前妻異常美麗,那種美不同于玉秋也不同于靈清。玉秋的美帶著一種沉靜的氣質,像秋天的樹葉,干凈內斂沉靜,只是帶著一絲稚氣。而靈清是明艷的,開朗的,大大咧咧沒心沒肺的,說話咋咋呼呼,讓人一眼就看到心窩子里去,沒有心計卻活得開心,煩惱不會超過三天。如果說玉秋和靈清都還是姑娘的話,那霍青松的前妻就稱得起是女人。按理說她也不小了,至少也有四十歲了,但她的美貌還是遮不住;和她一起來的還有一個十來歲的小姑娘,小姑娘長得也很漂亮,可以說是這個女人的翻版,美成這樣真的是上天的眷顧。小姑娘和霍青松的老婆都穿著價格昂貴的迪奧,靈清知道這個系列的款式價格不菲,她一年賺的錢也買不起。
霍青松的前妻叫芝芝,芝芝和霍青松結婚的時候,霍青松還是一個什么也沒有的小伙子,兩人創業多年,商海沉浮終于有了自己的事業,關系卻沒有那么好了。芝芝愛上了別的男人,并且有了孩子小若。小若出生之后霍青松離開了家鄉,他不能忍受相濡以沫的妻子對自己的背叛,但還是把所有的產業都給了芝芝。芝芝并沒有和那個男人結婚,這些年一個人帶著小若生活。她一直不知道霍青松在哪里,然而生活的戲劇性就在不經意間展現:她的一個朋友到沙巴度假,意外地看到了霍青松。芝芝就帶著小若來了,想找回霍青松。霍青松對芝芝說:“我們的感情在命運面前早就已經疲憊不堪,我根本無法照顧你和孩子,你只能自己照顧自己,我沒有辦法面對你。”芝芝說:“過了這么多年你還不能原諒我嗎?”霍青松說:“不,我早已經原諒你了。只是我已經不愛你了,我有了新的女朋友。”說完他摟了摟靈清的肩膀。芝芝看著靈清,眼睛中有一種復雜的感情。芝芝失望地帶著孩子離開了沙巴。
靈清問霍青松這句表白是不是真的。霍青松說:“當然是假的,你想多了。”
六
靈清帶游客去威斯特紅樹林看螢火蟲,在救一個頑皮的孩子的時候摔斷了腿。還在月子中的玉秋和秦正新自顧不暇,照顧靈清的事情自然就落在了霍青松的身上。他雖然是個大男人,但照顧人還是非常細心的。兩人認識好幾年了,都是在一起喝酒聊天,這樣子的相處還是第一次,感情不知不覺又近了一些,霍青松不再說靈清總是穿得不男不女的了,靈清也不再說霍青松胡子拉碴。這天傍晚,霍青松帶著拄著拐杖的靈清到海邊玩,兩個人坐在沙灘上,各自拿著啤酒。靈清對霍青松說:“來沙巴這么久,第一次自己這么輕松地坐在海邊欣賞落日,像做夢一樣。”兩人坐著聊著,消磨著時光。
霍青松突然說:“我準備回去了。”靈清有些不解地看著霍青松,霍青松笑了一下:“我準備回老家去了。”
“你不是拒絕了芝芝,怎么又想回去了?”靈清有些不解。
“逃避了這么多年,也該回去了。家里還有一些親朋,父母雖然不在了,但人老了,也該葉落歸根了。我不想在這個海鮮館當一輩子廚師,每天煙熏火燎的。”
靈清有些失落,她“哦”了一聲,把自己的啤酒喝盡了。
離別的日子很快到來,霍青松走的時候并沒有刻意去和靈清告別,那天靈清帶團出差。霍青松走了之后,靈清覺得沙巴的日子突然冷清了下來,沒有了談得來的朋友,內心變得空蕩蕩。
后來,秦正新帶著玉秋回廣州創業,靈清更孤單了。沒有多久她就結束了沙巴的工作,也回到了中國。在北京,她重新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寫字樓里做白領。這種工作其實并不適合她,她沒有處理辦公室政治的能力,性格又太直接火暴,繞不起那么多的腦回路。所以她混得不夠好,但混口飯吃是一點問題都沒有的。她還是時常會想起霍青松,想起在沙巴海邊吃海鮮喝啤酒的日子。那時候她似乎很快樂,覺得天地很大,而現在,她在高樓林立的都市叢林中,只能縮在自己小小的鋼筋水泥圍起來的鴿子籠中。
至于愛情,顯得很像快餐。有不少人給她介紹,她也談過幾個,都不在狀態,沒有愛的感覺,她就都拒絕了。她常常會回廣州看看玉秋和秦正新的孩子,那是她比較快樂的時候,可看到他們一家人其樂融融、經歷過不少波折后更加緊密相連,靈清的失落感更深了。秦正新和玉秋開了一個海鮮檔,他們夫唱婦隨,生意做得很是紅火,少女時代吃了不少苦,一直有點營養不良的玉秋越發圓潤起來了。如果不是見過曾經多愁善感、楚楚可憐的玉秋,靈清都不相信這會是一個人。
這次回來探親,靈清待得似乎久了一些,她看了很多以前的同學朋友,也走了不少親戚,在這些推杯換盞中,靈清看到了自己的意興闌珊。她知道對于很多離開家鄉超過十年的人來說,故鄉有的時候真的就像過年時停留的一個驛站,很多人的內心是回不去的。而遠方又是自己的歸宿嗎?在這回與去的過程中,她感覺到自己的輪廓漸漸變得模糊。
靈清拒絕秦正新送她,獨自一個人走在廣州深夜的街頭。她說自己住的賓館很近,不需要送,讓他們回去帶孩子。今天她喝了不少酒,歷來號稱千杯不醉的她有些醉了。她有些踉蹌地推開酒店大堂的門,卻看見一個熟悉的身影在大廳的咖啡吧和人聊天。她搖搖晃晃地走過去,在那個人的身邊轉了一圈,用手指著那個人說:“霍青松!你是霍青松!”那人看到她,顯然一驚。兩個人相視而笑,不約而同說了一句“天涯何處不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