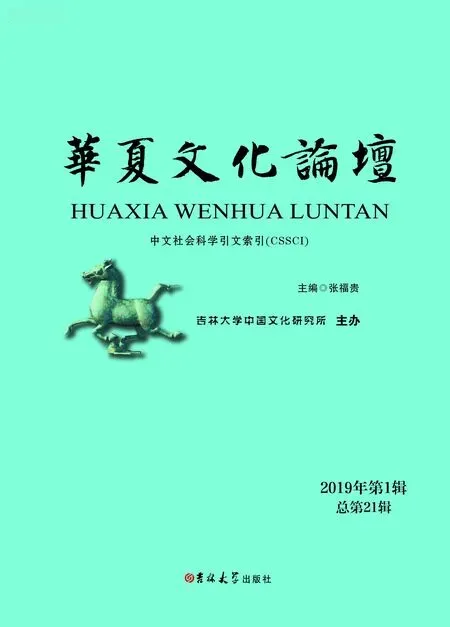關于文學教育
張清華 譚宇婷
譚宇婷:
老師,您可以大體介紹一下北京師范大學創意寫作教育目前的狀況嗎?張清華:
先糾正一下,我們這兒不叫“創意寫作”,我們的叫作“文學創作”。我們沒有“創意寫作研究中心”,我們的中心是“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寫作中心”。因為“創意寫作”是美國來的一個概念,跟大眾文化、實用的、流行的、消費的寫作聯系可能比較密切。我們強調“人文”意義上的“純文學”的創作,這是概念。人民大學的叫作“創造性寫作”,我覺得這個概念也挺好。創意寫作是“MFA”,是專業學位,側重于實用寫作訓練,可能強調技術化的訓練。我們則強調純文學意義上的寫作教育。我們的理念,我簡單介紹一下,就是文學教育要復興。文學教育要復興主要是基于最近幾十年來形成的一個——我認為是陳規、陋習,即完全把中文教育當成了一種知識教育和學院教育。而其作為素養和能力的向度被長期漠視了。大學老師會公然宣稱“我們不培養作家”之類的說法。當然作家也確實不是培養的。但是你不能說在你的教學當中只強調知識,不強調能力。這樣的話,它就不是一種知行合一的教育。古代中國的文學教育也不是沒有問題,但是它有一個很大的優點——所有受教育者都是既能讀又能寫的。一個古代的學人字寫不好,肯定不行;不能寫一手好文章,不會寫詩,肯定不行。也就是說,只要他接受了基本訓練、基本教育,他的這兩種能力是同時兼備的。新文學早期那批學人也都是這樣,因為他們深受傳統教育的熏陶,既能研究又能寫,比如執教女師大的魯迅、執教北大的胡適、陳獨秀、沈尹默、劉半農、宗白華等。他們既能做非常深的學術研究,又能寫一手好文章或者好詩歌。
在最近若干年,大學文學教育被邊緣化為以“寫作教研室”為主導的一種能力訓練,但是寫作教研室在最近三四十年中,在各個大學里都萎縮了。萎縮的一個原因,我認為是定位有問題。它把寫作定義為應用文或者是一種專用文體、實用文體的訓練。當然也會有少量寫散文的訓練,但離藝術真正的核心部分比較遠。第二個原因是方向。文學教育體系的構建方向仍然是“知識化”。寫作課老師還要講一套理論,而這個理論實際上是沒有太多實際意義和用處的,也缺少學術上的自足性和深度,有些知識屬于假知識,那么實際上受害的首先是老師。
譚宇婷:
老師,請問如果不用一套理論去指導學生寫作,您覺得應該用什么指導?張清華:
第一,它不是說不應該用理論指導,關鍵是這些理論是一套完全知識化的東西。這些知識化的東西在實際理解中并無真實的價值;第二,寫作不應該只是紙上談兵,關鍵在于實踐與互動。這就需要教師不只會“教”、不止懂得一些看上去無比正確的理論,還需要老師能夠自己寫,能夠真正指導學生的寫作練習。譚宇婷:
有些教寫作的老師后來會漸漸轉向中國現當代文學或者文藝理論這兩個方向。張清華:
這也是一個原因。因為寫作專業的專業邊界、學術內涵不清晰,那么老師的自我發展就會受到影響。老師寫論文都不知道寫什么樣的論文,在哪里發表,這個學術體系怎么建立?老師評職稱都成問題了,要想在寫作教研室評職稱,要么靠到現當代,要么到文藝理論專業去。作為其他專業的附庸,他才能夠有飯吃。所以對老師的影響很大。總之,我認為主要的原因是專業設置的方向和定位不清晰、不準確。譚宇婷:
請問老師,你們是怎樣解決這些問題的?張清華:
我們主要通過幾種方式。一是大學要引進作家。真正的作家,他是懂得創作的。同時大學的老師在自我發展中不能忽視寫作能力的保有。大學里的學術老師自覺保有寫作的興趣,方能對學生有更多的影響。第二是課程的設置上,增加實用的、能夠促進文學能力增長的、對學生實際寫作能力有幫助的課程。這些課程可以由作家來講授,也可以由懂創作的學術老師來講授。第三就是招收文學創作專業或方向的本科生,甚至研究生或者博士生。通過這種專業方向的增設來促進創作人才的培養以及寫作風氣的養成。我覺得主要還是通過各種各樣有益的形式,來提高所有學生的文學素養。中文學科的所有學生必須以既能讀又能寫作為自己的成長目標和學習使命。你會寫了,自然你就會看了。因為你的標準已經比別人更苛刻、更貼近語言本身了。一個會寫作的人對語言的敏感性、對語言的要求的苛刻程度比一般人要高得多。如果每個學生有這樣一種自我要求,整個教育的品質肯定會有提高。一個中文系的學生不能說上大學就背了一堆知識,離文學仍然很遠,甚至越來越遠。大部分學生是這樣的情況——入學的時候對專業還有一些熱愛,畢業的時候便對專業基本沒有任何感情,也沒有任何發自內心的熱愛了。這主要是知識化帶來的問題。知識化現在在中小學是問題最嚴重的,大學里的知識化傾向也是越來越嚴重。
還要再強調一下——我不是反對知識,我是反對單一的知識化,特別是文學教育是不能單一知識化的,因為審美活動是一種精神活動,對藝術的感知是一種經驗的、心靈的、審美的、精神性的活動。這種能力的培養與知識化的東西有時候是有關的,有時候是無關的。不只是單個的施教的老師,整個教育觀念和體系都應該有一個反思。所以我們北師大就是借助莫言老師的加盟,成立國際寫作中心,并且秉承我們過去的傳統。因為北京師范大學文學教育的傳統還是有一些值得梳理和挖掘的。當年魯迅先生在女師大任教時間是最長的,他在女師大任教六年,女師大是北師大的一個前身。后來像沈從文、穆木天、黃藥眠、鄭敏等很多作家和詩人都曾任教北師大。當代以來,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蘇童、莫言、余華、劉震云、遲子建、嚴歌苓、陳染、劉恒等一大堆作家都是從北師大各類不同的辦學方式中走出來的。
譚宇婷:
請問老師,具體到課堂上,你們是怎樣做的呢?張清華:
我們文學創作方向和當代文學方向的研究生主干課程是一致的,并在這個基礎上再給學生另開三門課。一門是作家的專題講座課。每屆學生都要有一個學期的課由作家來講,每次作家講的題目都不一樣。十幾個作家分別講,每人講一到兩次。作家們的創作觀念、文學主張都很不一樣。這樣對學生創作會有多方面的啟發和激活。然后由擅長創作的老師給學生開設文學創作和創造性寫作的實踐課,分兩種形式,一種是直接在課堂上進行文學虛構訓練,跟愛荷華的寫作坊很像,我們直接在課堂上就開始寫。比如說有一個題目,大家嘗試如何去虛構,寫了之后相互交換、討論,互相給對方提出評價、分析。這樣相互激活、認知如何進行虛構,如何推進文字的生成等,構成寫作的一個全過程的訓練。另外一種方式就是通過講一些寫作中的問題,讓學生學會不同形式的寫作模型。比如我們會讓學生寫一篇向某個原型致敬的小說。比如我出一個題目,“失物復得”的原型敘述,以《今古奇觀》里面《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為原型。《蔣興哥重會珍珠衫》是一個非常經典的古典傳奇,它的故事非常曲折,但是可以歸納為“物歸原主”。以它為原型,可以找一些現代的故事,讓學生寫一篇以失物復得、物歸原主為內容的小說。我的一個學生崔君,就寫了一篇非常漂亮的中篇小說,發在了《西湖》雜志上。人家還讓我給她配上一個評論。她就寫得特別好。我們希望學生有類似的訓練,讓他知道寫作是有規律的,好的作家的寫作一定是和前人有關系的。這也是艾略特講的傳統與個人才能之間是一種呼應關系,沒有哪一個人的創作是單獨依靠自己的才能能夠成立的。你現在的寫作一定是和前人的經驗發生關系的。譚宇婷:
請問老師,您覺得這個規律是可以總結的嗎?張清華:
當然可以。譚宇婷:
可以總結并且可以教授嗎?張清華:
美國人是這樣認為的,但這只是一種訓練。真正的創造性的寫作是把這種訓練作為一種有效的技能,在這種基礎上還要“出走”,還要跟他的寫作個性結合,也就是“去知識化”。要不然老師就講一堆知識,講一堆知識學生都聽得很明白,但是學生還是不會寫。不會寫有什么用?但對于更多的學生來說,即便不會寫,也要能夠懂得文學的肌理——不只是懂得作為知識的文學,更多是懂得作為藝術的文學。我們應該實現這樣一種教學。譚宇婷:
老師,寫詩也能總結出規律嗎?張清華:
到目前為止我都不敢跟學生講如何寫詩。寫詩只能單獨指導,作為課程我覺得很難。譚宇婷:
是因為覺得寫詩是需要天賦的嗎?張清華:
對,但不只是天賦,因為天賦不是先驗的。你說你有天賦,你的天賦在哪里?天賦是通過實踐來驗證的。你不寫怎么知道你有天賦?你只有寫了才能知道有天賦。而且你的天賦有時候是不可預料的,就是說一開始你沒準什么天賦也沒有,但突然就很厲害了。這是個人悟性和努力程度決定的。所以,如果不在寫作實踐當中,而且是多少年如一日、持續地努力地寫作的話,一個人是沒有什么天賦的。沒有離開語言的思想,也沒有離開寫作實踐的文學天賦。你說一個大作家那么厲害,你說他天賦確實厲害,但是你知道他肯定是癡迷這件事,沉迷其間,他才能最終成為作家。但對很多人來說,他成不了作家。成不了作家沒關系,能寫一筆也很好。比如你學一學漢賦的鋪排,你說話的氣度就不一樣,你的修辭就比別人華美和豐贍。當然,你要是能寫出漢賦式的句子就很厲害了。我幾年前給我曾就讀的中學寫了一篇賦,寫到最后,我覺得寫得最出彩的句子都是跟《楚辭》借來的。“轉吾道夫昆侖兮,路修遠以周流……”前面我覺得寫得都平平,但寫到最后,我寫著寫著把自己都感動了。一到學校的重大活動,中學里的所有師生就一起高聲齊誦這篇賦,挺有氣勢。我覺得,就我的目力所及范圍,我的中學里出來的人,如果我不寫,別人寫了可能不靠譜。我寫了以后,這篇賦可以用很多年,直到將來出現一個比我更厲害的,把它廢了。這個東西必須是在某種情況下才有效,你不能無條件地認可它。詩呢,可能不能作為寫作課來講,只能作為分析課。但是老師還是不能把詩當作知識來講,必須把它當作詩來講。這是有難度的,不是每個老師都能做的。
譚宇婷:
請問老師,您對美國的創意寫作教育有了解嗎?張清華:
我們與愛荷華簽有合作協議,我們也去訪問過,他們也來我們這兒回訪過。我們每年暑假都有學生被派到愛荷華去。在他們那兒,學生還是覺得挺有收獲的。他們是小班嘛,每個班就是幾個學生,不超過十個學生,老師跟學生互動較多。譚宇婷:
請問老師,在愛荷華的學習中,您覺得寫作訓練對學生個人影響更大還是中美文化差異、沖突對寫作潛力的激發更大?張清華:
中美文化沒有什么沖突。這可能是想象出來的。總體上可能有這么一回事,但具體到個人就不一定了,看你交流什么,如果是單就一個文學問題,你跟一個美國人交流極有可能比跟一個中國人的交流還要順暢,這是有可能的。譚宇婷:
思維方式上的差異呢?張清華:
至于思維方式,如果你是讀一個美國詩人的作品,和你讀一個中國詩人的作品,誰離你更近,不一定。你要是讀一個好的詩人,比如史蒂文斯、狄蘭·托馬斯等,你會覺得你和他們其實很接近,心靈并不遙遠。從人性上來講,并沒有什么。所謂文學差異更多是被言說、被虛構和夸大的一種政治敘述,是從制度上和所謂的文化上被構造的。譚宇婷:
請問老師,您對我們這個年齡的學生學習寫作有什么建議嗎?張清華:
學習寫作,要盡快地丟掉自己。我給我們學生上的第一節課就會說,從現在開始,把你們原來寫的那些校園生活、你自己的小的情感經歷通通扔到垃圾桶里。這只是一種說法,就是說你要盡快地嘗試、學會普遍意義上的寫作,而不是一種自發寫作。像寫日記、小孩寫成長故事等都是自發寫作。大部分在中學成名的小孩寫了很多東西,有的出了很多書,有的家長拿出來說,你看,我們孩子都出了一摞書了。我說,那我也不看,你出這一摞書沒什么用,因為它不是什么文學作品。當然這只是一種強調。不是說張老師怎么這么偏激、武斷,我是希望學生學會不只是用自己的經驗來寫作,而是以他人的經驗去寫作。你必須走出自己,走向別人,建立多個主題。你在寫作時不止作為一個作者,還要作為一個讀者。你只有同時作為讀者,你對自己的作品才有反思。你寫給誰?只寫給自己嗎?你只寫給自己有什么意義?那你就寫,寫了一會兒擱在抽屜里你自己看。那不是文學,文學是將所有普遍的形象重新還原它一個生命,是對大多數人,甚至所有人共同經驗的傳達。這也是它的難度。譚宇婷:
嗯,老師,請問您對現在文學教育不滿意的地方在哪里呢?也是知識化的那一面嗎?張清華:
我覺得現在大學中文教育的問題,歸根結底就是單向度的知識化。譚宇婷:
請問老師,您覺得寫作教育以后的發展會越來越好嗎?張清華:
寫作教育,歸根結底不是目的。你不可能培養太多的作家,所有的人都成為作家是不可能的,也是沒有必要的。但所有的人都應該成為藝術的知音或者是內行,文學的知音和內行。寫作教育歸根結底是一種人格教育。古人還說,“腹有詩書氣自華”。中文系如果培養市儈或者完全不懂文學、沒有文學氣質的人,那設置中文系干嗎?現代社會人的分工都很精細,文學是既有分工又包羅萬象的,它是一種人格教育。從文學系出來的人應該比從其他系出來的人更有氣質,更懂得文學和藝術本身的奧妙,作為人,他的人格也更健全和復雜。譚宇婷:
請問老師,北師大在寫作方面的培養目標是什么呢?張清華:
沒有一個定制的目標,我覺得最終還是培養人,作為藝術知音和內行的人,培養人文精神。拿音樂類比,你可以彈巴赫,但是你也可以彈很多練習曲。這個練習曲是什么意思呢,實際上就是練習你的技術。從藝術角度來說,練習曲可能不是一個自足的藝術作品,但是它會更多地包含藝術的元素和要素。譚宇婷:
老師,您平常會寫很多詩,請問您覺得寫詩對您最大的改變是什么?張清華:
寫詩其實也沒有什么改變,但是它會有另外一個自我,會讓你覺得你比別人多活了一世。你這輩子既是作為一個“俗人”在生活,同時也是作為一個“潛伏者”,一個可能的詩人在生活。你處理你所遇到的事務,所遇到的一切境遇和經驗的時候,你等于是比別人多活了一遍。